1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我如梦游般在郧西山城与李相华第一次相遇。一顿大酒后,我感觉这家伙好像正是我要寻找的同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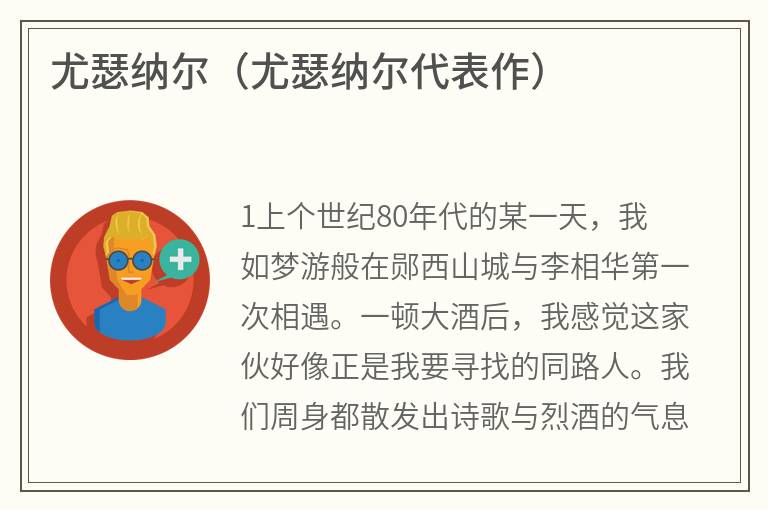
尤瑟纳尔(尤瑟纳尔代表作)
我们周身都散发出诗歌与烈酒的气息。
他不善言谈,长得魁梧或粗莽,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草药味,原来他在一家中医药材公司混饭。我记得在他的单身宿舍,他用简易电炉做了几道菜,呼朋唤友,我们喝得东倒西歪,最后我念念不舍坐上最后一趟班车。在车上,我借着酒力,掏出他的诗稿,大声地读了起来。
我们用书信、诗歌交往多年。他的手写稿,一律横排繁体。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用繁体字写着现代诗,你不跟他见面,会觉得有些古怪,以为其人是个小县城里泥古的酸腐老文人,喜欢钻故纸堆。那时他除了书,也基本一无所有。内心沉郁,眼神明亮,大智若愚。
某年某月,与一位当编辑的作家文友在一次闲聊中,他情不自禁地谈起了李相华的一篇小说,说在终审时被主编拿掉,大骂主编有眼无珠,对此耿耿于怀。他说这么好的作品,被埋没,太可惜了,便推荐给我供职的刊物。小说刊发后,正好碰上当年湖北省期刊评选,这篇小说榜上有名。
时隔多年,我记得这篇小说是《猎人来得》,《武当风》刊发时间为1990年。
2
后来李相华辞职南下,在闽南扎根。他寄给我诗集《死亡照亮的眼睛》,后又收到他的小说集《黑白桐》。多年过去,感觉李相华的写作,一直在诗歌与小说之间切换。从诗到小说的写作者不少,成功率也高;从小说到诗歌极少,也几乎没有成功的样板;既写小说又写诗歌者,大多把诗歌当成“轻武器”,而重点在小说,很难有把诗歌看得比小说同等要重的小说写作者。李相华写作属于后者,他不是简单的“切换”,而是“融合”。
这就注定,他不管用哪种形式写作,在现实和虚构之间,他寻找的是诗意,是真实。尼采有言:艺术的最高形式是诗,而诗的最高形式是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也说:悲剧是最高级的艺术。由此,可以猜想,高级的语言艺术其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表达都统一在完美的叙述里,高级的小说,就是超越现实的悲剧诗。
谈论李相华的小说,我不得不谈《猎人来得》。时隔多年,再读他的这篇处女作,恍惚在读一篇新作,内心时松时紧。这个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一个人与熊互相复仇、互相被打败、互相和解的故事。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小说释放出巨大的张力。海明威写过多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但他是凭借中篇《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其小说讲述的是人与鲨鱼搏斗的故事,一个含义饱满的主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桑迪亚哥的独白,成为影响世人的经典金句。而在《猎人来得》里,人和熊都可能被失败和被毁灭,但是最终两者用死亡走向了和解。这是小说从复仇,到你死我活,到最终“打了个平手”,这个悲剧升华成诗,蕴含一种人与自然生存之道、哲学之道。这个小说还有一些神来之笔,意味深远,比如村寨人拿黑熊当图腾,阻止来得猎杀黑熊,是因为内心长久的惧怕;而当熊死去,他们才把猎手当成了英雄,以熊来祭奠。故事的反转,更呈现出一个短篇蕴含的复杂人性。
这个故事把人性与兽性融合在一起,写出了让你想不到的结局。
尽管人与熊双双倒在血泊中,但出现了神奇的一幕:“……老来得苏醒过来,他感觉到,仿佛有一只温软的手在抚摸他的伤口,他吃力地睁开眼睛,见公熊依偎在他的身边,伸出长长的舌头残喘着。一行热泪,从老来得的眼眶流出,他记得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他伸出手去,动情地抚摸着公熊的头。此时,夕阳正落入两山之凹,暮色渐起。老来得的眼前,有无数个金星银星在闪烁,飘忽不定,仿佛在为他和公熊唱着一支支幽幽的葬歌。他朝夕阳投去最后的一瞥,他看见了,在天边在夕阳没落的地方,有无数个白云仙子在向他招手,命若游丝之际,老来得幻觉到公熊变成了年青的来得,他们手携着手,朝白云的仙乡飞去……”
我们看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狮子在一场王位的争夺中,尽管伴随着背叛、悲剧和冲突,尽管对象是狮子,但也要体现出好莱坞英雄主义的经典套路。来得和熊走向死亡最后抚摸,然后在一个梦中飞去,这意想不到的结局,折射出一种悲剧之美。这种升华,才是小说的力量。
从一开始,李相华的小说叙述,就显得老辣。小说语言的精炼,节奏的控制,成为他写作的难得起点。
3
小说是一门手艺活。这话来自古老的讲故事的传统,说书人就是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技巧是留下包袱和玄机,带有煽动,夸张,尽显铺张,最后自圆其说。有一类小说,就把这样的手艺学得很圆通。但是这种套路写作,大多写的还是故事。说与写,有天壤之别。而小说中的故事却往往只是一个壳,壳里装的东西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故事的叙述、结构、角度,要靠语言来编织,还有小说语言本身就决定其小说气质。
短篇的空间很小,但是如钻石一般,你切割的面再多,每个面的光,最终要聚焦到一点,以达到饱和。估计李相华本人和其他读者,很在乎他的中篇小说的写作,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对他的短篇更感兴趣。比如读《路上》《白狼》《孤山道士》《考伯的棋谱如叔的棋》,其完成的饱满度很高,精致而耐读。与他的早期小说想比,显然他对描写失去了耐心,消减了某些惯于叙述的腔调,几句简短的对话,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这让我油然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道出了短篇的“物理原理”。
知名作家中,如余华、王安忆、莫言等,他们曾透露过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怕写人物的对话。一个人外在形象、心理特点还好把握,但是把对话写到精而准,就有难度,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段的意识流的内心独白无关;而海明威是写对话的高手,某些短篇小说,全是用对话构成,素净,简练,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对极简主义小说大师卡佛而言,他简在哪里,约在何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翻开卡佛,好像他的讲述和故事平淡无奇,但读完你会惊讶、沉思。显然他“简”在限制性叙述,“约”在给小说的走向,以放开性结局。
《路上》就属于这种简约的风格,除此与李相华的早期写作相比,他讲述的方式有明显的变化,不露声色,虚虚实实,人鬼相杂,现实与梦幻如多棱镜折射出一些奇异的光亮。虚构的力量就在于看似背离了生活的逻辑,但又切合了艺术的逻辑,这种逻辑,也是小说的真相,或是要抵达的人性的真实。据他所说,这是一篇“偶拾”的作品,他不知不觉让小说走向了“歧路”,也就是说,干脆把现实拉进幻境。这样,短短的一篇小说,便获得了飞升的姿态与力量。这个小说被《小说选刊》编辑一眼相中,并情不自禁写下编辑感言,便可见一斑。想必这个小说,如一束缝隙里的光,触动了一个编辑麻木的神经。对一个审美疲劳的职业编辑而言,本人对此深有感触,那就是读到一篇独特的优秀作品,会获得这种职业带来的满足感。
看来“歧路”上的“偶拾”,已经不自觉地抛开了限定的意图。余华说,他的写作就是从“虚假”开始的,他说的“虚假”是怎么摆脱现实的表象,回到人性的真实。而小说得寻找到这条路,尽管走起来并不轻松。虚构的力量,是多种元素构成的,还因为你的写作意念和故事走向了一条隐秘不知的小路。
4
《孤山道士》《考伯的棋谱如叔的棋》虽然只是短篇,但时间跨度大,是一篇峰回路转的复杂小说,人物刻画,故事的延展,悲情而超拔。《孤山道士》让我联想起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也写过的一个道士,写得轻灵、浪漫,具有东方道教文化的坐忘之境。而孤山道士生在动荡年代,无所依求,躲进一个荒废的孤山寺,偶尔独行于山下的世界。他的身世穿起一些人世的苦念和奇异的经历。人世的偶然,对小说而言,要集合起必然的理由,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这个小说,有些“笨重”,如果减掉一些“线头”(情节),会显得更合理、轻盈一些。这或许是一个中篇的料,做成了短篇。
《白狼》的故事凝重,情节纷至沓来,具有传奇性,让人感觉面对的是幅厚重、沉郁风俗画卷。这个小说比《猎人来得》来得更粗砺,如烈酒,劲道更足。
5
李相华的小说故事大都具有传奇性,但为何他的小说不乏很强的现代感,这是因为他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小说里的诗意。当然这与他写诗有关。一种潜藏的诗意,在一些段落里,让人内心一怔。诗意不是诗化,诗化的语言,不一定就有诗意。一首纯粹的诗由意象构成,意境深远,跨度很大。而对小说而言,其诗意是一种时隐时现的东西,是一种语言的味道,是一种对人物形象准确的点击。当年何立伟的《白色鸟》,汪曾祺的《受戒》,影响深远,具有明显的诗化意味,这是一种类型的诗化,简略,白描,淡然,但又直击人心。对短篇而言,学会克服惯常的叙述习气,确实很难。写短篇就是对叙述控制的考验;或者说,好的短篇小说,都具有诗的特质。
6
多年来,李相华的写作,好像在中篇上居多,每次他发给我作品,我都有些为难,就因为刊物的容量有限。他的“三个证明”(《王固本的活人证明》《卫仔玉的死亡证明》《宋公明的无罪证明》)成为他中篇写作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小说的标题即可以看出,他的小说已经深度介入严酷的现实与深度的人性。也可以说这是废话。我要说是,写当代生活是有难度的,总有人说,作家的想象与虚构已经追不上现实的荒诞与离奇。其实这是个伪命题。我们确实生活在剧变或聚变或裂变的现实里,我们每天的关注点,其实都已经令人麻木或支离破碎,我们追踪现实的热度,碎片化猎奇和刺激,但是你已经被经验,人生被结构,想象被僵化。变化的是现实,但不变的是人性,为此,小说的虚构,或阅读小说,不会过时,不会被现实的错乱所消解。小说不是简单罗列现实的离奇故事,最终要回到更深度的人性拷问。
“三个证明”中,最结实的,最打动人心的还是《王固本的活人证明》。这个中篇小说曾入选《小说选刊》,获2017首届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提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让学生先大量阅读《小说选刊》,再从几年内发表的作品中,挑选三篇对自己有触动、有感觉、有表现空间的小说,由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活动总编导赵武最终选出一个片段进行改编和排演。最终参演的十部作品里就有《王固本的活人证明》。
故事的感染力,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除了叙述角度,人物的刻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小说的语言。语言的味道,也可以说是小说的味道。具有沉稳气质的小说家,总是不动声色,把你引向人性的断崖边,让你提心吊胆。我们现实的故事,再怎么曲折、离奇,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熟悉的呈现方式不足以打动我们,或只是展示了社会现象。如王固本的故事似曾听闻,不足为奇,但小说对现实的处理,已将其陌生化,将现实编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一条通往人性的隐秘路径。这样的讲述不再是道听途说的谎言,而是一种可怕的人性的真实。
因此,写这种直面现实的小说,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这条路径最终像现实的倒影,被虚化,被模拟。余华写《兄弟》《第七日》,走的是一条窄门,就是硬碰硬,直面人生,现实主义作品很容易滑向浅白、廉价。
7
小说的气质与小说家的气质有某些相关。李相华的语言有时诗化,有时坚硬。他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是底层小人物,如屠夫,盲流,赤贫者,流浪汉,妓女等,这些人物乖张,粗鄙,卑微,混不吝,油滑,这些人物是社会的底色。李相华的小说,含着悲怆,而不是悲惨,他也不是把现实撕破给你看。他几乎带有一种悲愤在写作,有时看似有一些戏谑化,实则带有强烈的理念。小说的表现高度,跟个人对现实的认知相关。李相华短篇小说有一种很好的识辨度,其语言特色就显得特别明显。
生活中的李相华,是那种言语不多,甚至显得木讷的样子,长得粗壮,也基本不修边幅。酒桌上,他一声不吭,喜欢一饮而尽,除了不错的酒量,就是他有很好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气量,如他结实的身体,似乎可以抵挡一切。
他笔下的孤山道人,研究棋谱、下盲棋的伯考等人物,都能找到李相华本人某些特征。多年前,我就知道他喜欢围棋,但在一个山区小县城,却难以找到对手,我曾想象他拎着围棋,徘徊在孤寂小巷的情景。有一年我被派居乡下,翻山越岭去找他喝酒,那天他正好与人对垒象棋。见我过来,赶紧丢下棋子,安排酒局。对手不悦。为了速战速决,李相华说酒后再战。后来我才发现,为了留住棋友,他常常下的是“让棋”。
这些年,我们见面稀少,李相华在闽南写着小说和诗歌,在当地名声鹊起。他的小说基本都是写故乡里的人和事,这是他的文学根基,这是他的文学地理。
他还是偶尔写诗,想必是在写作小说之余,来一次畅快的呼吸。
(作者:潘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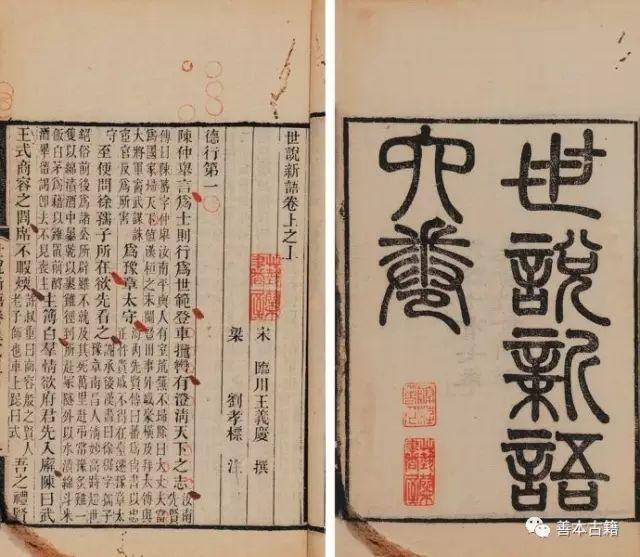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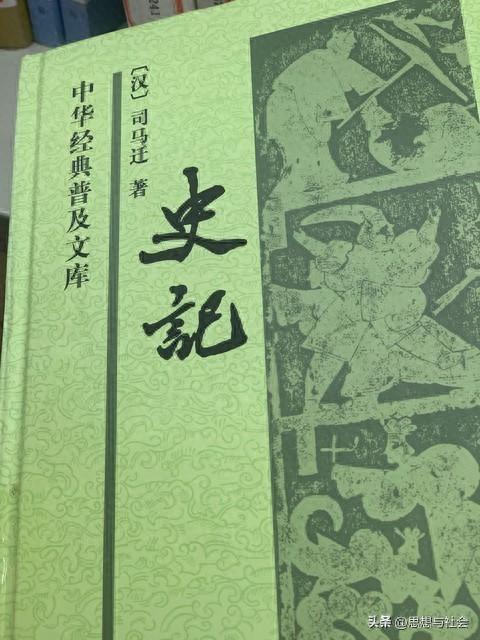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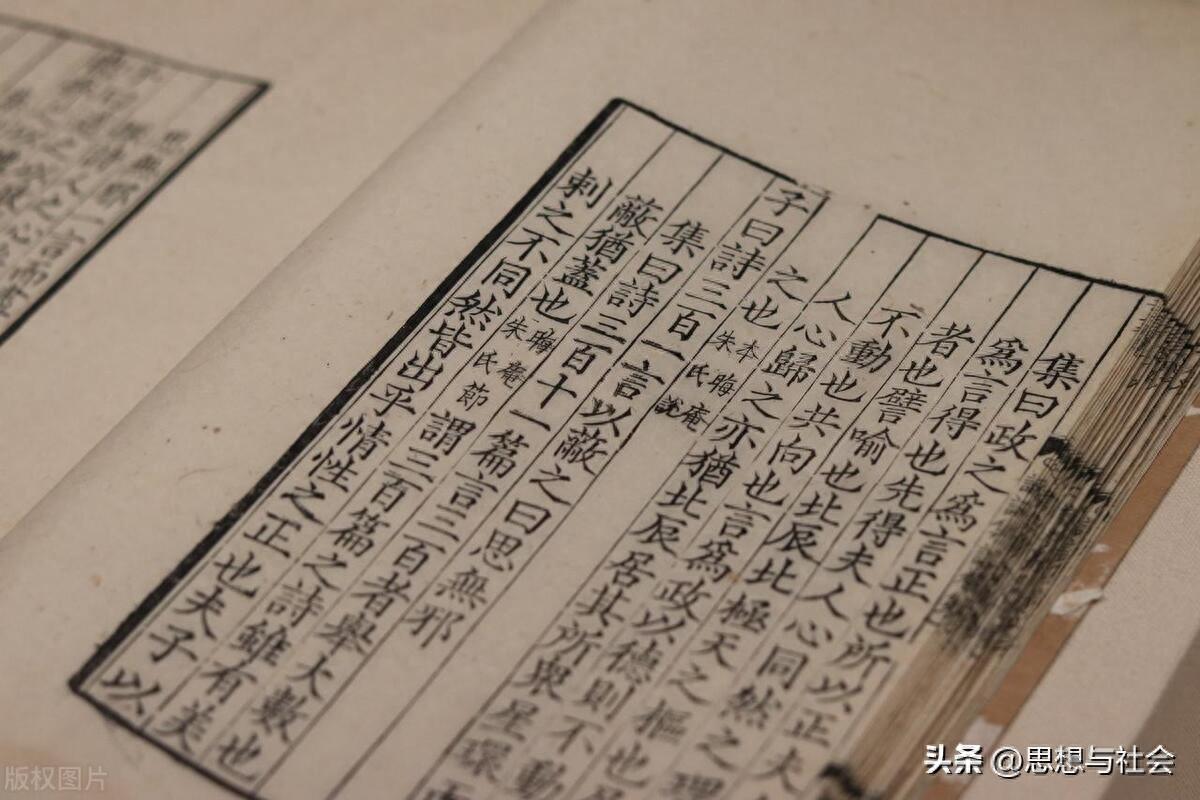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