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她在抗日战争期间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叫《牺牲》。

邓发简历(邓来发工作简历)
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极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去世后,我真的在母亲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确实触目惊心。这部印制粗糙,纸已经发黄的书里展示了70多具装在棺木中的尸体相片。有的是同一个人两张相片,一个生前,一个死后。个别的还龇牙咧嘴,相当惨烈,想当恐怖。
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更别说女人了。等于是在死尸堆里走了一遭,能闻见尸臭和血腥。可以说,任何人看了这部书,都会被震撼,毛发竖立。
何况母亲这么一个多愁善感,富有小资味儿的知识女性。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做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更有怕死的一面。堡垒户王寿云的孩子说:当村里一有狗叫时,杨沫就很紧张,我母亲就安慰杨沫:不要怕,有我就有你,敌人来了咱能对付。
因为她对死极端敏感,所以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中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张家口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
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都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
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至于犯了一场心脏病。
王若飞空难飞机
连根据地的地主也那么忘我,那么爱国!
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别有用心时,他一时冲动,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王汉秋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了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危险、最残酷、最紧张、最艰苦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母亲却说:
多少年过去了,可是,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却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22)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
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内心很压抑。
当时,报社内一些做文字工作的同志都不太安心,觉得这工作没多大出息,不被人重视,不如干群众工作或政权工作,又可深入实际,又受人尊敬。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
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
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跟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打交道,一个炕头睡觉,与农民们耳鬓厮磨,养成了她平易随和,甚至有几分憨厚的气质。让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都有些土里土气。
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毫无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她的同事吕果说:“1949年5月我调到北京市妇联宣教部,为的是创办妇女刊物。因此得以和杨沫共事。起初,我完全没有想到她是文化人,竟以为她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皮肤黑中透红,胖胖的,戴一顶八角帽,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列宁服。大大咧咧,憨厚随和,满口老百姓的京白,用语也不严谨。平易爽朗,很少当时某些干部的那种浓重政治色彩。”
不止吕果,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1949年5月2日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的情绪不高。
母亲对职务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当革命眼看就要胜利,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时,任何人都会随大流参加革命,根本不需要什么觉悟。
谁势力大投靠谁算觉悟吗?这些随大流的,跟母亲那些在革命还很危险,却冒险投身革命的人没法比。
解放后,对那些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待遇上好一点,职务上高一点理所当然。所以母亲对工作安排上的不满,也算不上斤斤计较。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呵斥,让母亲难以忘怀。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订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
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呵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自到妇联宣传部后,母亲似乎被当成一个打杂的,给人抄过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下被服厂了解女工情况……从没有一个固定工作。领导和同事们都认为她动过几次大手术,百病丛生,身上的好零件寥寥无几,也不指望她干多少工作。
母亲对妇联失望了,后悔了,觉得还是搞自己的报社编辑好。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1949年7月因剧烈腹痛,检查出是宫外孕,母亲在市立第三医院动了手术,把子宫、盲肠全都割掉,连右卵巢也割掉。
手术后一段时间,她经常全身疼,还总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她才35岁,就开始秃顶了,所以她常年戴一顶帽子,不管上班还是回家。她照的相片中也大都戴着帽子。
所以,母亲的心绪极坏。不过养病期间,她没闲着,修改好描写抗日战争一段经历的稿子《苇塘纪事》。于1950年7月正式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它的出版给了母亲一丝安慰。
那时还是供给制,每月的钱很少,她连个刷牙缸子都没有,为省钱,特地到东单的集市上买个旧的。
有一次,得了几块钱稿费,把父亲高兴得大笑,竟笑出了眼泪,因为能买点好东西吃了。尽管母亲有公费医疗,很多药还是报销不了,如当时的中药就无法报。她的肝、胃、子宫、关节、眼睛、神经……都有问题,还有一些没搞清楚的病。要彻底治愈,需要自己掏一部分钱。可哪里有钱呢?正忐忑不安时,母亲的妹妹白杨听到了她的情况,热情邀请她到上海治病,一切费用由白杨来解决。
于是,绝望的母亲赶赴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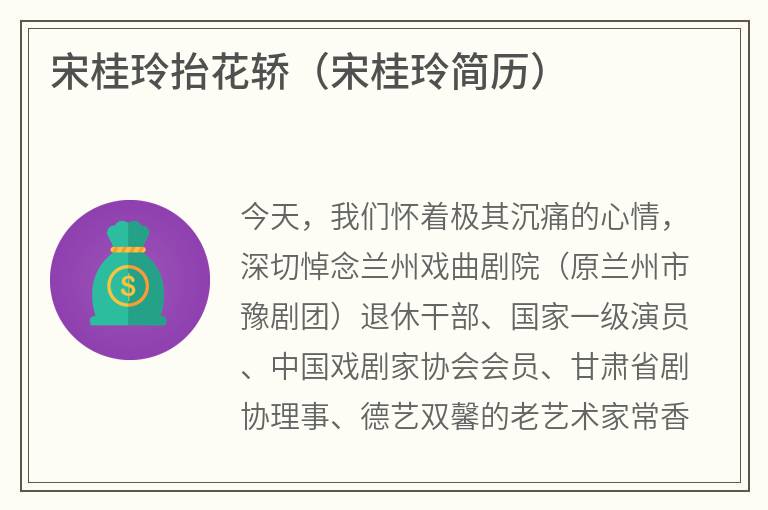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