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史传,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作为文史结合部的中间存在状态,史传文学以独有的双重身份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影响着中国后世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走向。就史传传统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实际关系而言,无论是文体上还是观念上,前者对后者的积极影响与消极束缚、后者对前者的创造性继承与被动性接受是同时存在的。
【关键词】史传传统;中国古典小说;小说文体;小说观念
所谓“史传传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既是指以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作品为主体所呈现出的史传文学传统,具体包括史传文学作品中的文体因素,诸如叙事、结构传统以及题材提供等等方面;同时,也泛指本已存在、而在史传文学的推动、促进下表现得更为强烈的中国人的重史尚实传统、“史贵于文”观念等。就史传传统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实际关系而言,无论是文体上还是观念上,积极影响与消极束缚、创造性继承与被动性接受是同时存在的。但对于这种纽结关系,本文则更多是以文体上的积极、正面影响为着眼点;而对于传统的重史尚实观念,本文更多关注的是其对中国小说观念上的消极、阻滞作用。这将有利于我们看清史传传统与中国小说关系史中的主导方面。
一、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文体的引导
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神话和子书是小说得以发生的车之两轮,史学则是驾着这部车子奔跑的骏马。”①形象而巧妙地说出了小说与神话、子书、史传的关系:从小说发生学着眼,神话和子书的作用相当显著;而从小说长期演变和成熟上看,史传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产生与史传有着更加深刻而直接的血缘关系,史传是孕育中国古典小说的母体。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众多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因其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也因其本身所含有的丰富的、与小说创作息息相通的文学素质,而理所当然地规束着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乃至成熟。
这首先体现在结构形式的有机融合上。史传的结构形式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例,二是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例。编年体例始终以时间为序,将已逝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宏观视角对历史作出连贯的、清晰的记叙。“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以日系事是它的重要特征。”②由于以时间流程作为记事的准绳,就使得作品不可能对某一个人物或事件作出过长的停驻,对人物或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完整的记叙。纪传体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描写,也可以对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当然,整体结构看似松散是纪传体避免不了的缺陷。
中国小说对史传这一传统的继承并不是简单的照搬、挪用,而是在其创作实践中试图将两种结构形式进行有机地融合。这里可以大致归纳出中国古典小说总体上所呈现出的一套相对稳固的结构模式:
(一)以自然时间的推移作为串联作品事件的基本线索
这明显是受到编年体例的深刻影响。古典小说中的绝大多数,开端皆标以明确的时间,情节总是在一丝不苟的时间记录中逐步发展。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来证明我们的发现,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拟话本小说、明清小说几乎篇篇如是。即使是作为萌芽阶段的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虽然内容庞杂,也多采用编年体的记事格式。且不管书中出现的那些纪年成分真实与否,但这种做法却正迎合了国人的“求真心态”,以虚假的真实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二)以历史人物或事件构成作品的中心、骨干
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深刻影响正突出体现在此一点。关于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和环境)孰轻孰重,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家们一直争论不断。本文认为,三要素中哪一个方面最重要并不是关键,也永远不会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关键在于具体的创作实践是否与小说的整体构架相匹配,是否有利于最好地传达作者意图。拿中国古典小说来讲,从唐传奇始,就以人物为核心,而故事的展开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这是因为,中国小说既然在总体构架上采取了史传的编年体例,以时间为经贯穿全文,那么势必要求在叙述过程中以具体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去充填、丰富那已经架构好的时空,通过点(人物)线(时间线索)的结合达到结构上的平衡。
(三)以大团圆结局终止故事的全程叙述
作为史传文学作品,它终归是属于历史著作,实录原则使得史传作家尽量不放过与记叙对象相关的每一个环节。因此,无论是编年体的恢宏叙事,还是纪传体的具体细致描绘,都尽量对人物或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作出最完整的叙述。这一传统显然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得到最广泛的弘扬。作品中每件事必有缘起、有结果,每个人必有来历、有去处。而更为明显的是,小说结尾多以大团圆为结局:行善积德的,会封妻荫子、福分无边;为非作恶的,一定会受到惩罚。这些作品的结局,往往与故事情节或人物性格发展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多是由于作者的一厢情愿创造出来的。因为小说作者真诚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这大概是小说作者追求大团圆结局的一个内在原因吧!
其次,全知视域下的叙述角度变换。全知叙述方式是一种权威叙述,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对于故事中人物的绝对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密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史传文学作品的叙述都是在此种方式下展开,而中国古典小说也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这种方式。
史家作史,是“述往事,思来者”,是为了在归纳、总结前代旧事中找出可以为当代人借鉴的经验教训。因此,面对过往诸事,史传作家总能以后来者的优势、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俯瞰他笔下的人物或事件,这是史传作品中普遍采用全知视角的一大原因。对于史传作品来讲,真实性原则是它的生命,所以在人们“先验”地认同“史传=真实的历史”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全知、全能式的叙述视角反而更增强了作品的可信性,以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使人们接受它。
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来讲,运用全知视角,作者可以从容地把握各类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然而,这样一种权威的叙述视角对于中国小说来讲又是极其危险的,它很可能以使小说作品流于虚妄作为代价。因此,中国古典小说在自觉不自觉采用全知视角的同时,为了加强信实的程度,为了使读者可以暂时忘却世俗、进入“真实”的小说世界,又往往自觉地通过视角的不断切换来淡化全知叙事的人为性痕迹。比如《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进荣国府一节,作者首先通过黛玉的眼睛看到宁、荣二府的豪门气象,贾母和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的装束和容貌;接着,视角移入众人,描写众人眼中的黛玉;然后又回到黛玉的位置,现出王熙凤和贾宝玉的风采。在这里,作家似乎已经隐退,他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故事中的角色,各个角色在表演着自己的同时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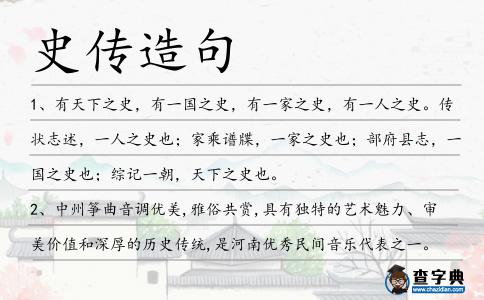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