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千万别拿现在的伪书和汉代的伪书比,汉人作伪至少也还有点政治诉求,有点理想,而且大多水平不低,今天的伪书就是骗钱。虽然伪托并不高尚,但假如写得好,还是可以将功补过的,一些伪托的书还泽被深远呢,譬如《黄帝内经》。
最终对得起读者的是文字本身,而不应该是名字。这种荒诞之所以可能,跟世间有众多李鬼没太大关系,因为李鬼再多,没有编辑和出版机构的允许,是不可能出版的。金庸新只有三分错,那个编辑应该担七分。
向珂(新星出版社“大端”文库编辑):任何一本畅销书都会带动同类产品的密集出现。跟风之作如果也像原作那样立论有据,启人智慧,这股风潮便清新可喜。但如果是一部多由百度百科内容凑成的东西(我不忍称之为“书”),还如此高调,读者响应,那监管部门不能再仅仅盯着黄赌毒了。
这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匆匆编书,精耕营销,编辑也就变得可有可无。刚刚入道的图书编辑,见此光景,不容易把持住,一则自甘降身为臣妾,一则仓皇出逃。长此以往,图书业成为低端的广告业。
杨硕: 我们可以轻易地把伪书的不断涌现归因于无良书商对规则的不断蔑视,但蔑视的背后呢?是缺乏制约,是维权之难,在一个法律形同虚设的地方,山寨就会肆意横行,不只是在出版业,也不管是其背后的目的为何(商业的、政治的)。唯一能起到制约作用的恐怕还是行业自律,有良的出版业同人集体发声,在媒体上公开表明自己对于此类伪书的看法。
其实,伪书一定程度上也是出版不自由的表征,试想,在一个出版自由的地方,选题几乎是完全开放的,有那么多好书可以做,为什么非要冒风险出一本伪书呢?
李闯:图书都来自于作者出于某种目的的创作,所以很多时候荒谬的不是书或者作者,而是某个时代。好在图书的生命周期比报纸、广播、电视、期刊都要长很多,书可以传世。所以编辑能做的,就是细致耐心地把当代思想以出版的形式留给后代。即便这些思想在后人看来简单幼稚,但实际上他们所立足的高度建基于我们今天的努力。
建立做书的抗恶纺线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能给编辑多大发展空间?
新京报:书评周刊做一个专题,“抗恶的防线”,这个观念适用于很多事情。在做书这一行,当代存在一个抗恶的、抵御无良与荒谬的有力防线吗?或者说,这样的防线要如何建立起来?

“金庸新”的作品《九阴九阳》,读者质疑其利用了金庸之名。书封上的作者标注疑似在“金庸”和“新著”中间有空格。
李闯:在工作中我们会用编校的差错率、内容的重复率作为学术出版的最低标准,比如重复率超过15%的算作抄袭,或者差错率超过0.008%就算不合格。我们需要这种客观的出版标准,也需要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奖惩。但我个人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工作,在于天分、勤奋和机缘;编辑的操作空间非常大,所以书能做成什么样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而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另外,关于“恶”的定位,让我想到有次和一个青年学者聊“烂书”。他说“烂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坏书”。“烂”是你一眼就能辨别出其“不可读”的,但“坏”可能以某种良善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毒害的是思想。建立某种“防线”可能是历史性的任务,而不是当代就可以完成的——当然,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某种目标,指引我们的日常工作和阅读。
向珂:做书这个行业只是国内所有行业中极为微小的一个板块。餐饮业有地沟油,这里有所谓的“伪书”。据说,地沟油的问题由监管部门的努力有所改善,那么,监管依然可以出现在出版行业,光鼓励大家读《弟子规》来提高道德觉悟,多少不靠谱。当然,图书业从业者的收入普遍偏低,急于改变生活状况,也就盼着出奇以制胜。如何建立防线?也不能呼吁全社会向广大图书编辑发起扶贫募捐吧?
王重阳:何怀宏老师多年前不就提出“底线伦理”吗?这是我感到特别悲哀的事情。尤其是今天的出版行,面对的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局面。
首先是一些出版社把图书出版变成传销,把图书变成迎合人性缺陷的自慰产品,采取譬如买榜、雇佣水军、给平台返点、虚假宣传等手段,于是心灵鸡汤、成功学、励志学、情色暴力都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了。作为一个名门正派的大社编辑,眼睁睁地看着一些烂书天天占据网店首页,我真的觉得很沮丧。
沮丧的不是因为好书卖不过烂书,而是因为很多国人因长期受误导,都不知道什么是好书了。你想想,80-90年代初的时候,引领畅销书风头的是海德格尔、李泽厚、刘小枫、路遥、三毛这些人,过了二十年就成了韩寒、郭敬明、于丹了。你说大众的阅读品味是怎么回事了?其次,出版机构、图书媒体、读者群整个都处在一个酱缸里,没有完成真正的分化。
国外,学术书和通俗读物之间,纯小说和流行小说之间,出版社不同,发布和推广的媒体也不同,读者群更不同。可是国内呢,一个书评版会把于丹和王国维放在一起,一个图书促销活动会把余华、苏童跟青春作家放在一个台上。归根结底,对于利益的追逐,就把本来应该有的分层给打乱了。
作为编辑而言,现阶段必须忍受这种失落,否则就转行呗。要想发财、成名、走向人生巅峰,做一个好书的编辑是很难实现的。但那些真正靠做烂书、伪书、粉丝书而发财的编辑,要记住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要想比富,你得做多少本烂书,才能实现王健林那1个亿的小目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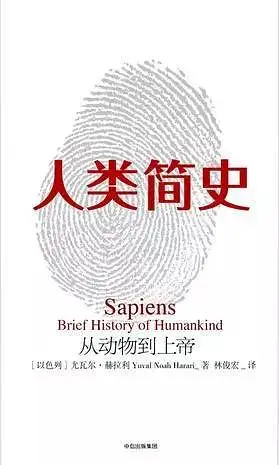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作者: [以] 尤瓦尔·赫拉利 译者: 林俊宏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7年2月《人类简史》成为畅销书,让尤瓦尔·赫拉利一举成名。
挑战重重的做书年代“你不推,怎么就知道墙不会倒呢?”
新京报:葛红兵曾在《我们身处‘伪书时代’》一文里谈到另一种伪书的伤害:“这对读者是一种蒙骗,对作者是一种羞辱,对原作是一种冒犯,是对真相、对历史的犯罪。”我们这个时代,作者和编辑能够交到读者手中的书可能是“不完整”的,很多原因会导致内容删减,编辑如何理解和应对看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伪书”?
李闯:葛所谓“伪书”,是经过删减而成为另一个版本(洁本、删减本),但这不代表书是杜撰的、假的。“无良删减”是审查制度层面的问题,老编辑会教育我们:学术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就是说学者可以思想无界,但编辑要在国家制度下对读者和社会负责。
我觉得如果把一些问题都归结为体制性的,似乎不是一种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可以采用很多灵活的方式加以处理,比如以编者注的形式说明本书有删节,或者某些词汇已经被统一替换为符合出版规范的其他词等。
杨硕:在目前这样的社会状况面前,一个有志的做书人不仅要能裹腹,还要勇于去打破边界——出版的边界、认知的边界,去启蒙,当然有风险,可是你不推,怎么就知道墙不会倒呢?做书人的痛苦也在这里,一部好好的书经过多次审校之后被删改的不成样子,在骂娘的同时也开始怀疑做书的意义了。

并非所有的编辑工作都能像《天才捕手》(2016)中那样获得成功。
新京报:在这条路上,在这个时代,做书人最大的困惑、痛苦或者安慰是什么?
王重阳:困惑之一是上面提到的无序,就是出版行本来跟其他行业一样都是分层的,如同有很多园子,有的园子养的是鹿,有的园子养的是猪,现在的局面就是猪都跑到鹿的园子里来了,猪脑袋上插了两根树枝,也说自己是鹿。
困惑之二是目前出版界的二元体制。国有的出版社,大多机制僵化、反应缓慢、文化沉闷,但对于图书品质和社会影响还有所顾忌,而民营机构则大多与之相反,机制灵活,但唯利是图。编辑真正的职责难以在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完全发挥。
至于安慰,那就是还总是能看到有同志和自己一样在坚守,而不屈从俗流。单说做书这行,三联还在,商务的汉译名著还在扩充,剩下的大社只要碰上一个“有梦想的领导”,五年之内会有小成,十年之内就成了品牌,就像当年的辽宁教育、河北教育、山东画报,今天的理想国、甲骨文等等。
李闯:我的困惑是,我是不是真的忠实于作者的写作,同时又使其符合出版规范。我的痛苦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很差的稿子因为各种原因从自己手上溜走、出版,而自己无能为力。我的安慰是,认真写作、阅读和工作的人,他们的生活因为有书而变得有趣精彩。
结尾的话:编辑眼中的好书是怎样的?
向柯:“《牛津英语大词典》。这是一部永远都写不完的书。1857年,语言学会的专家们建议系统考察他们的语言。收集资料的工作便由此开始,22年后,一位名叫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的编辑才开启了这项图书编撰大工程。一百多年来,它的内容在不断更新,形成了大IP,又有了一系列的衍生产品,也包括我们熟悉的《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对于这种事儿,造伪书的只会嗤之以鼻:账上回款,月月一算,如何敢想一百年!” 李闯:“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豆瓣页面下,编辑这样写道:“(今天)我把最后的清样交给了出版部的同事,历时五年,这本书终于可以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了;感觉有些复杂:既有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轻松感,又有某种忐忑,觉得如此重要的著作,其实值得进一步推敲、打磨。策划、编辑这本大部头,对我而言真可称得上是一次冒险。”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