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邢星星
新历史演义小说文体的生成
——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一)
李遇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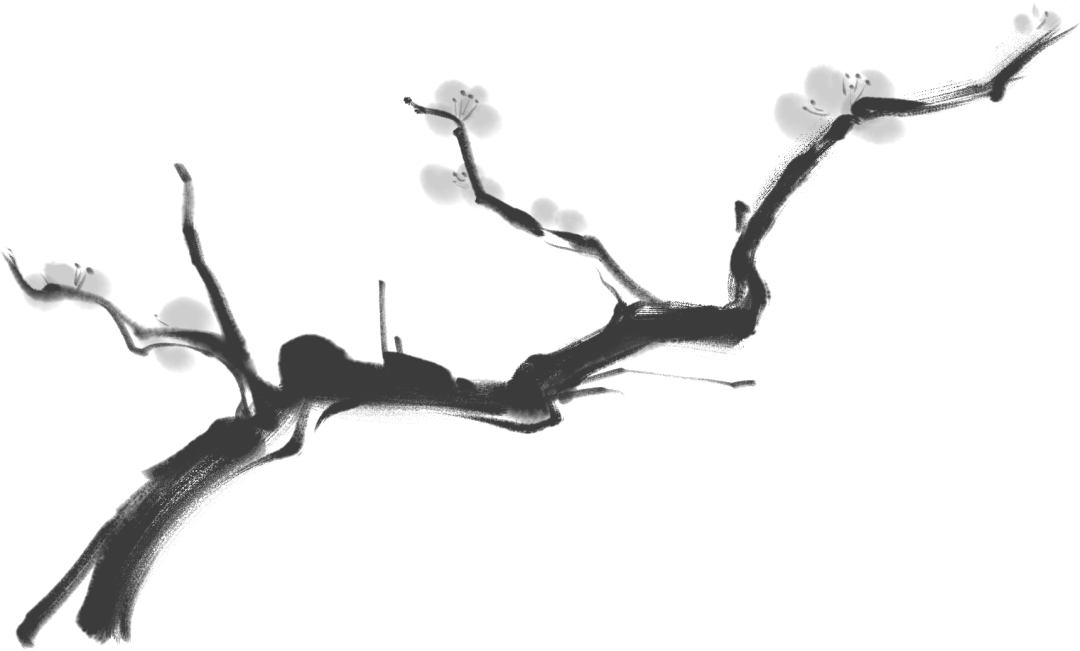
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系列中,《山本》无疑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作品。不仅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体量大,多达五十万字,超过其体量的唯有《古炉》,更重要的是,《山本》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单独书写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中国史的长篇小说,虽然此前《老生》也写过秦岭游击队的历史,但仅是《老生》的四个叙事单元之一,其余三个单元都是写新中国史的。这意味着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已走在从现实题材向历史题材掘进的广阔道路上。作为巍峨屹立、蜿蜒曲折的文学山脉,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系列正如同他笔下横亘在中华广袤大地上的秦岭一样,既有北方的豪壮又有南方的灵秀,既有现实的广度也有历史的深度,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文学所能抵达的艺术高度。但《山本》似乎有些生不逢时,这部不仅在陕西文坛而且也在中国文坛上能与陈忠实的《白鹿原》相颉颃的长篇力作,面世后毁誉参半,甚至一度出现了激烈的否定声音。事实上,贾平凹在创作之初并非没有顾虑,但他还是怀着谨慎的善意与乐观,期待文学解人的出现。“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与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1 这看似幽默,其实隐含了贾平凹低调的自信。问题是,贾平凹的这种艺术自信从何而来,他究竟在《山本》中想要表达什么,又是如何表达的?在我看来,贾平凹在《山本》中试图创造一种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文体新形态,换句话说,他想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小说叙事传统,以民族化风格传达现代性忧思。所以他在写作《山本》的过程中,室中左边挂的条幅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2,这是提醒自己既要吸纳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资源,也要防止坠入中国传统文人大多思想境界不高的陷阱,借此实现中西文学与思想的艺术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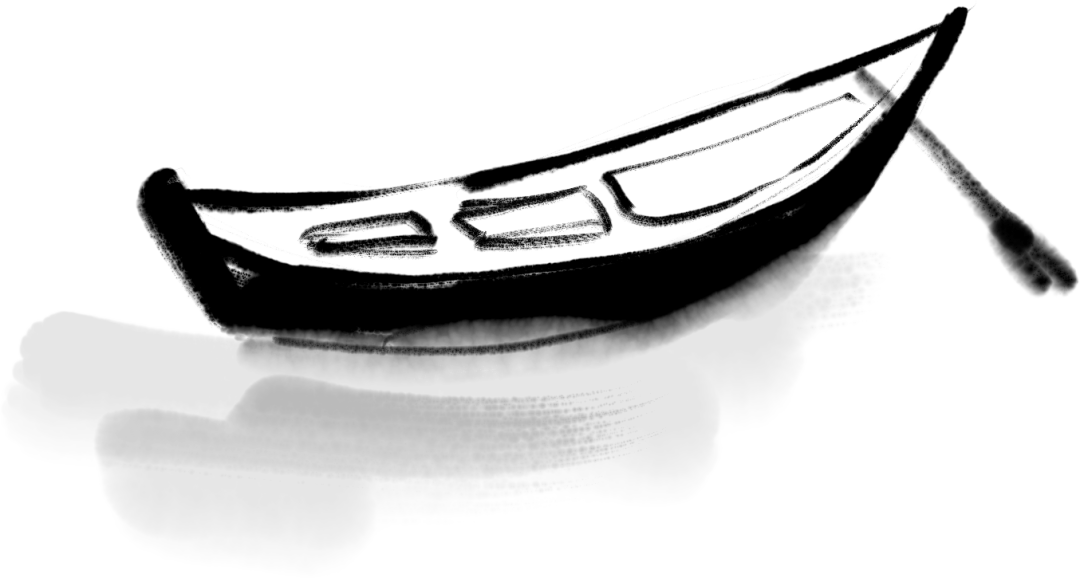
一
熟悉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潮流的读者一看便知,《山本》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小说文本。所谓新历史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大体上是一个与革命历史小说相对应的概念。一般而言,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历史故事,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小说就是如此。但也有偶尔突破新民主主义革命范围的红色经典作品,比如李六如的三卷本《六十年的变迁》就将叙事时间范围上溯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清末辛亥革命一直写到新中国建立,可惜第三卷未能终篇。而新历史小说则是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原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形态的改写或重构,它所涉及的叙事历史时段大体涵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与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新历史小说不再执着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不再执着于战争史或军事史的文学书写范式,而将叙事立场确立为民间本位,将叙事主干由战争史或军事史拓展至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风俗史以及日常生活。由此,新历史小说实现了对旧中国史的整体性重构或改写,让读者体察到了与新中国史不一样的历史书写,也领略到了与革命历史小说不一样的叙事魅力。对于贾平凹这样一位长期执着于讲述新中国史或新中国故事的大作家而言,追溯起来,在他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讲述旧中国史或旧中国故事的作品并不多见,除了长篇近作《老生》部分涉及旧中国史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土匪题材中篇小说系列了。事实上,那本以《逛山》命名的中篇小说合集给我们谈论的这部长篇力作《山本》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至少可以说,早在三十年前贾平凹就已经埋下了创作《山本》的艺术伏笔,因为在《山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山地土匪故事。但《山本》毕竟不是一部土匪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不是对早年的《逛山》的简单扩大或改写,因为这部长篇巨著中涉及的秦岭各种社会力量或社会群体实在过于庞杂,除了不同类型的土匪群体之外,还包括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同群体、绅商内部的不同群体、乡民内部的不同群体等,这就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题材类型小说范围,而深入到了立体地重构旧中国史的小说艺术境界。
然而,让秦岭的历史进入文学,这对于贾平凹而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在《山本》后记中说自己在数年里陆续去过秦岭起脉的昆仑山,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去过太白山和华山以及其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他的文学原乡“商州”(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最初他去的目的是收集和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和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原因未能完成,但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料到这期间他收集到了秦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诸多传奇故事。“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3面对如此庞杂混乱的秦岭历史素材,贾平凹感觉自己就像一头企图追捕兔子的狮子,眼看着兔子钻进了历史的荆棘藤蔓中却无计可施。终于有一天他从老庄的比较中意识到,虽然自己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但那堆历史其实也面对着他,他“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4。这意味着贾平凹从庄子的“天我合一”美学而不是老子的“天人合一”哲学中获取了新历史小说叙事灵感,无疑也暗合了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和解构主义元史学的精神旨趣。
所以贾平凹才会这样说:“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儿是碑上的文字哪儿是虫子和苔藓。”5 这就形象地揭示了历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给作者以“天我合一”的方式重构秦岭大历史提供了艺术合法性。但“天我合一”毕竟不是“以我为主”,“以我为主”容易陷入“我注六经”的主观主义泥淖,“天我合一”强调的是“我”与“天”之间的主体间性或对话机制。显然,贾平凹在《山本》的创作中并未落入诸多新历史小说习惯性陷落的戏说历史窠臼,他在构思和写作中格外重视历史素材的搜集与消化,尤其强调创作主体(“我”)与历史主体(“天”)之间的平等对话,由此恪守了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主义底线,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避免了主观宰制和随意切割历史的反历史主义行为,因为“改写历史和艺术虚构完全是两回事。艺术虚构是必要的,而改写历史却是要不得的,是反历史主义的”6。对于贾平凹而言,要想真实地写出秦岭的历史,不是说要反对虚构,而是要处理好历史素材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写出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实性,让历史的隐秘真相或本相自动敞开,这就是《山本》命名的由来。
那么问题在于,一个作家究竟该如何处理历史素材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叙事传统中,在这个问题上大体形成了两种历史演义处理模式:一种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七实三虚”处理模式,即大部分遵从既有的正统历史叙述,如《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相关历史记载,只有少部分由小说家来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虚构。再一种则恰好相反,就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三实七虚”处理模式,即少部分得自既有的历史叙述,且正史和野史相混合,如《宋史》《宋江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等,而大部分则由小说家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虚构。关于前一种演义模式,鲁迅指出:“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组》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7 显然,鲁迅对这种“实过于虚”的处理模式给予了讥评。而关于后一种演义模式,茅盾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水浒传》“不是严格的或正宗的历史小说”,因其“历史性只在于史有其人、史有其事”8 而已。言下之意是不赞成这种“虚过于实”的历史与文学(虚构)处理模式。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究竟哪一种处理模式更好,因为二者都取得了令后世仰望的艺术成就,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小说叙事典范。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大体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家大都遵从《三国演义》那种历史演义模式写作,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和唐浩明的“清吏系列”都是如此,偏重于历史的实,而以文学的虚为辅。而在新历史小说家笔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则有意无意或显或隐地传承了《水浒传》那种历史演义叙事传统。虽然这些作家在写作前也做足了历史功课,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则以文学之虚凌驾于历史之实。显然,贾平凹的《山本》属于后一种历史演义一脉。当然,并非所有的新历史小说都是新历史演义小说,只有那种带有历史演义文体特征的新历史小说才能划入“新历史演义小说”范畴。比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李锐的《旧址》、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这类常常被人划归为新历史小说的小长篇,它们从文体上看显然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关系不大,而且大多明显带有外国现代派或后现代小说叙述游戏的痕迹,所以并不属于我们所谓的新历史演义小说文体形态。而《山本》与《白鹿原》《丰乳肥臀》《伪满洲国》《圣天门口》这类新历史小说巨著则不同,虽然它们有的也被贴上了被外国小说流派,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之类影响的标签,但总体而言,它们更能显示出世纪转型之交中国小说的中国气派来。而这种中国气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演义体”传统的发扬,尤其是《水浒传》那种泛历史演义文体传统的滋养。
显然,在贾平凹众多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唯有《山本》具有历史演义特质。据贾平凹自己说,这部长篇小说最初题名《秦岭》,后来为了避免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秦腔》重复,改名《秦岭志》,再后来又嫌命名读起来不够响亮,最终定名《山本》。在我看来,三个名称中,《秦岭志》最能传达中国古典历史演义体小说的文体特征。它很容易唤醒中国读者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等民族历史文学经典的集体记忆。事实上,贾平凹确实在搜集秦岭历史素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遗憾的是我们一时还无法知道贾平凹究竟掌握了哪些第一手的秦岭历史素材。这就决定了我们一时还无法做出严格的《山本》本事考证。但陈思和先生还是慧眼独具,他敏锐地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山本》的“本事”来源——历史本事正是历史演义和历史虚构的基础。按照陈思和的初步考证,《山本》的历史故事主要来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史,这在整体上站得住脚,但中间也夹杂了历史疑点,体现了民间说史无时间感的叙事特点。具体来说,小说中写到了冯玉祥部在中原向红军大举发动进攻,红军分三路突围,一路进了秦岭,秦岭特委指示游击队一方面与冯部周旋,另一方面还要护送一位重病的首长通过秦岭去陕北延安。陈思和认为这里的历史背景描写有不尽合史实之处,因为冯玉祥与蒋介石在 20年代末联合反共不假,但那时反共主要是清党,还不是大规模作战,此其一。
其二,冯玉祥在中原发动战争主要是与奉系军阀及河南当地军阀作战,不存在与红军的中原部队作战。其三,写游击队护送首长去延安,只可能发生在抗战以后——在 20 年代末红军既不可能有中原部队也不可能有延安根据地。但陈思和同时又指出:“1927 年是红军草创时期,小说写到阮天保与井宗秀分裂,从保安队倒戈为红军,可能是影射 1927 年 10 月共产党人唐东源、李象九、谢子长等利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发动清涧起义,分裂了井岳秀部队,创建陕北红军的历史事件。红军与冯玉祥的军事交锋应该是在 1928 年 6 月,冯玉祥以三个师的兵力围剿唐东源、刘志丹等人创建的工农革命军,革命军失败后,有一路军队进入商洛山区,与当地零星的游击武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小说里蔡一风、井宗丞领导的游击队。”9 不难看出,如果将小说中的平原游击队置换成陕北工农革命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显然,贾平凹在《山本》中将史实中冯玉祥部与陕北红军的战争改写或置换成了小说中与平原游击队的战争,也就是说,小说中关于平原游击队的历史演义正来源于陕北红军的历史本事。至于为何不明写这段历史本事,答案也并非不可理解,无非是因为那段历史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贾平凹在叙事中会不经意地留下叙事破绽,即陈思和质疑的秦岭游击队护送首长去延安不符合史实的问题——因为贾平凹的历史本事确实就是来自陕北红军史,小说中置换成平原游击队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故而一念间出现了小说中根本不必出现的地名延安——即使要出现也可以换成“平原”或“中原”的某地即可。
除了发现《山本》中的“本事”大体是真事外,陈思和先生还初步证实了《山本》中的“本人”大体是真人。按照陈思和的说法,《山本》中最重要的人物原型是陕北军阀井岳秀。只不过小说不是实写而是虚写,贾平凹根据井岳秀的生活原型塑造了井宗丞、井宗秀两个人物,以此为井氏兄弟树碑立传10 。这个说法似可商榷,为井氏兄弟树碑立传不假,但兄弟俩的生活原型都来自井岳秀则不那么合情理。更为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根据历史上的井家兄弟故事塑造了小说中的井家兄弟形象。陈思和文中将历史上的井家兄弟误记为哥哥井勿幕、弟弟井岳秀,其实井岳秀(1878—1936)才是兄长,井勿幕(1888—1918)乃胞弟。井勿幕早年在外进新式学堂,后参加中国同盟会,为陕西辛亥革命先驱,曾被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可惜三十一岁时因在陕西参加反北洋军阀的战争而被人暗杀。井勿幕的生平与《山本》中的哥哥井宗丞的经历暗合,都是在外求学参加革命,只不过史实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被置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于被人暗杀的结局则与史实高度一致。历史上井勿幕死后,井岳秀为弟弟报仇,曾将革命叛徒李栋材活捉归案,对其施加砍头挖心、剥皮抽筋等酷刑,祭于亡弟灵前。他甚至还将仇人的人皮制作成马鞍,整天骑于胯下解恨。
这在《山本》中也被移植到了井家兄弟的复仇故事中。小说中写井宗秀派人捉拿凶手邢瞎子,施加挖眼凌迟等酷刑祭奠亡兄,至于剥皮则移植到了另一个叛徒三猫的身上,井宗秀下令用奸细的人皮做成人皮鼓挂在城楼上警示众人。如果说井宗丞的原型是井勿幕,多少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井宗秀的原型是井岳秀的事实,则十分明显。历史上的井岳秀被称为“榆林王”,在领导榆林地区经济建设、维护统一等方面政绩卓著。虽然在政治上井岳秀不如胞弟井勿幕有正声,但陕北军阀井岳秀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至今,陕北榆林地区还流传着井岳秀的种种野史杂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1992 年陕西省榆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发行的《井岳秀传奇》,此书署名李云峰著,系章回体长篇小说,共计二十五回,有回目,有绣像插图,可供评书演播之用。历史上的井岳秀擅长骑马,治理榆林二十年间每天晚上都骑马巡查,这一点在《山本》中也被作为井宗秀的标志行为多次刻画。历史上井岳秀之死充满传奇性,一说死于偶然,说他看家眷打牌时起身坠枪走火,命中要害而死;另一说死于必然,说是被共产党指使刺客暗中枪击身亡。《山本》取后一说,暗示其是被红军团长阮天保指使人行刺而死的。但小说中也综合了第一说的场景,即死前他确实在宅中看妻子和戏子打牌。
从以上简略的文史互证中不难发现,《山本》所讲述的历史故事确实有着比较坚实的历史基础。尽管我们无法判明贾平凹具体依据了哪些正史或野史来展开他的秦岭历史演义,但得出贾平凹在《山本》的创作中实际上是在演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段秦岭历史这一结论,应该是完全可以的。按照茅盾讨论历史与历史文学的关系时提出的四种思路,即“真人真事”“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和“人事两假”11 来看,《山本》中的“真人真事”所占比例其实并不低,但由于作者采用了“真人隐去、真事留下”的做法,除了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等历史人物采用真名外,绝大部分小说人物都采用了“假名”或“化名”,就给这部历史小说披上了神秘的文学面纱,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部作品的历史演义小说本质。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小说中关于井宗秀的事大体上属于真人真事范畴,但其中必然隐含了“真人假事”,即根据井宗秀的性格而虚构的故事。至于“假人真事”或“人事两假”,即把真实的历史素材安插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或者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虚构某个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及其故事,这在《山本》的创作中更为常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本》的创作更接近《水浒传》那种“虚过于实”的历史演义模式,即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人物来自作者合乎历史条件的虚构和想象,只有少数重要人物形象有比较可靠的历史原型做基础。这就与《三国演义》那种“实过于虚”的历史演义模式区别开来了。当然这仅仅是就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虚实关系而言所做的判断,如果换成其他角度,比如从单体型或拼贴型的叙事结构比较而言,显然《山本》更接近《三国演义》而不是《水浒传》,因为前者叙事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显然高于后者。但无论接近哪一种历史演义体,都无法改变《山本》的新历史演义小说的内在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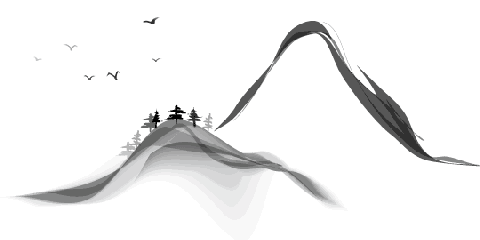
注释:
1.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页。
2.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6页。
3.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页。
4.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页。
5.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页。
6.庄浩然、倪宗武选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戏剧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8.茅盾:《茅盾文学评论集》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4页。
9.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见《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春卷,第289页。
10.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见《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春卷,第289页。此段中关于井宗秀与井岳秀之间的文史互证借鉴了陈思和先生的相关成果,略有修正和补充。
11.庄浩然、倪宗武选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戏剧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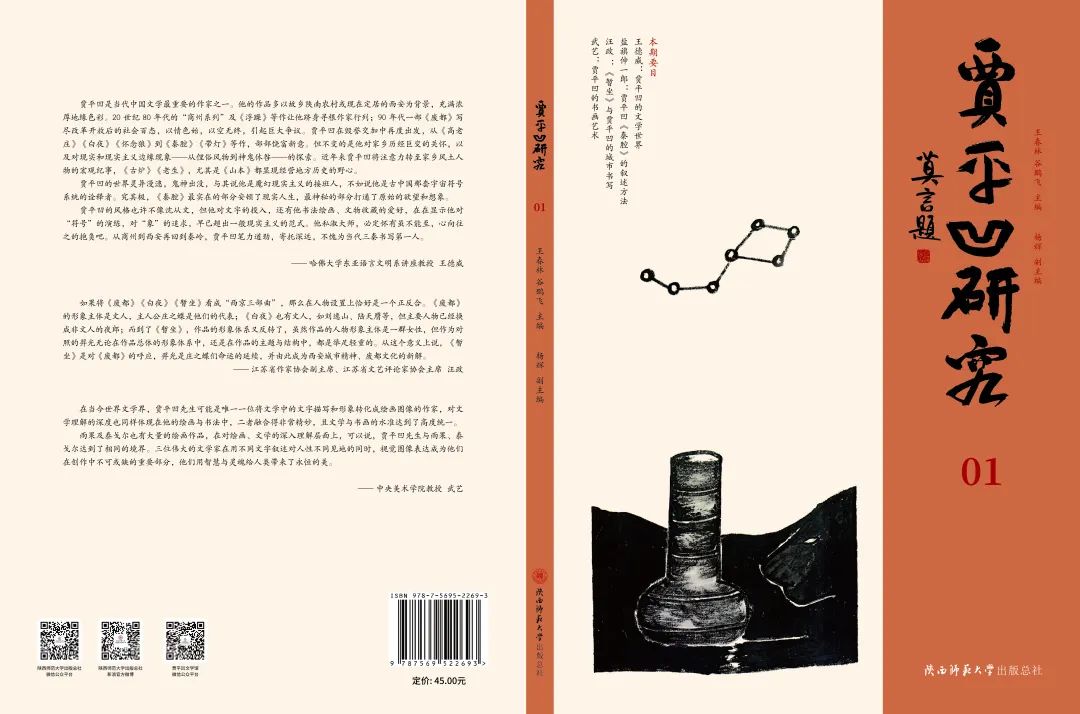
本文刊于《贾平凹研究》2021年第1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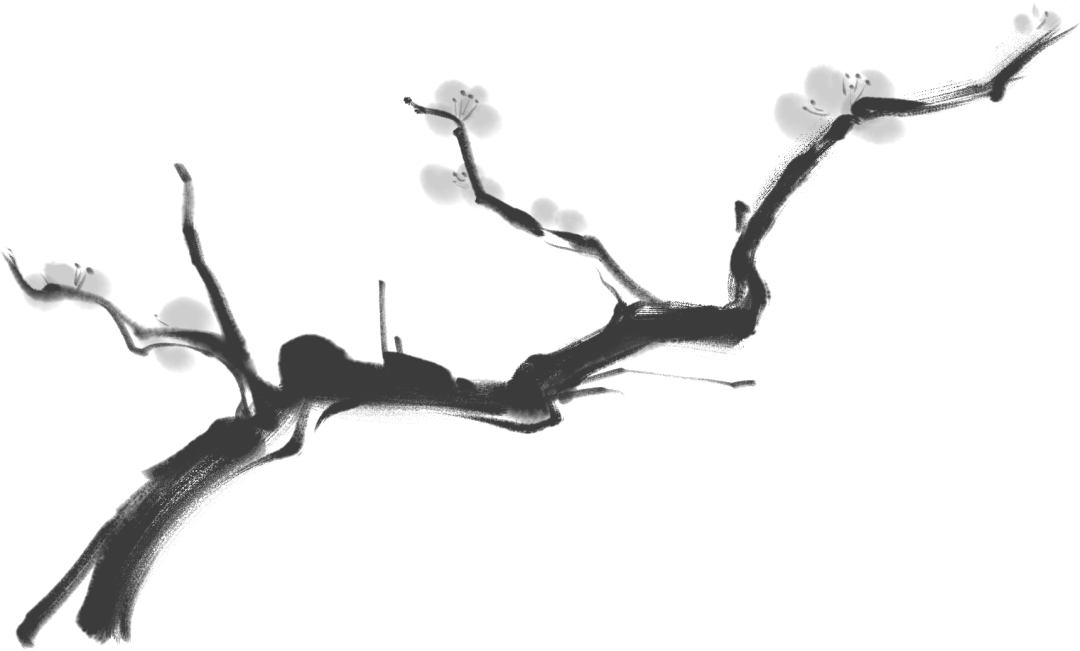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