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刘丹

新历史演义小说文体的生成
——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四)
李遇春


四
从人物形象角度考察,《山本》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众所周知,贾平凹从《废都》开始明确借鉴《金瓶梅》《红楼梦》的艺术资源,其中就包括借鉴两部古典文学名著的人物群像塑造经验,并将这种艺术经验从塑造古典贵族人物形象转化为塑造当代平民人物形象,《秦腔》就是这种艺术经验转化的卓越代表。而《山本》作为贾平凹的第一部新历史演义小说,它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再是贾平凹多年来擅长的当代平民人物形象,而主要是革命年代旧中国的各色传奇人物,这里面有枭雄、英雄和奸雄,有土匪、政客和商人,还有种种神秘的世外高人,当然也有旧中国的众多底层平民百姓。在这种情况下,贾平凹不可能不做出相应的艺术选择与调整。如前所说,贾平凹此时转向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古典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主动从中去寻找现代转化的传统资源,由此改变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风格——由原先师法《红楼梦》《金瓶梅》所形成的阴柔之风,转向了取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的雄健气魄,准确地说,是两种艺术风格的兼容与杂糅,借用古人评杜诗的说法,谓之“沉郁顿挫”,庶几近之。显然,这种文学传统取向的变化,对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而言,其意义不容低估,它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贾平凹日后新的文学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当贾平凹转向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小说,复古开新的时候,他再次选择了效法那种人物群像结构的历史演义小说传统,至少在主观上他有意识地回避了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中心人物结构模式,这显然与他长期以来效仿古典世情或人情小说过程中热衷于《红楼梦》那种人物群像结构所形成的散点透视审美习惯有关。对于贾平凹而言,以《说岳全传》为代表的那种在中国民间高度流行的历史演义小说,其中心主义人物结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演义小说中实在过于常见,乃至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了“三突出”新英雄人物塑造指南,这自然无法适应当代中国新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在世纪末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潮流中,以《亮剑》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演义作品再度落入中心主义人物塑造成规。这就更加促使有艺术使命感的作家积极向多中心或反中心主义的人物群像结构方法汲取艺术资源。这种人物群像结构方法中隐含着一种法国理论家德勒兹所谓的“块茎状思维”,它不同于中心主义的“树状思维”,而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思维方法,由此形成的“块茎状文本”自然也就不同于“树状文本”。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所谓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超越,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思想传统高度契合。而这种融通中西的返古开新,正是贾平凹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艺术方略。于是我们看到,在《山本》的创作中贾平凹以“块茎状思维”构思和设计人物群像结构,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美学雕刻人物群像,从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如果粗略地分类,我们可以把《山本》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划分为若干系列:一是军人土匪系列,其中又可分为红军(游击队)系列、国民党军(保安队、预备团或预备旅)系列和土匪系列。红军(游击队)系列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形象有井宗丞、蔡一风、宋斌、夏开轩、米家成、杜英、范哈子(叛变)、程国良、许文印、李得旺、王三田(叛变)、蔡太运、程育红、周瑞政、薛宝宝(叛变)、白秀芝、黄三七、元小四、张福全等,不局限于纯粹的军人,也包含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地方领导人形象。国民党军系列中,属于保安队的主要有阮天保(先投预备团,后投游击队)、史三海、邢瞎子(投游击队,又叛逃)等,属于预备团(旅)的主要有井宗秀(以酱笋坊掌柜起家)、杜鲁成、周一山、杨钟(离开)、冉双全(叛逃)、李文成、王成进(西北军第 6 军下派)、陈来祥、郑蚯蚓、巩百林、赖筐子、马岱、唐景、唐建、三猫(叛变)、陆林、张双河、苟发明等,另外还包括麻县长、刘必达、尹品三、李克服、梁伍、王喜儒、白仁华等国民党不同派系的大小地方官吏形象。土匪系列形象中主要包括牛文治、林豹、五雷、王魁、玉米、崔天凯(投韩掌柜)、夜线子(投预备团)、梁广、曹地、罗树森、瓜子老大、璩水来(原县警察局局长)等。
二是绅商地主系列,其中绅商系列主要有陆菊人(茶总领)、杨掌柜、井掌柜(伯元)、吴掌柜、岳掌柜(附姨太太)、韩掌柜、李掌柜、崔掌柜、陈皮匠、方瑞义等,地主系列主要有程茂雨、柴广轩、高云干,红军游击队攻打的许多秦岭地区无名富户也都包括在内,部分属于恶霸地主。三是民人系列,即平民百姓人物系列,主要有涡镇民人系列,如老魏头、阮船公、白起、柳嫂、五魁、刘老庚、刘花生、白氏父女、剩剩、吴妈、阮上灶、赵屠户、孙举来等。其他秦岭民人系列,有如孟星坡父女、张栓劳、张老仓、黄伯项、钱老大、烧窑师傅、任老爷子、严松、女戏子等。四是高人系列,即民间世外高人形象,主要是陈先生和宽展师父,至于陆菊人、麻县长、杨掌柜、杨钟、周一山,他们这几个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方面的某些精神特点。不难分辨,这是一个堪称庞大的小说人物形象群体,有名有姓的就有一百多人。这些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群体之间有交叉组合或者移动换位的现象,充分说明了革命年代秦岭历史的复杂性。《山本》的作者就如同文学界的一个高级农艺师,精心地创造着一切艺术条件,让这百来号人物自由自在地在文本“块茎状结构”的土壤中各自野蛮生长。当然,正如自然界的阳光雨露也不可能赋予每个生命以完全同等的造物福利一样,《山本》中的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获得完全均等的表现机会,因为平等并不是绝对性的固化概念,不意味着平均主义的均等,每个人物形象还需要在文本“块茎状结构”中自由地参与竞争,以期获得足够的艺术表现机会并成就自身艺术形象。
说到底,“块茎状思维”和“块茎状文本”仅止于提供自由平等的艺术发展条件,仅止于赋予艺术人物形象以民主发展权利,但不可能也没必要决定每个艺术形象的最终发展高度。在“块茎状”文本中,唯一能规定的就是每个人物都可以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作者不会有意扼杀某个人物的艺术声音,不管是达官贵人、英雄豪强,还是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他们在文本结构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声音,哪怕与权力话语无关,也依然在文本中有独特的艺术显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判定《山本》是具有“块茎状思维”和“块茎状文本”的新历史演义小说,与众多革命历史演义小说的“树状思维”和“树状文本”区别了开来。

不难看出,在《山本》的庞大人物形象群体中,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群体均有各自的艺术地位与使命,同一人物系列中的不同人物形象也有各自的艺术地位与使命。从小说“块茎状文本”建构的角度而言,这些人物都属于自由平等的芸芸众生,谁也无法取代他者的艺术生命。但“块茎状文本”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反中心主义,反中心主义的本质其实是倡导文本的多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不是不要中心,而是主张文本有多种声音,类似于巴赫金所谓的多声部小说和复调小说。依此而言,《山本》中有大量的人物形象其实是多中心主义的艺术产物,他们尽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因为他们都有自身或大或小的艺术使命。这些小人物虽然如鲁迅评《儒林外史》时所言,“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但《山本》毕竟不是《儒林外史》那种“集锦”式组合体小说,全书不唯有叙事主干而且有多条叙事主干,故而能将众多的小人物统一纳入多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中,使其“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1。显然,那种过度现代性的小说文本习惯于秉持绝对的中心主义人物立场建构单调文本或主旋律声音,而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的杰出作品往往擅长于“块茎状文本”或“复调小说”营造,这正是今人应该大力发扬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伟大传统。
多年以来,贾平凹一直致力于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典小说的这种伟大叙事传统。从《废都》到《秦腔》到《山本》,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他从未停止小说艺术实验的脚步。《山本》中除了那些偶尔露真容的人物之外,还有很多贯穿全书的人物,而在这些贯穿全书的人物中,又有少数人物在“块茎状文本”结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叙事枢纽作用。比如红军系列中的井宗丞、国民党军系列中的井宗秀、周旋于两者之间的阮天保、绅商系列中的陆菊人,还有国共双方的重要基层领导干部蔡一风和麻县长,这些都是《山本》中举足轻重、贯穿全局的叙事枢纽人物,毫无疑问,他们也是这部长篇小说作为“块茎状文本”生长得最为充分、形象也最为立体的中心性人物形象。他们作为《山本》“块茎状文本”的多个中心,其命运同频共振,又彼此对话(对立),在复杂的差异性中又显示出深刻的同一性。简单地说,他们的人生命运轨迹中都隐含了特定的历史悖论和历史反讽意味。这就暗合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奇书”结构传统。按照海外汉学家浦安迪的说法:“在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奇书文体有刻意改写素材的惯例,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对素材作戏谑性的翻版处理,不再单纯地复述原故事的底本,而注入了一层富有反讽色彩的脱离感。
”2 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的奇书文体,不论在题材上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性,其叙事框架中都隐含了高开低走、前后背反的反讽性原型结构。如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中,最后的历史归宿与当初的历史目标之间存在背离,西游神话故事中也隐含着人生成长的意义悖论,至于《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世情小说更是揭橥了现实人生中的巨大反差与戏剧性反转。
具体到《山本》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都隐含了历史的苦涩与荒谬。比如井宗丞,他少年得志,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以大义灭亲的方式出卖了父亲井掌柜的财富秘密,以致其父遭绑架后一夕毙命。此后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屡建功勋,多少地主富户和保安队队员成为他的枪下之鬼。但就在他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之时,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团长遭到内部肃反而牺牲,他的人生的戏剧性转折中隐含了深刻的历史悖论。无独有偶,井宗秀从早年的家道困境中崛起后一直励精图治,事业不断扩张,威望日渐隆盛,然而也就在这种盛世奇才翻云覆雨的鼎盛状态中,井宗秀兵败如山倒,走到了人生与事业的尽头。井家兄弟高开低走的命运轨迹如出一辙,其中隐含的历史悖论堪称异曲同工。与之相对应的是阮天保,他在国共党争的复杂历史局势中左右逢源,最终成了井家兄弟的历史掘墓人,其命运轨迹的低开高走与井家兄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阮天保这个形象的复杂性与《白鹿原》中的白孝文差堪比拟,且两人最终都是历史的胜利者和人生的大赢家,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三国演义》中三国归晋的历史大结局——当魏蜀吴三足鼎立消解之时,即司马家族开创新政权之始。与井宗丞命运轨迹相似的红军将领是蔡一风:作为秦岭游击队的创建者和红 15军团的政委,他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居功至伟,但最终和井宗丞一样惨遭肃反。
而麻县长作为国民党西北军下辖的平川县政府首脑,他的命运轨迹同样高开低走。这个旧中国的书生官吏原本想在秦岭山区建功立业,但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被井宗秀的预备团(旅)以挟天子令诸侯的方式操纵于股掌之间,最终他选择了自沉涡潭,随井宗秀走向历史的终结。至于陆菊人,其人生命运堪称女界传奇,她以一个早慧的童养媳身份一步步地介入涡镇乃至秦岭地区的革命历史大旋涡中——陆菊人一直期待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那块龙脉宝地能够在涡镇显灵,当她发现唯有井宗秀堪当大任时,就把无限的救世希望寄托在井宗秀身上,并竭尽所能地帮衬和辅助井宗秀在涡镇成就大事业,让涡镇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常生活。让陆菊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所盼望的那种不世出的大英雄,那种挽救苍生黎民于乱世水火的所谓大人物,最终将涡镇以及涡镇民众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历史绝境,也使陆菊人陷入了历史的虚无陷阱。从这些贯穿全书的叙事枢纽型人物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们的历史命运中都隐含着挥之不去的荒谬感,带有强烈的历史反讽色彩。其实不仅叙事枢纽型人物如此,其他主要人物的命运同样如此,比如井宗秀的左膀右臂杜鲁成和周一山,主动投奔井宗秀的绿林好汉夜线子,被陆菊人引导嫁给井宗秀的民女刘花生,还有陆菊人的公公杨掌柜和丈夫杨钟,他们的苦涩命运也带有黑色反讽色调。杨掌柜至死都难以明白为何井宗秀和阮天保这样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兄要你死我活地杀来杀去;一直像个贾宝玉的“混世魔王”杨钟最终稀里糊涂地在战争中送命;刘花生嫁给井宗秀后“越想爱他心里越乱越苦”,她对陆菊人说“我现在活得没意思,像被抽了筋,是一堆软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井宗秀历史人生的荒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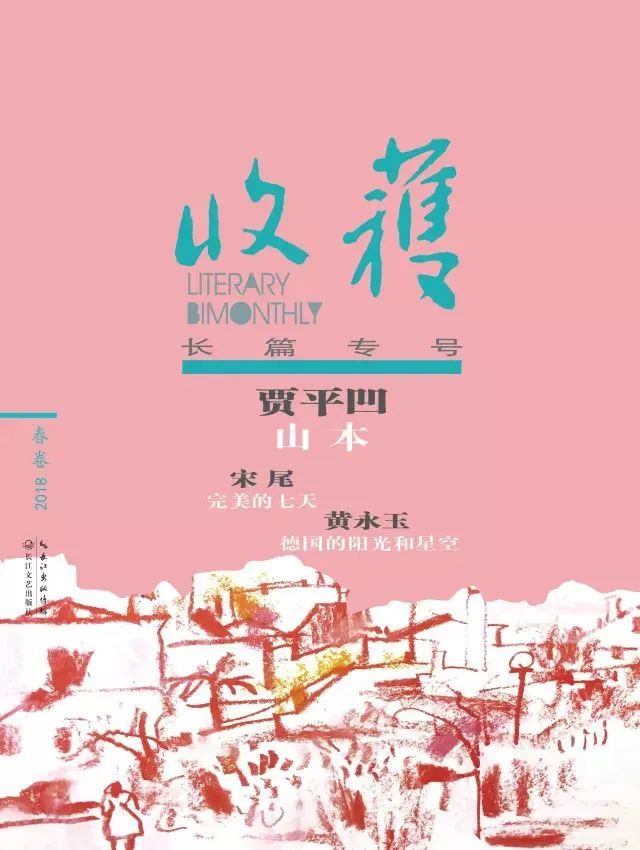
虽然《山本》作为“块茎状文本”让多达百人在其中自由生长和发声,但井宗秀无疑是其中得到野蛮生长因而形象最为丰满的“这一个”艺术典型。这就如同《山本》虽然涉及大秦岭地区诸多城镇,如方塌县、三合县、桑木县、麦溪县、平川县之类,但最终着墨最多的还是地处平川县的涡镇。作为秦岭深处最大的乡镇,涡镇和它所孕育的“这一个”典型井宗秀无疑是《山本》这部新历史演义小说的核心或灵魂。因此井宗秀和他的涡镇故事就成了《山本》历史叙事的重中之重。于是我们看到《山本》虽然由多个系列的秦岭历史人物形象的野史杂传组合而成,但“涡镇传”和“井宗秀传(传奇)”无疑是其中最意味深长的叙事组合体。井宗秀和涡镇可谓彼此成就、互相拆解,最终同归于灰烬。一句话,井宗秀及其涡镇故事中其实隐含了这部新历史演义小说的“义”之所在。它与古典历史演义小说所演之“义”迥异其趣。中国古典历史演义由于起源于儒家经传的“演绎”“衍义”“衍绎”,最初是指用于释经的言说方式,故而所演之“义”多为儒家圣贤经传的纲常伦理信条。如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庸愚子序即云《三国演义》之“义”与孔子因获麟而作《春秋》的春秋笔法和春秋大义相合相通,正所谓“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3。
其他古典历史演义小说的“义”大都可作如是观。而《山本》所演秦岭现代革命史之“义”则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意蕴,这包裹在小说叙事框架的重中之重,即井宗秀及其涡镇故事中。从精神实质上剖析,井宗秀及其涡镇故事中其实隐含了一个从乌托邦叙事到反乌托邦叙事的内在断裂或反向拆解过程。在《山本》中,以井宗秀无意中得到陆菊人的龙脉地为暗示,井宗秀就是陆菊人理想的“真龙天子”;而以井宗秀赠陆菊人古铜镜为隐喻,陆菊人就是井宗秀人生的一面镜子。最初的井宗秀尚在陆菊人的理想期待视野中发展,他在关键时刻还能以陆菊人为镜子反思自己的人性弱点,如他听取陆菊人的建议不重蹈土匪五雷和岳掌柜在涡镇的历史覆辙。但随着井宗秀在涡镇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日渐得到巩固,他被诩为涡镇的活城隍,被涡镇人当作土皇帝而顶礼膜拜,此时他已经听不进陆菊人的逆耳良言,他内心深处的权力欲望日渐膨胀,开始醉心于穷兵黩武和大兴土木,对外主动攻击阮天保的红军游击队,对内集资仿照平川县城重建涡镇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人性阴暗面日益暴露,不仅报复心重,杀人如麻,而且人格虚伪分裂,手段阴险歹毒。井宗秀以自己的喜好将涡镇的城墙和军营全部装点成黑色,而且每晚两次骑着高头大马巡查全城,总之他以自己的至高权威为涡镇的日常生活确立规则,他成了涡镇说一不二的立法者。
但井宗秀越活越色厉内荏,小说中暴露了他的生理暗疾,这个白面少须的中年男人其实是“人里面的骡子”,不男不女,经常整宿难以入眠,只能变态地让妻子刘花生裸身在床供他半夜欣赏,而每夜找来的涡镇女人们也不过是陪他解闷而已。就这样,《山本》中真实地揭示了井宗秀由造福涡镇的英雄异化为祸害涡镇的枭雄乃至奸雄的过程,同时也深刻地揭橥了在井宗秀的主宰下涡镇由一度的理想型乌托邦异化为最后的荒诞型反乌托邦的过程。
这样的反乌托邦叙事虽可以让人联想到西方文学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但《山本》中对乌托邦异化为反乌托邦的叙事进程做出了极具中国本土化色彩的深刻描绘与细腻表达,而且作者将其巧妙地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之中。正如贾平凹所言:“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承接过建国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4显然,《山本》就是贾平凹所期许的中国“四不像”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外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改写,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叙事传统的传承,还可以看到欧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响。在《山本》中,这种欧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响,就集中体现在小说的乌托邦叙事与反乌托邦叙事的历史背反中,其核心哲学基础即西方现代所流行的存在论或存在主义话语体系。长期以来,这种存在论话语体系所催生的荒诞派美学对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着重大影响,但它常常被包裹在贾平凹小说中习见的以谈佛说道为特色的中国叙事外衣中。
贾平凹在《山本》中再次通过佛道文化叙事将小说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精神包裹起来,或者说让后者天衣无缝地融入前者中,以此达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或曰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化。小说中的安仁堂陈先生是个盲人郎中,早年随元虚道长学医,因无辜被拉壮丁当兵,只好自己弄瞎双眼回涡镇行医陈先生在小说中是作为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信徒而出现的,在他看来,井宗秀诚然是英雄,但涡镇要是没有英雄就好了,就可以天下太平,这是典型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外篇·胠箧》)的翻版。而在陆菊人看来,涡镇不可能不要英雄,问题主要在于英雄太多而且英雄做得不够大,如果英雄做大了且只有一个英雄,那涡镇就天下太平了。陈先生对陆菊人的说法不置可否,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涡镇的大结局——当涡镇在炮火中化为尘土时,一切都会有答案。与陈先生不同,城隍庙的宽展师父是个佛门弟子,在她那里,众生平等,不分所谓政治派别,人死了都需要超度亡魂。她带着陆菊人、刘花生在旅店里念《地藏菩萨本愿经》超度井宗丞的亡灵回故乡,神秘而又慈悲。意味深长的是,陈先生和宽展师父在小说中都成了战争劫难的幸存者,与他们性情相近的陆菊人和剩剩母子最终也劫后余生,而小说中的儒家士人文化传承者,那个曾经幻想着自己能传承张载《西铭》精神的现代儒生,最终不但未能为天地生民立心立命,更不能为万世开太平,而且就连他写的“绝学”《秦岭志》手稿也毁于战火,而他自己则在绝望中走向了涡潭。
在这些来看,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道释三家文化的立场可见一斑。事实上,贾平凹更看重佛道文化的悲悯情怀和空无境界,因为它与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精神相通,二者可以会通融合。借用晚清张之洞的名言而反其意,我们也许可以说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另类的“中体西用”论者,即以中国本土文学文体为体,而以西方域外思想精神为用。或者反过来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西体中用”论者,即他自己所言:“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5此处的西体指文学的精神、内容,而中用指文学的文体、形式。两种说法皆通,直指贾平凹的文学理想境界。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
2.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3.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见黄霖等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4.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4页。
5.雷达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本文往期精彩: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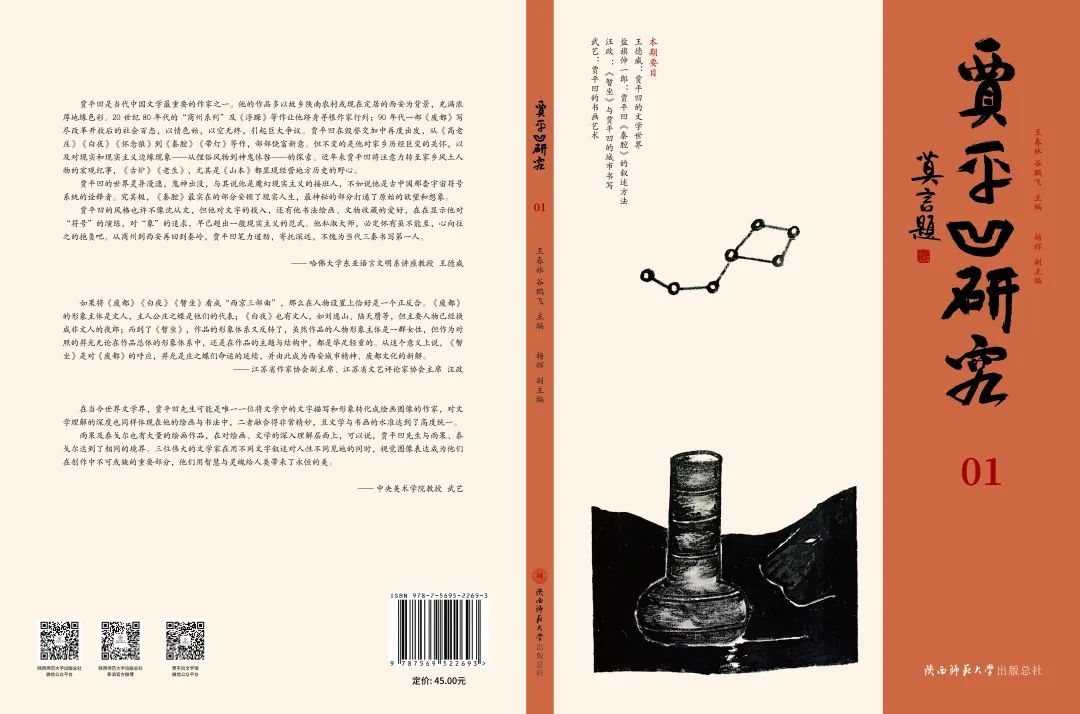
本文刊于《贾平凹研究》2021年第1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