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est Observers等外媒消息,法国出版商阿尔宾·米歇尔(Albin Michel)于当地时间9月29日表示,法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逝世,享年92岁。

保罗·韦纳(1930年6月13日 – 2022年9月29日),罗马史研究专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古罗马的性与权力》《人如何书写历史》等,并主编《私人生活史》第一卷《从罗马到拜占庭》。
韦纳1930年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首府艾克斯,1955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日后,韦纳以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蜚声学界,日后成为法兰西公学院的名誉教授。他曾声称,自己选择历史和考古为业并非出于任何“人文主义的冲动或者特定的崇拜”,而只是源于他孩提时期的一次与文物的偶遇:8岁时,韦纳在卡瓦永村附近的凯尔特遗址发现了一块双耳形罐的碎片,这引起了他对罗马文明特别的兴趣。
从巴黎高师毕业后,韦纳定居在自己的故乡普罗旺斯艾克斯,并在普罗旺斯大学担任教授。在这段岁月里,他发表了一些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文章。在一个计量方法占据法国史学主流的时代,这些文章表达了韦纳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历史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也预示了他此后对历史叙事给予特别的关注。
韦纳著有《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人如何书写历史》《古罗马的性与权力》《福柯》等知名作品(这里提到的作品均已有中译本)。他的研究颠覆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许多固有的看法。韦纳关心政治史、战争史之外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心态的历史。在他看来,不存在所谓“大写的历史”,只存在一种“....的历史”——一种具体的历史。历史学家应当努力地讲述“以人为表演者的故事”,“历史学是真实的小说”。从这点来看,历史学并不是一门有普遍规律的科学。
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韦纳曾表示,一个人从来不会生来就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一个人成为历史学家,意味着“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与时代中的偏见作出足够的反应”。因此,“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就在于思考如何反对他自己”。在专业研究者的身份之外,韦纳也积极关注公共事务。他频繁参与法国知识分子的辩论,2015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Palmyra)的书——彼时这座古城正遭遇伊斯兰国组织的破坏。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人如何书写历史》中《一切都是历史,因此大写的历史不存在》一章,有删改。
原文作者|[法]保罗·韦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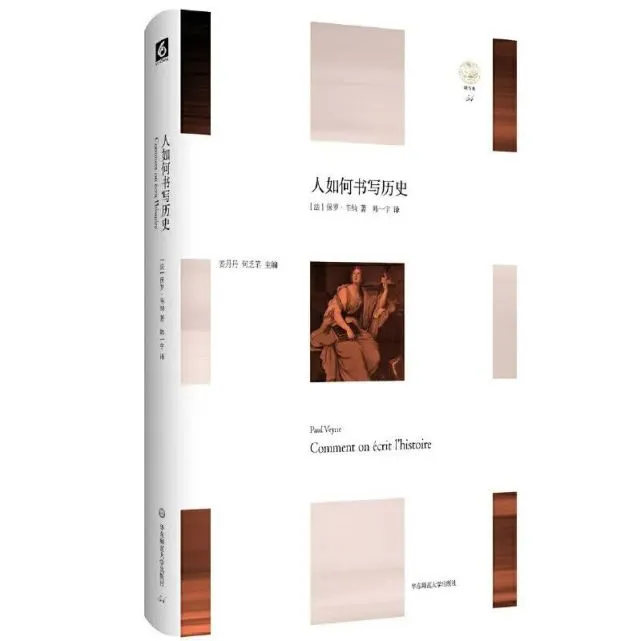
《人如何书写历史》,[法]保罗·韦纳著,韩一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历史的不连贯性
历史的场因此是完全不确定的,除了一种例外情况,也就是所有在那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至于其余部分,这个场的结构是紧密或是疏散,是完整还是有缺漏的,对它都无关紧要;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一页拥有足够紧密的构造,以至于诸多事件的逻辑差不多可以被透彻地理解,某个马基雅维利或是托洛茨基可以从中提炼出某种政治艺术;但是,一页东方古代史,局限于只是某种简陋的编年材料,包括我们关于一个或两个只留下其名的王国所知的全部,也仍然是历史。这种反常现象已经被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生动地揭示过:“历史是一个不连贯的整体,由诸多领域组成,每一领域都有其特定的周率来定义。
有一些时代,众多的事件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提供了非同寻常的事件特性;而其他的则相反,对他而言(或者,当然,对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发生的事情非常之少,或者有时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这些日期并不组成一个系列,它们从属于不同的种类。如果在前历史的体系中被编码,现代历史中最著名的插曲,也不再会是恰切的,也许(同样,对此我们一无所知)除了某些重要方面,从全球规模考虑的人口演变,蒸汽机、电和核能的发明。”一种模式的层次与什么相对应:“历史学家的相关选择,从来只不过是在一种传授更多而解释更少的历史和一种解释更多而传授更少的历史之间进行。
《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栾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传记和轶事的历史,处于最低层级,是一种弱势的历史,其自身不包括可理解性,而只有当人们把它整体移 置到比它更强的一种历史中间时才能够获得可理解性;然而,我们要是认为这种嵌合渐进地重构一种完整的历史,那就错 了,因为,我们从这一边得到的,总是会从另一边失去。传记和轶事的历史是最少解释性的,但是由于它依据个性来考察 个体,对每一个都详述特点的细微差异,动机的起伏变化,思虑的不同阶段,因此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它就更加富有。这种信息自行简化,随后,在过渡到越来越强势的历史时自行消解。
非重大事件的观念
因此,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有自由随意地切割历史(政治史,博学化历史,传记,人种学,社会学,自然史),因为历史没有天然的关节;现在该是在历史事件的“场”和作为体裁的历史之间加以区别的时候了,这要运用人们在不同的世纪为设想这种区分而形成的种种不同的方法。
因为,在连续不断的演变中,历史体裁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扩展,在某些时代,它与其他体裁 分享自己的领域,如旅行史或是社会学。因此,让我们区别历史事件的场一它是历史体裁的虚拟领域——和这一体裁随着时代变迁在其领域切割而成的各种不同程度延展的王国。古代东方有它自己的国王名录和朝代纪年;在希罗多德那里,历史是政治和军事,至少原则上如此;它讲述希腊人和蛮族的业绩;但是, 旅行家希罗多德没有把它与一种历史人种志区别开来。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合并了人口统计学、经济、社会、精神面貌,它憧憬 着成为“总体历史”(histoirc totalc),统辖它全部的潛在的领域。
《历史:详注修订本》,[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在这些彼此相续的王国之间,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连续性在我们眼中建立起来;从那里产生了一个虚构的演化中的体裁,连续性 从历史这个词语本身(但是,人们确信必须排除社会学和人种学)和都城的稳定得到保障,这个都城即政治史:然而,在当代, 都城的角色有转移到社会史或者是我们称之为文明史的倾向。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什么又不是历史的呢?我们将在下文追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此刻马上要说,为了区别这一点,我们不能信任以历史体裁在某一特定时刻的边界作为其边界;就像是我们相信拉辛的悲剧或者布莱希特的正剧均体现戏剧的本质。在推理的这一阶段,不可能理性地确立在历史、人种志、传记和通俗社会新闻之间的区别;不可能说出为什么路易十四的 生活该是历史,而17世纪生活在纳韦尔的一个农民的就不是;不可能宣称以三卷叙述路易十四的统治是历史,而以百卷来叙述它,就不再是历史了。
人们尽可以尝试进行区别,尝试去设置一个定义(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性内容的历史,是对我 们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的历史……):德国历史主义已经表明这 一点,而且,它的失败也不情愿地确认了这一点,即,没有什么定义是站得住脚的;眼下,仅有的边界仍然是这一体裁那些变化的 惯例成规。我们顶多能证实,这一体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拥有诸多变化,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倾向于越来越铺开;如同一条河 流在过于平坦的区域,放任地铺展,而且很容易改变河床位置。
历史学家最终把建立这种帝国主义作为教义;他们求助于森林的比喻而不是河流的比喻:通过其言论或是行动,他们宣称,历 史,即如人们在不论哪个时代所书写的那样,不过是一望无际的森林中间一块经过清理的拓荒地,而这片地,理所当然地完全归属于他们。在法国,年鉴史学派,围绕马克-布洛赫创办的杂志聚集起来,致力于开垦这块拓荒地的边界地带;依据这些拓荒者,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过于别无选择地研究那些自古以来为人公认的足够重要的事件;它所做的是“条约-战争史”;然而,还余留下巨大疆域的“非重大事件”要去开垦,而对于它我们甚至还看不清边际;非重大事件,也就是还没有被给予过重要性关注的 事件:各个时代的土地史、心灵史、疯癫史或是安全保障寻求史。因此,我们将把我们未曾意识到其像那样存在的这一历史性称 为非重大事件;这一短语在本书中将以此含义使用,这是公正 的,因为,这一学派及其观点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多产。
事件没有绝对的尺寸
在这个拓荒地的内部,每个时代的观念或是惯例在历史性的场域中进行剪裁,各省之间不存在稳固的等级制;任何一个地带既不管辖另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吞并另一个。最多不过是,人们可能认为某些事件比其他的更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本身完全取决于每个史学家取舍的标准,并没有绝对的分量。区别经济史、政治史、技术史等等,是方便的,但是没有哪一个方法的规则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历史中哪一个领先于其他的;若它会告诉我们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将会是被证实的真理,它也将是非常柏拉图式的真理,并不会影响讲述历史的方式;技术不会使经济消失,经济也不会使社会消失,因此,可以照惯例去描述的社会事件、经济大事和技术大事总还是存在。有时,一个身手灵活的导演装置了一个巨大的布景:勒班多战役,整个16世纪,永远的地中海和沙漠,真主在那里是唯一的存在;这是建立了一个有景深的舞台装置,而且以巴洛克艺术家的风格,各种不同的时间节奏并置,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系列化。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论构建的想象》,[法]保罗·韦纳著,张竝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对一个柯瓦第(Koyrc)的读者,即使物理学在17世纪诞生可以用上升的资产阶级对技术的需求来解释的观念不是靠不住的或者甚至是荒谬的,科学史并不会由于这样被解释而消失;事实上,当一个历史学家坚持科学史对社会史的依赖性时,经常的情况是,他在写一部有关整个某一时代的一般史,而且顺从一种修辞的规则,这种规则要求他在关于科学的章节和有关社会的章节之间搭建一些桥梁。历史就是并置的王国。
然而,印象仍然是,1914年的战争毕竟是比巴黎慈善市场的火灾,或兰杜事件(Taffairc Landru)更重要的大事件;战争是历史,其余的只不过是社会新闻。这只是一种错觉,它让我们混淆这些事件中每一个事件的系列,以及它们在系列中的相对尺寸;兰杜事件比起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但它是否与路易十五外交方面的一个细节或是第三共和国治下的内阁危机不成比例?而且,该怎么讲述希特勒德国曾玷污人性脸面的恐怖,怎么讲述奥斯维辛巨大的社会新闻?兰杜事件在一本犯罪史中占据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是,这部历史不如政治史重要,它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占据较为次要的位置?对于哲学史,人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对18世纪之前的科学也是如此;它有较少的现实后果?路易十五的外交真的有更多现实后果吗?
然而,还是严肃一些吧:假设一位天才允许我们在十页篇幅中去了解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文明的过去,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会优先了解高超的犯罪,还是去搞明白这一社会到底更像什么,是像美拉尼西亚部落制,还是不列颠的民主制?很显然,我们首先想知道它是部落的还是民主的。只不过我们刚刚还是混淆了历史事件的尺寸和它们的系列。犯罪的历史只是社会史的一小部分(但是非常有暗示性,在一个高超的历史学家手中);同样,常驻性的外交机构,这一威尼斯人的发明物,是政治史的小部分。必须要或是比较犯罪的大小和大使的规模,或是比较社会史与政治史。我们想要优先了解什么,这一未知文明是民主的而不是部落的?还是想要知道它是工业化的还是仍处于石器时代?可能是这二者;除非我们会宁愿纠缠不休于确定是否政治比社会更重要,是否大海比去山里度假更好?一个人口统计学者突然出现,他宣称人口统计学必定拔得头筹。
让我们头脑混乱的是俗称通史(Thistoirc dit gcncralc)的这一体裁,它的标准也还是心照不宣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且也并不少主观性。这种通史的主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政治史,但是,今天则更多地是非重大事件的:经济,社会,文明。这并没有我们的报告比例失调,还是谈论对于最大多数亨利三世治下的法国人最重要的东西;政治史将不再具有重要性,因为国王的大多数臣民除了作为纳税者与罪犯之外与权力机构毫不相干;我们将尤其要谈论好人雅克(Jacques Bon hommc)的劳动和生活;一个简短的章节勾勒文化生活的图景,但是精明人将会尤其在那里谈论历书,到处传播的小册子和比布拉克(Pibrac)的四行诗。
然而,宗教呢?就16世纪而言是极大的空白。但是,我们是致力于描述这一时代日常生活的平均线,还是其情感的顶点,它无疑同时是强烈而短暂的?还有,我们是一般地叙述16世纪,还是讲述它与之前或之后世纪的区别?地理学家们熟知这种困境:在以渔民著称的某个沿海省份中,人们却发现,渔业只占其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一省份的独特性的的确确归功于它;同样真实的是,渔业是敏感的因素,是其经济上最弱的战略要点;那么,是选择平均、差异还是战略要点?又冒出来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眼里,最重要的是被选择事件的持续长度:深度的结构,缓慢的脉搏,数百年的循环;量化的标准。第三个历史学家偏爱作品胜于事件:17世纪,这是物理学、巴洛克、笛卡尔主义和绝对王权的世纪。对于一个研究古代文化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个同样可接受的原则是可理解性:不是提供给读者一个有空白缺漏的历史,就像萨福的集子一样,他选择把历史缩减为一个事件的选集,以此来比其他做法较少残缺;庞贝的地方史和政府组成人员的人物研究将会比罗马城邦和整企3世纪占有更多的篇幅°或者还有,他会以它的高峰来定义廿个文明,而不是以它的总量来定义:维吉尔的虔诚因此将是切入如此难于了解的罗马虔敬的一种视点。
《福柯:其思其人》,[法]保罗·韦纳著,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2018年2月。
不可能决定一个事件是历史性的,而另一个事件是轶事插曲只配被遗忘,因为所有的事件都进入一个系列,只是在它的系列里才有相对的重要性。那么,是产生后果的规模大小使一个事件显得比另一个事件更重要,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些能够把公元前404年雅典的失败的后果分离出来,而且一直追踪到我们时代的人是幸运的;而后,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起源极少有美好的'此外,那些后果必将使它们本身成为一种选择的对象;这里就会插入那个令人生厌的“历史的意义”问题,人们通过选择给予历史的意义:维吉尔和罗马的命运,马克思和资产阶级,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和第三等级,拉维斯(Lavissc)和法兰西的统一。
不管怎样,后果重要性的准则不过是一种严肃的头脑激发的虚构:历史讲述路易十四的战争为了其自身,而不是为了它可能拥有的遥远后果。不是更应该根据那一时代本身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每一个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吗?这是好心地把当事人的主观性当作了客观性;不幸的是,价值标准本身也属于事件的性质。我们不是为了同时代人曾经对它的关切而讲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如果这个条约产生而未被人们注意,这种漠不关心本身也是一个额外的事件。
人们并不是以罗马人对其感兴趣的精确程度来对竞技场发生兴趣,但是,人们也对罗马人对竞技场的兴趣感兴趣。那么,是否那些不是个性化的东西,那些有关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东西,才会是历史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做出这种区别的人,或是那些自认为能够给它找到一种意义的人有权发言。
路易十四得的一次流感,即使是国王的,不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它有关法国居民的卫生史。事件的场是各个系列的彼此交织。因此,我们看到历史编纂学转向怎样的调节性观点:朝向一种总体历史,对于它,只要是事件就不再可能是无关的;事实上,没有人再会感到吃惊,在期刊目录里,发现一种时间观念的历史或是色彩分辨(或者分类)的历史。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再能够清楚地看到,一部关于路易十四治下的社会史,一种庞贝的绘画史,或者13世纪托斯卡纳的乡土史,与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当下社会的描述,对巴黎郊区北非裔劳工或是对作为大众艺术的摄影的描述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在历史、描述性的人种志和作为当代文明史的社会学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传统的,或是建立在大学教学体制之上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