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队伍初步组建后,清史馆开始正式运转,而体裁、体例的确立是第一步工作,这是历代官方修史的传统,因为采用何种编纂形式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制约内容的安置,实际上直观反映了再现客观历史的路径和方式,同时又与正统论、春秋笔法、笔削标准、是非判定、价值取向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民国取代清朝又在性质上有别于以往的王朝更迭,故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本应充满新旧思想的交锋。
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民主共和进程,而清史馆的设置又是其中重要环节,袁甚至在设馆命令中已经作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表述,因此有关清史编纂的体裁并未经过大的讨论就达成一致,差异仅在于具体体例的确定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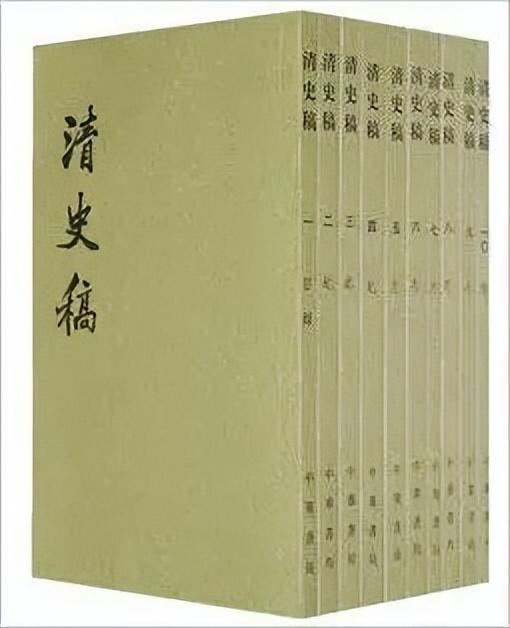
当时,清史馆就体裁、体例问题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馆内外学人(以馆内纂修人员居多)纷纷就某一方面建言,比如于式枚等撰《拟开馆办法九条》、梁启超撰《清史商例》、吴廷燮撰《清史商例》、金兆蕃撰《拟修清史略例》、张宗祥撰《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朱希祖撰《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等。
多数人认为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后体例如何,自当别议”,但清史乃“与二十四正史并列之书,实在矣数千年帝制结局之作”,故而主张沿用纪传体,并在类目上“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纪传体并非单一体裁,而是带有综合性质,能够容纳丰富的史实,从不同层面反映历史演进情形,但同时也是君主专制制度在史书体裁上的映射。
其时,“新史学”已风靡全国,以章节体为主的新式体裁已颇为流行,对旧式体裁的改造也方兴未艾,但以遗老为主体的清史馆显然未能表现出足够的求新意识,而是恪守传统,致使不少具有创新价值、反映时代进步的看法被有意忽略了。
比如,有人提出志、传应添加图,认为:“旧史无附图者,近代舆图,日以精密,工技之精,非图未辨,左图右史,古学所重,大约疆理、河渠、邮传之志,礼器之数,兵之船械,皆非有图,无以证明……既无因袭,亦可特创。”有人建议增加民俗志,认为:
志宜兼详民事。中国旧史,大都详朝廷制度,略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千古称之,今宜扩而充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切日用风教有关者,良窳得失,灿然无遗。
此类意见虽不占多数,但毕竟说明新的科学精神和史学理念已开始向官方修史领域渗透。
修史机构能否有序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然而,清史馆开馆之初,馆长赵尔巽并未制定详细的工作条例,仅设置总纂诸员分撰表和功课簿,依据馆员专长而分配任务,要求馆员每两个月到馆交稿一次。
由于秉承袁世凯羁縻“遗贤”的宗旨,上述考核制度多流为形式,并不具有实质上的约束作用。严格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缺失致使史馆组织涣散,出现许多“领执笔名义者、坐领厚薪者、饱食而嬉者”,他们“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甚至出现“有请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学术”的荒诞现象,因此最初几年虽成稿数量众多,纪、传、表、志等均粗具初稿,但质量参差不齐。对此,朱孔彰曾建议对“全史体例加以审正,而慎选总领之人,商定分纂之办法,庶不致紊乱无纪,冀可观成”,惜未被采纳。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军阀割据、混战渐次粉墨登场,在动荡的局势下,清史馆因丧失政治象征意义而被新政权体系迅速边缘化,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经费的骤减:“馆中经费骤减十万,其后递减,月至三四千。此三四千者,犹不时至,或参以国库券公票之类。”馆员随之大半散去,仅余二十多人。
不过,政治负担的减轻以及素餐之人的离馆反而让赵尔巽能够放手整顿,他进一步统一凡例,明确分工,并特聘邵章为提调,专司其事,负责与编纂人员联系,同时整理先前已撰好的文稿,又在缪荃孙建议下制定了“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的统稿、审查原则,馆风遂大为改善。
然而,直皖、直奉战争的爆发令东华门经常关闭,馆员无法“调书考证”,经费亦几近枯竭,“在馆人员,等于半尽义务”。最终馆内仅余十四人,并被迫进行馆外兼职,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馆长赵尔巽向吴佩孚、张宗昌等寻求支持,而“诸军帅慕义乐善,而重公之名德……皆慨输巨款”。
1926年,鉴于全稿已粗具规模,史馆决定用两到三年时间进行终审定稿,并重新分配任务,即:柯劭忞总阅本纪、王树楠总阅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与金兆蕃总阅列传等。1927年春,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赵尔巽以“时势之艰虞”和“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为由,决定将史稿付印。
部分馆员对此持赞同意见,希望以刊印后的稿费补发欠薪,而夏孙桐等则极力反对,认为史稿错漏太多,“断不可冒昧行之”,否则恐贻笑世人,并建议“实事求是,逐加修正,务延总阅,全体讨论,以期详审”。
但赵尔巽意在有生之年完成清史编纂心愿,遂坚持己见,并称:“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不久,赵尔巽病重,适逢袁金铠来京,遂委以刊印之事,而袁又假手金梁负责。同年8月,赵尔巽病故,由柯劭忞代理馆长,并再次缩短刊印之期,造成大量书稿来不及审核、修正即付刊印。全书赶在北伐胜利之前仓促印刷完毕,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八百余万字。
当时,共印制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被金梁未经馆长批准即运往关外,称为“关外本”;留在馆内的七百部被馆员发现多有金梁私自增改之处(如增加康有为、张勋传,修改部分列传,删改艺文志序,增加校勘记等),遂重加纠正,称为“关内本”。后来,关外再次重印,对部分列传、史表等做了删改,称为“关外二次本”。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