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治史三书》中曾谈起当代著名史家,他认为前一辈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两位陈先生、吕思勉诚之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
其他回答里提及不少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少则几十多则上百。这些人可以算是历史学者,但能不能算上大家,那还另说,至于大师,更是寥寥无几!我想说,大师的标准就那么低吗?哪有那么多大师呀!
史学著作推荐的话,只写过一个回答,可以看一下。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都推荐了(全部是名校院系,学界大佬力推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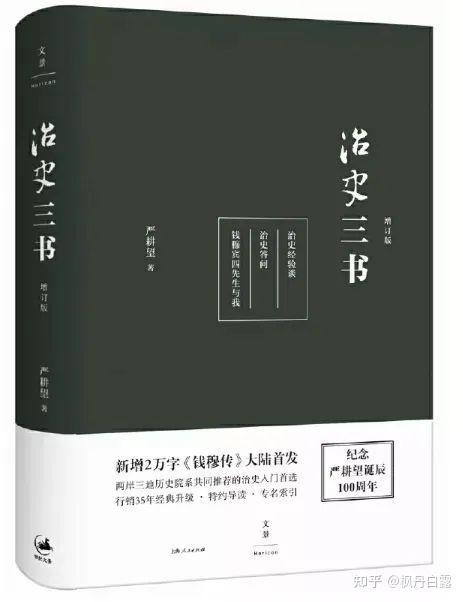
历史专业必读一、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早年求学经历与其卓越才识
两位先生中,寅恪先生声誉尤著,亦早两年谢世,兹先谈寅恪先生。先生自1902年十三岁东渡日本求学三年,1910年到柏林大学转巴黎大学,前后五年,1918年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1921年由美国再赴德国就读柏林大学,至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三十六。故其少年青年时代求学时期极长,在东西各国就读研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其学习科目,主要为古今各国语文,及中国边疆民族语文,次及哲学宗教,似亦稍涉社会科学。先生记忆力特强,据各家所记,除英、德、法、日等国语文外,遍习梵文及巴利、希腊、拉丁、波斯、土耳其、蒙、藏、满文,有些或且甚精。吴宓雨僧《空轩诗话》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第81页引)此语信实,非吹嘘可比。
(2)学术动向与治史历程
寅恪先生回国以后的学术动向,从其授课与著作次第看来,其治学以历史为中心,兼及佛教与文学。其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回国的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
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
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余英时著《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下篇,《明报》月刊1983年2月号,总206期)先生旷世奇才,加以早年环境优裕,语文工具特强,东西学术基础亦特别深厚,惟惜中年时代健康情况看来似颇差,殊难尽量发挥其才学,我在《治史经验谈》中已表示非常可惜。(《治史经验谈》第九篇《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第109页)
(3)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
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

二、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1]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2] 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早期代表著作与治学动向
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1917年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其第一篇学术性论著。自后二十年间,重要著作以次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等。
此诸著作涉及多方向:其一,各种宗教史,尤其西方诸宗教传入中国史。其二,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皆为历史研究所必备的辅助学科,先生诸书多为有创建性的工具书籍。其三,多种著作与元史有关。一、二两者都是一般学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这些地方,显得先生常能适时灵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义的问题,用最大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
(2)后期重要成绩
则有《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五书,都是极踏实有创获,应许为有永久性价值的著作。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这一时期,这几部书显示先生学术著作达到最巅峰状态,但也即此而斩。先生享年九十二岁,《胡注表微》写成于抗日战争末期,当时年龄不过六十五六,精神尚旺,何以此后二十余年都无重要著作?据最近出版的《励耘书屋问学记》(1982年6月,三联书店),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励耘书屋问学记》第一篇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代序)》第6页。后面各篇亦屡见此语)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3)史学二陈的比较
1、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
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
2、至就立身处世言。
最后总结一句: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三、吕思勉(1)著作
诚之先生平生著述极为丰富,为人所习知的,以出版年份序之,有《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二)、《经子解题》(一九二六)、《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史通评》(一九三四)、《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燕石札记》(一九三六)、《中国通史》(一九四〇、四五)、《先秦史》(一九四一)、《历史研究法》(一九四五)、《秦汉史》(一九四七)、《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燕石续札》(一九五八)、《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诸书。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未发表的札记与已发表的两部札记合并,分时代编为《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一九八二),还有《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未能完成,不知将来是否有人能整理出来,作为未定稿出版。
(2)治史意趣
综观先生一生著作程序,可知他的国学基础极深厚,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属于国学范围的居多,所以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这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在一九二〇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顾颉刚师在《当代中国史学》下编《通史的撰述》一目中列举诸家通史,就以此书为首,认为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谓当之无愧。我想这部书大约是当时极有销路的一部通史,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也是我读的第一部通史,相信这部书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必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称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他说唯物史观“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吾人应当注意,此时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好几年。再看他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册,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次年出版的《先秦史》,其编排次序,在先秦各代政治事迹之后,分类述文化现象,也是这个顺序。这一程序,正是他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更可见他这种意识发萌很早,与中共得政后一般趋附者大不相同。就因为早有此种意识,所以他治史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在通史及各断代史中,这方面的篇幅相当多,《读史札记》中这方面的条目也不少,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
就著作量言,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通贯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
(3)为何吕思勉名声不及二陈和钱穆?
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我想这可能有几项原因。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诚之先生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有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

(4)著作之价值
1、体例新颖
前文谈到,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记得高中读书时,看到张贴在阅报栏中的一张报,有一篇短文描写诚之先生与另一位文学家的生活习性。近年又看到黄永年所写《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一文与钱宾四师的《师友杂忆》(第二篇《常州府中学堂》第二节)写诚之先生一段,再参以他的著述风格,与半生株守光华一事,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的阅读过三遍,是可以相信的。
2、观点新颖
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当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有好处,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劄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只是厚古薄今耳!至于材料取给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参用。须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几部断代史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正是一项难能的基本功夫,后人尽可在此基础上,详搜其他史料,为之扩充、发挥与深入、弥缝,但不害诚之先生四部书之有基本价值也。
4、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1]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自民国元年(1912年)始,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抗战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抗战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2] 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 [3] 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 [3]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4] 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5] 还出版多种论文集,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如想深入了解钱穆的话,读钱穆传(严耕望为其师所作)。
有空会继续更新,谢谢大家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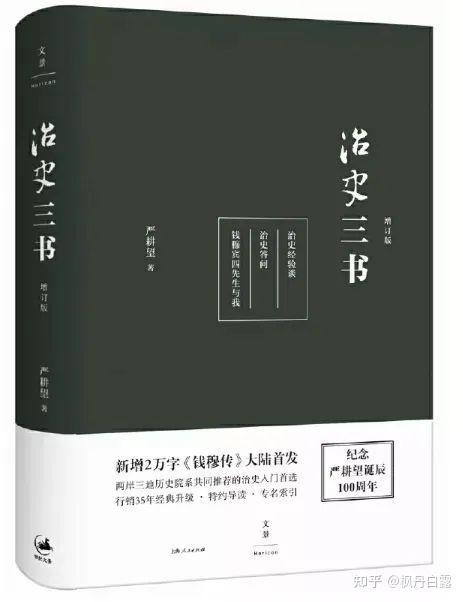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