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袁术暗有称帝之心,乃回书推托不还;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芬等三十余人商议……(见《三国演义》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对比《三国志》原文:
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见《三国志》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可以猜测,有可能是罗贯中看到《三国志》少了一个”弘“字,因为那时候没有标点符号,所以“长史杨弘”就变成“长史杨大将”了。
还有《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濬大笑,遂造大筏数十方,上缚草为人,披甲执杖,立于周围,顺水放下。
对比《晋书》第119章 王浑(子济) 王濬 唐彬(1):
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
这里又少看了一个“亦”字,结果把“方”错当做量词。这里不是要说罗贯中看书不仔细,而是可以从中看出《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即《三国演义》是参考史书写成的小说,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跟陈寿、房玄龄等人所写的历史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对“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书里列出来的九流十家中最末一家就是“小说家”。按照《汉书·艺文志》里的说法,小说指的是“琐碎之谈”,这显然是相对另外相对主流的“九家”来说的。到了元明之际,小说逐渐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里,都讲到了说书,可见说书是宋朝的时候市民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项娱乐。《东京梦华录》里汴梁的说书分为四类:小说、合生、浑话、说三分五代史,《梦粱录》里临安的说书也分四种:小说、讲经、史书、参请。合生、讲经和参请都和佛教有关,浑话是类似插科打诨的相声、段子,说三分五代史就是讲“三国”和“五代”的故事。“三国”和“五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都是非常混乱的时代,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因而最适合拿来说书,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无论是“说三分五代史”还是“史书”都是和“小说”并列的存在。根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这些说书人不仅有各自的话题、受众甚至还有专属地盘。比如合生、讲经、参请就不会跟小说一个堂子讲,讲史当然也有特定的场合和观众。有了活跃的商业行为,说书人就有强烈的动机精进自己的说书技能。于是在这个行业里,说书人对三国、五代的故事不断进行整理和加工。到《三国演义》成书的时候,说书的传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三国的故事经过了千锤百炼。
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梦梁录》
说明讲史有着明确的规范,那就是兴废战争之事,也就是“大”故事。一个朝代之所以兴,一个朝代之所以灭亡,这中间往往有很多战争,对比小说的“琐碎之谈”就有了截然不同的面向。另外,讲史不能够凭空去讲,通常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历代史书。比如《梦梁录》里说南宋临安最流行的是“说通鉴”,这里的“通鉴”并不特指《资治通鉴》而是指编年史这一类史书。通鉴的一个意义就来自编年体这个形式,这样的史书是按照时间顺序编纂而成的,这样展示出来的因此隐藏着一种叙事性,有情节的发展,有前因有后果,有大势所趋,还有治乱分和。另外,传统上常说以史为鉴就是“通鉴”的另一层含义。但是,从《史记》以来的史书大多采用纪传体,如此一来就让人很难完整掌握一件事情。比如鸿门宴这一件事在《高祖本纪》里写了,到了《项羽本纪》又写了一遍,仿佛是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两件事。从更大的视角去看,纪传体同样不利于对一整场战争,对一个时期的把握,那需要读者付出太多努力。或者说在这一个层面上纪传体的阅读门槛比较高,因为它在写作结构上是离散的,有着复杂的交叠形式。于是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对受众更“友好”的“通鉴”应运而生。再到“说通鉴”,历史就从一个相对比较精英的概念,一直不断下沉,降到了最普通的草根阶层。说书人把《三国志》的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句都翻译成白话,说给来茶馆喝茶的每一个人。把那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经过了整理,变成一个有头有尾有中腰,有因有果,环环相扣的一个完整的大故事。
主流说法称《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根据说书人的话本整理加工出来的一部小说。比如,很多人认为《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三国演义》的一个渊源的版本。可是,对于所有读过《三国演义》这部书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国演义》究竟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或者古代白话)呢?显然,相较于《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语言更加的“文言”。《三国演义》不只是语言上与史书更加接近,在结构上同样也有史书的特点。比如“主角”诸葛亮要到三十七回才出场,那么之前的核心角色其实是曹操,这一部分对应的是《三国志·武帝纪》。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里有很多的段落是直接挪用的《三国志》原文。甚至在比较原始的绣像版本前面有注明“晋平阳侯陈寿史撰,后学罗贯中编次”的说法。另外这本小说最开始也不叫做《三国演义》,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我们把它简称叫做《三国演义》,就失掉了这本书是依据《三国志》而来的这一层意思。它跟《三国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透过了说书这种长期的中介,一段一段地经过表演和捶打,然后他才把它整理出来。至少在罗贯中自己的心里面,《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从《三国志》而来的。
《全相三国志平话本》的开头叫做“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司马仲相是汉朝有名的狱官,他死了之后就继续干他的老行业,在阴间断狱。这个时候有一个复杂的案子呈到他的面前了,要他断四个人之间的恩怨,他们分别是刘邦、韩信、英布、彭越,这四个人经过转世轮回就依次变成了汉献帝、曹操、孙权和刘备。前世恩怨未了,所以他们来报仇了。当然这里最倒霉的是汉献帝,这三个原来建立汉朝的功臣,要回来把刘邦从他们身上夺走的拿回来,这才有了三分天下。这才是说书人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演练转变之后,他们认为最精彩曲折,最能够吸引听众的一种开头。显然,罗贯中并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中立场,他深浸在那样一个从宋朝长期传流下来,到了元明之际,已经非常成熟的讲史传统里。因此,他不会去照搬说书的讲法,而是把讲史的精神拿来改写《三国志》,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讲史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罗贯中很清楚,通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当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波谲云诡的战争和政治,最好就是用“通鉴”那样的一种编年史,依照时间一段一段地编织起来,让这段历史就可以连贯,让大家在读《三国志》的时候,不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因果变化,分分合合,就有了一个清楚的面貌。这大概就是罗贯中的动机和用意,同时这也是罗贯中最主要的成就。
《三国演义》的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一种循环史观。同时也清楚地显现出来《三国演义》把历史做了整理之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显示的是时间的本质。时间是不断流淌的,时间是不会停的。讲史就是要把被分割开来,在纪传体里面不容易形成的这种连贯的时间感找回来。在重建了这样的一种时间感之后,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体会如何分,如何合。在中国的循环史观当中,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因果也才能够建立起来。
在宋朝的时候,讲史主要有两种,一个讲三分,一个讲五代。这两个时代都是分的时代,因为有分,所以在重建历史感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一个主题,那就是看原来“分”的局面,究竟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的努力,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因果的关系,不管是来自于主观的,或者是来自于客观甚至偶然的因素,后来走向了“合”。这样一个“逆熵”的过程有着清楚的时间方向。
读《三国演义》,我们能感觉到三国这个时代,如此重视人才,因为重视人才,所以个体就会凸显,他们的个性,他的努力就变成了这个时代各种变化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所以《三国演义》有一个非常强的以人物的意志,以人物的努力来(试图)推动和改变历史的主轴。相对来说,五代的时候并没有像三国那样从汉末一路延续下来,对于个人对于人物,这种各种不同的品评跟重视,这是时代精神上巨大的差别。因而,在讲五代史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背后没有明显的人物意志和努力。因而在讲五代的时候,往往最后归结为历史的偶然。
比如讲到赤壁之战,在《三国演义》里很突出的情节就是“借东风”,可以说是诸葛亮的逆天神迹。而在借东风之前,又有周瑜跟黄盖所演出的苦肉计,之后还有曹操败走华容道,遇到了关羽,关羽就必须在忠和义之间作出选择。这些都是人物的意志和努力,它使得读者在情感上能够认同这些人物,认同诸葛亮的神通,认同黄盖的牺牲精神,也暧昧矛盾地但是仍然认同佩服关羽在华容道上所做的决定。所以虽然在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讲五代看起来受欢迎的程度跟说三分基本上是同等的。但在这里有一种朝代的自尊,朝代价值观的介入。因为宋朝是靠收拾了五代,也就是五代的“分久必合”造就了宋朝。所以宋朝的人在建立他们自己朝代认同的时候,五代就最为重要,此时五代就成了一个典型的错误示范,也因此五代不会有英雄人物,而只有一连串的混战和偶然。宋朝人当然是听得下去的,你看这些王八蛋,这些莫名其妙的荒唐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出来把他们统统收拾掉。所以五代的这些人被描述得越不堪,越不值得认同,宋朝的建立也就越加正义。但是,一旦离开了赵家天下的意识形态,五代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于是,说五代逐渐消弭,说三国却很好的流传到了今天。
《三国演义》源自于《三国志》,同时也是对《三国志》的补充。陈寿的时代距离三国非常近,很多认识反而是不够清楚的。因此《三国志》里面的这个“三国”看上去十分暧昧。另外,陈寿还来不及看到三国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比如《武帝纪》里记录的中原大混战,牵涉到边境,而且边境的作用越来越大。曹操打败袁绍之后,袁绍的两个儿子就逃到北边匈奴去了,所以曹操曾经派兵去到北方。 三国还多次提到一股特殊势力叫作西凉兵,西凉原来是董卓的基地,西凉再往西就到了氐族的势力范围。氐族也多次被动员,卷入到中原的战争。 其实这就是后来“五胡乱华”的基础,并不是到了西晋之后,才突然之间有这些“胡族”。边境各族正是趁着汉末的大乱,参与到中原的势力角逐,借机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开启了魏晋南北朝那一个更复杂、混乱的时代。
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历史的变化尚未抵定,等到元明之际,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那就不一样了,他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历史解释的能力和冲动,罗贯中的动机要求他要解释三国是怎么来的。所以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动了许多手脚。写《三国演义》,必然是已经确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都要变成建国者,因此他们的戏份是要加重的。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曹操参加袁绍联军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起眼,陈寿勉强把曹操拉高一点,就写曹操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曹操反对这些人按兵不动,然而陈寿的结论是:人家都不听曹操的。但是到了《三国演义》中,曹操也出现在袁绍集团里,而且是二把手,甚至让人觉得有的时候简直像一把手一样,是曹操在叫袁绍这样做那样做,只是袁绍不同意罢了。读者已经知道曹操就是主角,所以曹操当然重要了。
刘备就更明显了,刘备崛起的过程漫长且艰辛,在《三国志》里,刘备一路颠沛流离,仿佛一不小心就跌下去,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是绝对的主角,他不可能消失,他注定要成就这三分天下,而且是三分天下中最重要的一方,刘备不止要三分天下,他还要匡扶汉室。
《三国志》里孙坚的势力原来并不是在江东,他跟刘备一样,起初也没有确定的基地,要投靠不一样的人,想办法站稳脚跟。《三国演义》用结果反推前因,看起来似乎江东一开始就是孙家的势力范围了,实际上这是和历史不相符的。于罗贯要解释三国的来历,于是把这些枝枝节节的因素,按照他的方式整合起来。罗贯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历史上谁打赢了谁,谁败于谁手,统统予以合理化、戏剧化。这些看起来繁琐甚至重复的事件都只是过程,是不是真确,或者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儿其实都不重要,反而是对于历史的解释才是值得重视的。
按照中国传统史观,尤其是罗贯中的史观来说,历史本身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还是循环的。就比如汉朝历史,秦末豪杰并起,最后高祖得了天下, 传到哀帝平帝天下又乱了,后来有光武帝起来收拾局面,再过二百年就是汉献帝,天下再度进入混乱的局面。在这些分分合合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仁”与“奸”这两个因素。曹操是奸雄,而刘备则代表仁德,有仁德有奸雄,在他们之间的互相激荡中,才产生了能够改变局面,促使天下由“分”再到“合”的一个趋势。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解释。
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留给罗贯中的创作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况且他还是要遵循《三国志》的基本框架。在《三国演义》里有太多重要人物牵涉到曹操,比如他身边谋士,郭嘉、荀彧、贾诩、荀攸、程昱、司马懿、刘晔、杨修等,而且曹操和刘备、关羽也有大段对手戏。在这些情节里《三国演义》不能背离《三国志》,必须要把曹操看重人才的价值观呈现出来。于是,在小说中能够看到这样一位奸雄对关羽如此敬重,原来是因为关羽忠于刘备,上升到忠于一种道德和原则的地步,关羽越是忠于刘备,越是不愿意背叛刘备投靠曹操,曹操反而越是对关羽敬重有加。正是这些故事修正了曹操作为一个奸雄的形象,使得“脸谱化”的人物同样具备了另一种层次感,从而脱离刻板、浅薄的认知。
罗贯中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今天的小说理论,比如伊安·福斯特的“圆的人物”,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他不是追求各种复杂的情绪和动机,让人不能一眼就看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按照那样的维度和标准,《三国演义》的人物会是一种失败的示范,因为它的人物趋于平板。但是罗贯中所追求的恰好相反,就算某个历史人物原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在历史的记载中,他做了很多不太一样的事情,按照“讲史”的传统和原则,都要努力把他写成“扁平的人物”。也就是就算他有可以作为圆形人物的条件和材料,经过整理收束之后,呈现出来的将会是一个简单的、从整体上易于把握的答案。
罗贯中懂得如何运用《三国志》里曹操各种不同的,其实非常的立体,来自于不同的动机,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反应,通通都归结为一个“奸”字,一切都是他奸诈算计的表现,最后就构成《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而处在曹操对面的刘备,则是仁德的化身。
刘备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不是那么仁德的事。比如,刘备在最落魄的时候投靠了曹操,曹操接纳他,曹操还重用他,但是当他要离开曹操的时候完全没有道义上的压力。可是《三国演义》的刘备呈现出来后,不会让人感觉到刘备对曹操有不仁德之处。
在历史的解释上,《三国演义》简单的划分了正、邪的阵营,一边是奸雄,另外一边是仁德之士。照理说应该是正义战胜邪恶,仁者无敌,奸雄就该得到恶果,仿佛这样才是对的。于是《三国演义》沿着这条路线,把这个主题不断地彰显出来。刘备因为仁德,而取得荆州,向北打败了张鲁,向南打败了刘璋,进入蜀地,取得益州。可是到头来天意还是大过于人物的意志和努力,总有更高一层的规律是无法扭转的。
刘备在去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先遇到了司马徽,司马徽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一边是仁者无敌,但是另外有一条历史规律,却是个人无法抵挡、无法改变的天下大势。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里的两个“必”字就说明了这种规律的可怕。纵使是刘备这样的仁德之士,纵使他得到了诸葛亮这种人才的辅佐,也都无济于事。
一方面把刘备、诸葛亮说得那么好,最后又要让他们失败,这是《三国演义》给出的一个历史解释,这种解释是《三国志》无法给出的一种高度的悲剧性。
只从结局上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样一个悲剧结果,所有的读者从一开始就已经预知了这是怎样一个故事,都已经为最后悲剧性的结局做好了准备。这实际上是对罗贯中本叙事能力的一种考验。考验他如何让读者在已经知道结局不会是大团圆,结局会带来失望,甚至走向黑暗的预期里,还愿意读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三国演义》,就可以看到它的戏剧性是建立在双重的逆转之上,一方面是代表仁德一方最后是要倾覆的,这是一重逆转。另一方面,它在倾覆之前,其实一直讲述的是反败为胜的故事。因为仁德一方不管如何弱小,不管处于怎么样的劣势,都不应该放弃希望,这是第二重逆转。
在诸葛亮登场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样一种双重逆转的基调。刘备三顾茅庐,给了诸葛亮超出预期的礼遇,同时利用张飞、关羽两人的反应,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诸葛亮在这里是处于相对弱势的“胜者”。同样,刘备相对于曹操处于弱势,遇到诸葛亮之后,却够让处于强势的曹操在他的面前低头。
然而,这一路的逆转,最终仍要服从早已写在《三国志》里历史的答案。到头来,你的仁德,你的智慧,所有的正义和意志,所有的努力和希望,都逃不开一句“天下大势”。那是历史的宿命,那是时间的法则,英雄都被浪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
ps.很久以前的笔记修改一下发出来,大概从成书、语言和结构上,笼统的说明《三国演义》为什么不是小说的观点。各位姑妄听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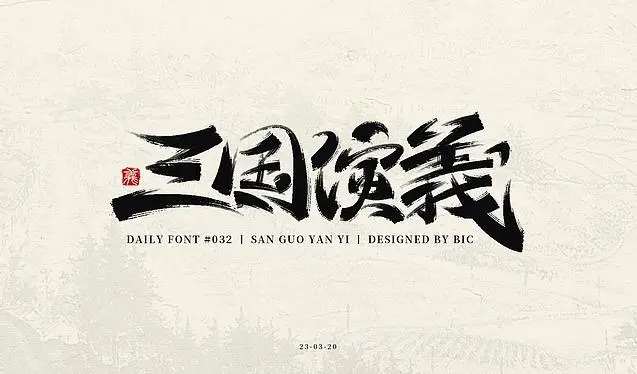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