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前,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叟,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这篇文字为《山静日长》。字字可喜,使人流连。古人留下的字,在故纸堆中依旧清晰,而幽远情意恐已在时间更替之中再难寻觅。隐遁生活在任一时代中都只是逆流和孤立,而与之映衬的“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却是主流。集体依靠迅疾而粗暴的力量向前推进。即便有人另辟蹊径,背离大多数人的归宿,在扑面击打的浪潮之中做不合时宜的事,其根本也只是一种个人选择。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醉眠》的诗句,清简如溪水中的松影,使时间循向缓慢,放空。这种变化需要内心的基底作为支撑。在缓慢中有丰富的流转,在放空中有笃实的基底,如此,太古和小年的感受,才不至于成为另一种寂寞的负累。清醒则时时逼迫出内心漏洞。佳境之前,原是险道。文字背后,唯见承当。
被湮没的古时,热衷于插花、焚香、点茶、挂画的日子,手工逐一制作出端正的纺织品瓷器漆器和食物,尊重四时节气,对万物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对风雅和优美投以深深爱慕,对高洁和矜持的情操不失信仰……这样的辰光貌似已一去不复返。被电视新闻、互联网、科技电器、虚拟空间、化学污染……种种新世界的衍生物所包围的我们,又可以对历史及传统作何欣赏、表达、维持和保护?
彼时有缺,也有光华。古今对照无定论。被吞没和推远着的价值观,如夜空中流转星光逐一熄灭。我们也许已忘却抬头看一看天空,寻找星辰轨道,感受它遥远时空之前迸发的光耀。而这光耀仍在等待。
因此,古书、古物、古人、古事不妨重提。
才有了这本关于古书的采访的开端。
庆山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北京
《古书之美》原本是安妮宝贝(现在改名为庆山)为《大方》所做的一篇采访。在此之前,我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上百家总有。很多记者在提问前会做一些功课,那些所谓的“功课”,通常是从网上找一点关于我的介绍,采访时基于那些介绍,换种提问的口吻或方式,其实都大同小异。而我也会像做命题作文一样,把他们想听的话复述一遍,谈到最后都是套路式的回答。
但安妮的采访不一样,从未有一位采访者像安妮这样认真。初一见面她就跟我说:“关于你的资料,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别人问过的我不想重复再问,我们可以另外谈些别的吗?”我说当然可以。她提问的角度也跟以往的采访者很不一样,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因此倾吐的欲望大增。以往我接受采访,很少超过三个小时,而这次采访前后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安妮对待这件事的认真,超出我的想象。
甚至有一次我去上海买书,她也提出跟我一起去:“我能不能跟你一起?我不会影响你谈事,也不参与你的事情。我只在旁边客观地观察你,然后客观地记录下来。你也别介绍我是谁,就当一个陪着办事的人就行了。”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向博古斋买了一批书,商谈书价时,安妮就在一边旁听。卖书的人很忌讳,一直问她是谁。我说她是一个圈外的朋友,也来出差,我们有别的事要谈,碰上了,就带她一起来了。对方放下心来,继续跟我谈书价,她就在旁边听着。晚上有人请客,一大帮人吃饭,她也跟着,就在那听我们侃大山。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样一种认真做事的态度。
采访持续进行了几次,录音量很大,整理出来有几十万字。最终出版时只保留了不到十分之一。出版方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舍,删改,反复多次,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从几十万字删到几万字,现在想想都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
可是这么多人费了这么多工夫整理出来,要刊登了,《大方》却停掉了。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可惜,费了这么多工夫,谈了这么多内容,不如把它编成一本书吧。可是,书与杂志专栏还是很不一样的,就又开始新一轮的修改,对内容也进行了增补,比如增加了介绍藏书知识的《古书收藏》部分。出版方还让我选十种认为有价值的书,跟止庵进行对谈。但书选出来之后,编辑和安妮都认为,这些书太过专业,能看懂的人很少。而《古书之美》的定位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本,在不了解的人眼里,一千万一本的书和一千块一本的书,没什么区别。甚至很有可能一千块一本的书,普通读者更容易接受。于是她们重新开了一个书单,让我来写。
写书要有感觉,写书跋同样要有感觉,而今强迫自己写几本没感觉的书,“为赋新词强说愁”,确实有些痛苦。以前写的最多的是藏书书跋,选的都是我认为有价值、有故事的书,并且是别人没写过的。像《红楼梦》,红学家遍地,我也没有什么独到的高见,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觉得无从下笔。而且写的过程中被编辑否了数稿,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出来的时候,觉得这样一本书,既不是大众读物,也不是学术著作,只能算是一个入门的小册子吧。没想到卖得这么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来,我确实不太了解图书市场,不太了解一般读者的口味。
当然,《古书之美》之所以能够这么畅销,百分之八十要归功于安妮。她的读者很多,而我只是个小众的爱书人。不过,从《古书之美》这本书上我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开始更多考虑写法的问题。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对自己的写作做了一些调整。我开始采用两种不同的文风,写学术著作时力求谨严,写其他类别的书则力求通俗易懂,专业走专业的路子,普及走普及的路子。在此之前,我总想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结果两头不讨好:学者认为不够严谨、不够学术,大众则认为太晦涩、不易懂。既然如此不如分开。比如,在有些书里,我开始以调侃的方式加入些藏书的掌故,倘若是正统的藏书史,这些都是不能收入的。
……
在受伤以前,我只是把写书当成我的副业,所做的工作多是搜集原始材料,有所感时就写一些,系统梳理总想留待以后。但在这件事之后,我开始加快步伐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在当下。我告诉自己能做就先做,别求全、求完美,别留遗憾。以前没有写完的一些半截书稿,我开始一本一本写完。除了每年一册的《芷兰斋书跋》,我做了《古书之媒》的系列访谈,也在媒体开设专栏,讲自己的得书记、失书记。同时也陆续把这些年寻访藏书家之墓、佛教遗迹等的所得整理出来。近年来,我基本把时间全都耗在了写作上,写得越多想写的也越多,丝毫没有厌倦之感。写作状态也比较自如,几种著作穿插着写,书跋写累了就去写访谈,或者整理寻访。
很幸运,我现在还活着。死是早晚的事,该受的苦难也逃不掉,但既然活着,那就尽量活得快乐。受伤之后,我对收藏古书这件事的喜爱并没有减少,那就继续享受这个过程吧。
而今我继续着自己的寻访之旅,并且题目越做越大,这很符合我好大喜功的禀性,经历了这么多,我已经用不着“三省吾身”来改变自己,既然喜欢这样做事,那就由着自己做下去吧。老天已经给了我一次苦难,按照能量守衡定律,它总要给我一些补偿,真希望自己能够快乐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
前段时间林妮娜给我来电话,她说不断有人询问《古书之美》,所以决定将此书修订再版。新版除改正之前的错漏,还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为了不增加我的负担,会从原采访稿中摘出一些上次未用的内容,放在修订版内。感谢她的体谅。而后她将跟佛经有关的一段对谈发到了我的邮箱,让我做一下校订。如今再看几年前的言谈,我能够明显体会到自己在一些观点上凤凰涅槃式的变化,修订时感觉削足适履似的放不开,于是彻底放弃,按照安妮当时的提问,重新做了回答。由此推及《古书之美》整个访谈部分,当时所言跟今日所想都有较大差异,但如推翻重来,则会是全新的一种概念,与这再版修订本完全不搭边。以这种思路想下去,文中的回答就是我当年的思想,没必要为自己的不成熟做任何遮掩,于是我决定一字不改,除了增加的部分,其余原样呈现给大家,以供各位读者批评。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社会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着巨变,这让我变得不能从容,时不我待的感觉与日俱增,这同样是一种不达观吧。且不用管它,就让我继续不达观下去吧。
韦力
二○一七年三月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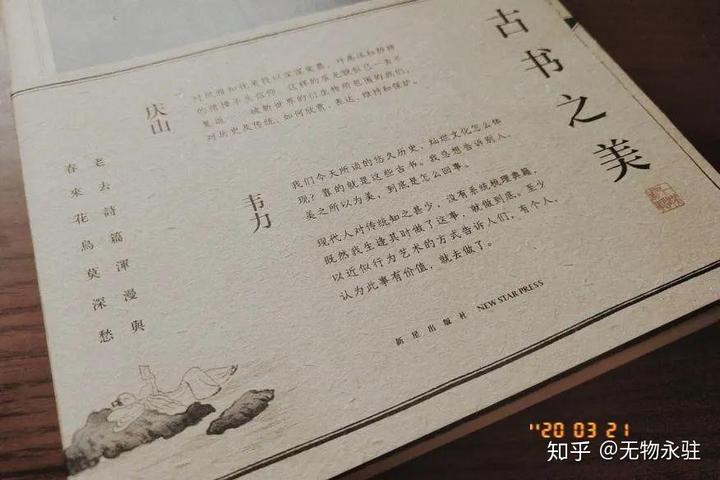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