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正式提出“伪书移置说”之后,不仅纠正了胡适对“伪书”的认识偏差,还深化了对“伪书”的认识。因此,此说得到了容媛、齐震、陈恭禄等人的基本认可。而吕思勉、翦伯赞则在批评或认同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伪书”中还有“真史料”的观点。要而言之,顾颉刚的“伪书移置说”是一个科学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
大凡一个突破性学说问世之后,都会产生一定的反响。因此,在对“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学术渊源与基本内涵进行了一番研讨之后,有必要对该说的反响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近代以来,在中国古书考辨工作上,最先具有自觉意识的是胡适。1919年2月,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但是,要将假史料完全弃去不用。就中国哲学史而言,《易经》“乃是一部卜筮之书”,故“全无哲学史料可说”;《尚书》“没有信史的价值”;而只有《诗经》因书中的日食得到了证实,才“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因此,“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于今来看,关于胡适的这一“截断众流”的做法,虽然被蔡元培认为是一种“扼要的手段”,但实则缺乏彻底的“历史的眼光”与“平等的眼光”。

早在1924年7月,杨鸿烈在《中国伪书的研究》中即指出,“自来处置伪书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是“放任派”,“这派对于真的古书和伪的古书都一视同仁,毫无偏私,他们以为读书便是读书,何必劳精费神去管他是真是假”。与这一派不同的是“排斥派”,“这派对于已证实的伪书固然是严格的排斥,就是疑性很大的古书也不征引”。其中,胡适是以“排斥伪书”“求得信史”为目的的“先觉”,其“在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连《左传》《周礼》《尚书》等可疑的书都一概不征引”。这种办法虽“是得当是合理的”,但“我们还想进一步来将所有伪书像废物似的利用来丰富史料的内容,设法把所有伪书造作时代的‘或然数’考证出来”。于今来看,杨鸿烈的批评颇能成立。要而言之,胡适在“审定史料的真伪”之后,不仅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伪书”和“真书”,更没有以“历史的眼光”将之置于“作伪”的时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可靠的“真书”。较之胡适,顾颉刚的这两种眼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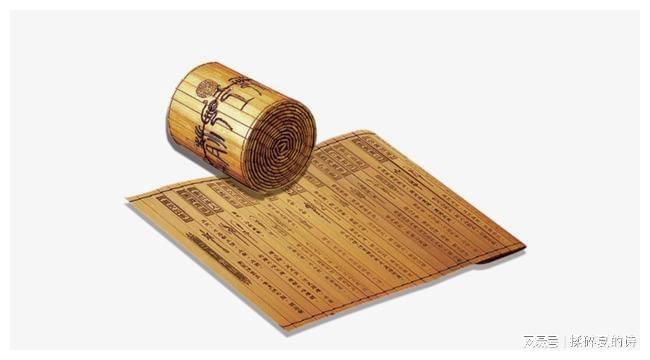
早在1921年1月,顾颉刚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说:“因为想做史学,所以极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1935年9月,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中则直言:“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②不过,承前所述,“审查史料”之后,顾颉刚并不主张将之“除去不用”,而是将之置于造伪的时代,使其成为“绝好的史料”。由此来看,“伪书移置说”之提出,不仅消极地纠正了此前胡适的“伪书”认识偏差,更积极地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科学认识。科学的认识一般会得到人们认可。顾颉刚“伪书移置说”提出之后,即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正面回应。最早注意到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是容媛。1931年12月,容媛对《古史辨》第三册进行了简要介绍,注意到顾颉刚在该书《自序》中述说的古书“建设”“只是恢复其原来面目”,而古书“破坏”“只是移出其所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出现之时代之意”。对此,容媛表示:“古史材料日出不穷,诚不当以古书自限,然古书既占古史之重要地位,则古书材料之分析及其时代之考定,确为今日急迫之需求。”由此可见,容媛对于“伪书移置说”是颇表认可的。继容媛之后,还有一些学者接受了顾颉刚的“伪书移置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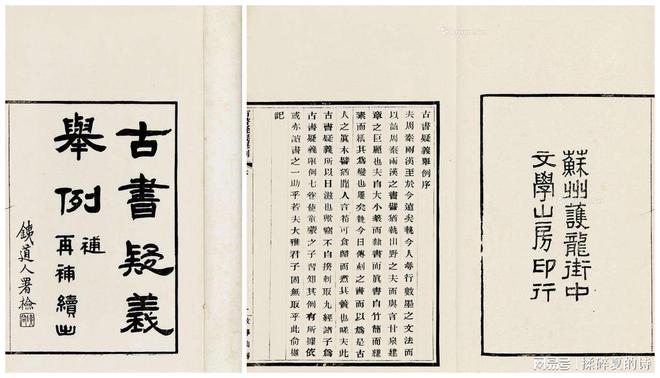
1934年6月,齐震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一文中先是强调,“传说与伪书的本身也是具有史料的价值”。比如,“《列子》是晋人伪撰的,虽然不能代表庄周以前列御寇的学说,但用来讲魏晋间的哲学思想是极好的”。又如,“《西京杂记》是晋葛洪作的而伪托给刘歆,拿他讲西汉的历史便错了,用他来推测晋人的风俗制度便有相当可取的材料”。之后,齐震则表示:“谈到史料问题则顾颉刚的《古史辨》是不可不注意的,他用校勘学做基本方法,在过去的史料(记载)中证明他所发见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条定例。”本来,“顾颉刚的史学,与其说是‘史学’无宁说是‘史料学’。他对于古书的素养比较深,所以他关于材料整理的见解是可取的”,而《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就是一个例证。由此来看,齐震之所以主张《列子》《西京杂记》等具有史料的价值,当是受到了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直接启发。除齐震外,受“伪书移置说”影响的还有陈恭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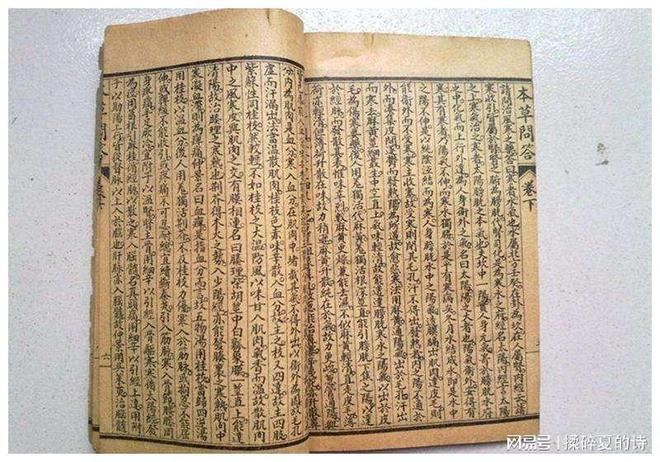
1936年,陈恭禄在《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中指出:“上古典籍存于今者,数实无几。”孔子以前之典籍存于今者,仅有《尚书》《周易》《诗》《春秋》。其中,“《尚书》之可信者不足二十篇,均为殷周文字”。至于“后人伪托之书,关于思想者,定其著作年代,尚可作为某时代之思想,伪托之史料,除特别用途而外,决无一顾之价值”。此外,陈恭禄在论及《诗经》成书之年代及其真伪可信之价值时专门提到了《古史辨》第三册中顾颉刚、俞平伯的观点。由此可见,陈恭禄之所以认为伪托之书有特别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影响。不过,较之上述学者的单向接受,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学者的修正与进一步发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吕思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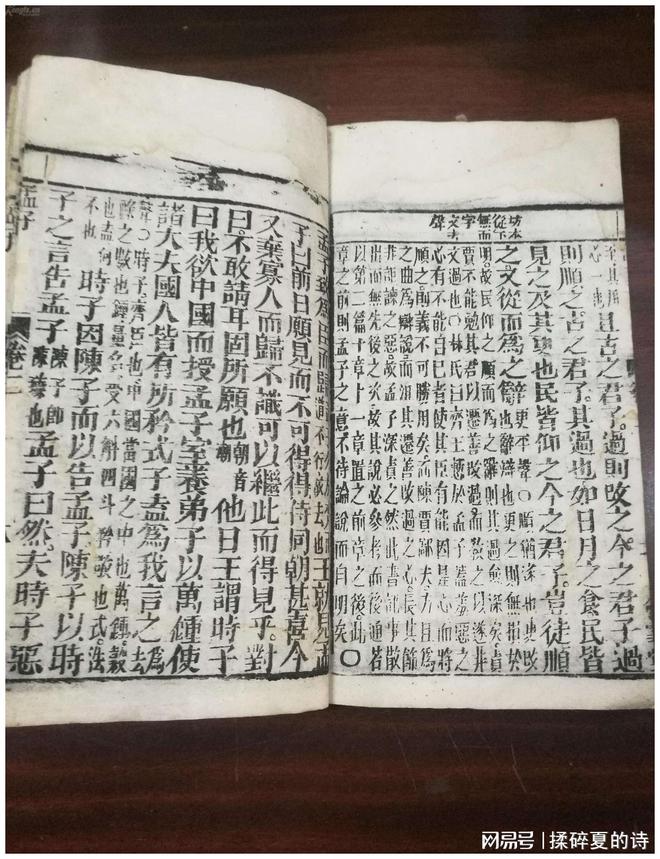
1941年12月,吕思勉在《先秦史》中对“古史材料”进行“料检”时批评说,近二十年来,“疑古”之风盛行,“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而且,“伪书仍有其用”。比如,在经书之中,《尚书》中《尧典》《禹贡》等,“决为后人所作,然亦可见其时之人所谓尧、舜、禹者如何”;《周官》“盖战国时学者所述”,“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固“诬”,然“战国时制者,独赖此书之存”。又如,在子书中,“《家语》《孔丛子》虽为伪物,然古书无全伪者,除以私意窜入处外,仍多取古籍为资,实足与他书相校勘”;“《列子》乃晋人伪书,然亦多有古书为据,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才,而尤可与《庄子》相参证”。于今来看,吕思勉对“疑古”的这一不点名批评,或是一种误解。其提出的“伪书”存有作伪时代的观念或制度,与前述顾颉刚的“伪书移置说”并不冲突。不过,吕思勉并不囿于这一认识,而是进一步认为“伪书”之中“多有古书为据”。除吕思勉之外,进一步发挥“伪书移置说”的代表性学者还有翦伯赞。
1946年10月,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讲到“史料择别与辨伪学”的时候指出,“到近代,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其中,“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而“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并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伪书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而要伪托古人,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而且,“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因为,“史前时代的人,尚无文字。没有文字时代的人,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不论是载于真书,抑或载于伪书,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因此,“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定,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
结语
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由此而言,翦伯赞不仅认识到“伪书”置于作伪时代的史料价值,还进一步提出了“伪书”在史前时代的“旁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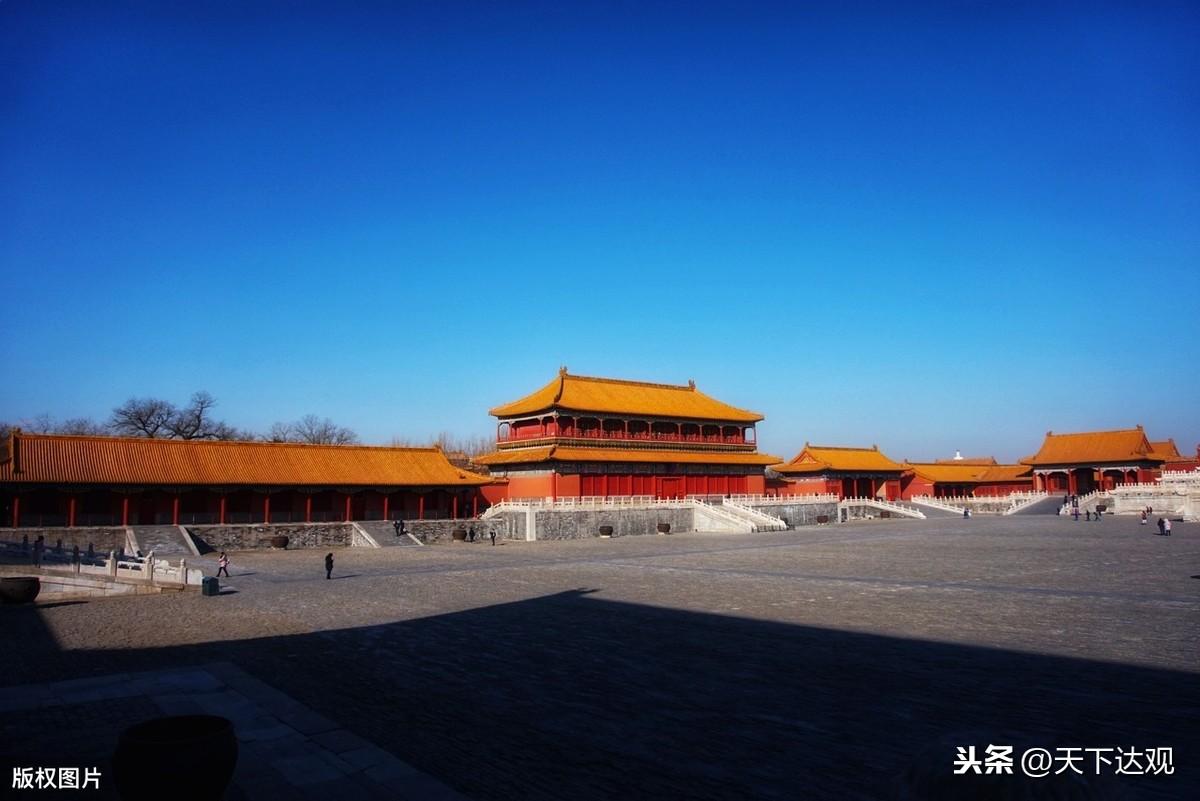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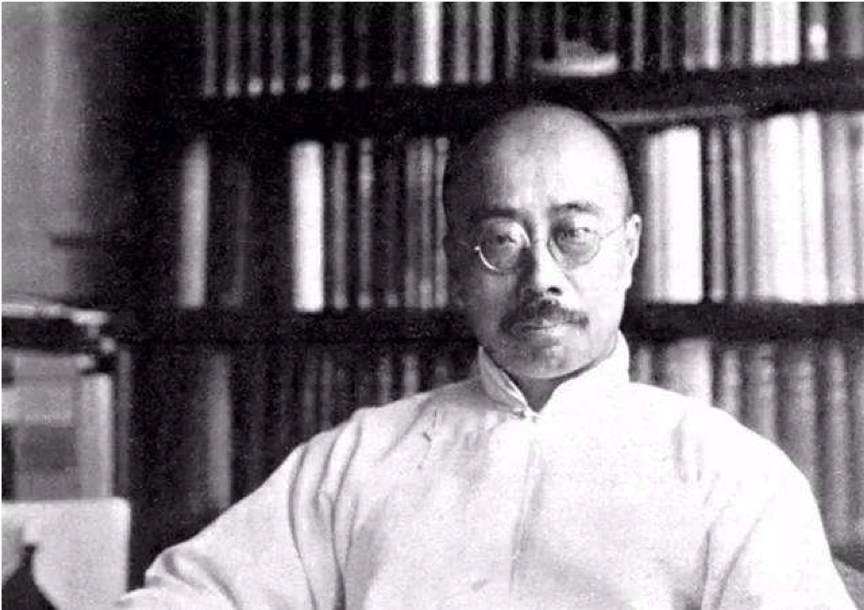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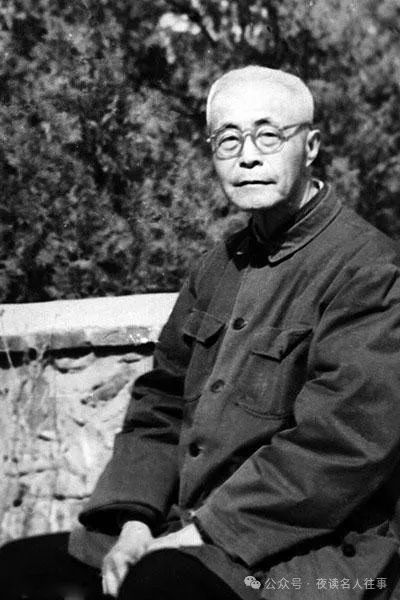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