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引申一个话题:现在的学界,包括中国学界,也包括欧洲学界,在研究中国跟欧洲关系史的过程中,多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研究中国跟欧洲的交流。凡是研究意大利传教士的,多都是意大利学者;比利时的学者最关心的就是来到中国的几位比利时传教士的情况。贸易方面的情况也一样,比如荷兰学者更加注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情况。这其实是有蛮大的局限性的,我认为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很多在16、17世纪还不存在;第二,耶稣会本身就具有跨国属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传教组织,其会士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第三,在文化交流中,传到中国的欧洲文化的国别属性并不是很明显,它是一种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是欧洲商业文化、物质文化。而中国文化被介绍到欧洲去,在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反响和被接纳的程度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不具有显著的国别性。因此用现在的国别观念去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和欧洲关系的历史,就会有一种割裂感。
接下来讲一下这些文献的形态。这些文献有书籍、书信、报告、账单、名录、地图,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文献,你如果仔细去爬梳它们,经常会有一些让你意外的发现。大部分的文献都是手稿。已经出版了的文献是占少数的。手稿部分又分为原件和抄本,抄本部分又分为不同时期的抄本,有的文献既有手稿又有印本。总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印本、抄本体系。我们除了要掌握欧洲各国的语言,还要掌握那个时期的语言,毕竟近代早期的欧洲语言跟现在不一样;还要掌握手稿的识别,能够识读不同手写体。
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经常会对不同版本、抄本之间的差异感兴趣,会去问一句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一个抄本里面这些内容在另外一个抄本里面不存在?我读到的一个文本,就看到有一段被划掉,而且旁边写着“本段不准抄写”。这一段话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教徒自杀的,这是负面新闻,所以不准抄写。要知道不光中国有文字审查制度,欧洲的审查制度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宗教裁判所的审查力度不比文字狱轻。
至于明清时期西文文献的内容,传教士书写的主要的就是传教事务,可用于研究传教史;商人们记录下来的是贸易事务,可用来研究中外贸易史;外交使节团留下的文献,可用于研究中国跟欧洲的外交关系史;这都是很显然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是超越这些内容和领域的,会涉及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我们把其称为民族志的内容,包括历史、语言、风俗、地理、物产、经济、宗教、不同人群(比如儿童、妇女、士绅、道士、和尚、藩王、太监)等。这样的文献很多,应该甚至必须被纳入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中。它们的作者是欧洲人,带着欧洲的文化眼镜,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们还会记载中国的时事,这种消息传到欧洲后是被当成新闻的,这类文献也应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西文明清史文献,不只是涉及中国跟西方交往的那一部分的内容,还包含纯粹的中国史内容。
这些文献最主要的馆藏地都在欧洲,基本上所有西欧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都可以找到与中国有关的西文文献。例如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甚至是维也纳大学图书馆,都能找到有关中国的文献,分布非常广泛。这些文献无论产生于何处,目标读者群都是欧洲人,绝大部分都要寄回欧洲。当然在亚洲不少地方也有保存,比如果阿,长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走了以后,一部分葡文档案还留了下来。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藏有不少西班牙文文献,其中也有蛮多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美洲多处也有收藏,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就找到了很重要的西班牙文材料,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何大化《远方亚洲》的一个抄本。墨西哥也有档案馆藏有与中国有关的西文档案。使用前人整理的目录是一个查找这类文献的捷径,比如来华传教士的文献,钟鸣旦主编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里就有很详细的目录。我个人“安身立命”的两套文献,一是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大概有6万页左右;二是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汉文献》中的西文部分。
那么这些外国人记载准确吗?可靠吗?傅斯年就讲过一段话,“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长短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致说起,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传闻既易失真,而外国人之了解性又每每差些,所以我们现在看西洋人作的论中国书,每每是隔靴搔痒,简直好笑。然而外国的记载也有他的好处,他更无所用其讳。……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史学方法导论》)他说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互有长短,我是同意的;但说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我不太同意。他接下来说我们自己的文献未必客观,这个我是同意的,然而“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这个我又不同意,因为恐怕外国人的记载也能见其精细,中国人的记载也可以见其纲领。所以他说考察文献既需要显微镜,也需要望远镜。无论是显微镜还是望远镜,都与我们今天谈的视野是很有关系的。
你去查英语词典,耶稣会士Jesuit,有“阴谋诡计、骗子”这样一层意思。那么他们的记录会不会有很多谎言和编造、杜撰的内容呢?很多学者对耶稣会的文献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从我个人的阅读和使用经验来看,我认为耶稣会士留下的文献,记载的内容具有极大的选择性,他们选择记什么,选择不记什么;但是他们记录下来的部分大体上是真实的。我还找不出几个耶稣会士编造谎言的例子。很多耶稣会士的记载,与中文文献一对照,常若合符节。商业文件就更不用说,因为他们要做生意,他们的账单、统计数据,你没有办法去质疑他。
西文文献对本土史料的补充意义
在谈到西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时,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可以补中文史料之不足,理由是中文史料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常常失载,而这些常见的事物对来华的欧洲人而言,可能就不常见,因此也就可能被他们记录下来。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其实只是一种逻辑推测。至于西文文献到底可以补充哪些中国史料的不足,以及应该怎么补,如果没有大量研读西文文献,就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以下我就根据自己研究的几个案例,还有前人学者研究一些案例,简单谈一下。
第一,中文文献跟西文文献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曾经研究过徐光启,写过一篇文章。徐光启我们都知道是晚明的科学家,这是我们愿意承认并极力塑造的一个形象。但他另一个身份,就是他后三十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去看有关他的西文文献就会发现,大量的记载是关于他信仰如何虔诚、他对教会的支持以及他的信仰实践,比如他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旁边放一个苦行的鞭子,还要抽自己,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符合的。如果后三十年他没有信仰天主,他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科学成就,其主持编纂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有大量西方知识。但中文文献在谈徐光启的时候,甚少谈他的信仰方面,而西文文献则较少谈他的官员、科学家的一面。中西文文献的侧重点不同,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徐光启的历史形象才能比较完整。
第二是中西文献立场不一样。我曾研究过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这个人。中文文献因为他是太监,就把他与大明江山的丢失、明朝的灭亡关联上,认为阉人误国,所以他是反面的形象,是被批判的对象。但西文文献则记载他多么虔诚和忠诚,他为四朝皇帝效力,勤勤恳恳、忠诚有加。庞天寿效力永历皇帝的时候,内心也曾动摇,他就问他的老师德国耶稣会士瞿纱微,说我有点坚持不下去,太难了,要不要继续为永历皇帝效力?瞿纱微跟他讲,一定要为永历皇帝的效力,这是应该做的,也是天主教的要求;只有这样,即使你死了,你也会为我们教会带来好的声望,我们会记得你是一个忠君的、虔诚的信仰者。庞天寿听后痛哭流涕。西文文献描述得非常生动,他抱着瞿纱微痛哭,说一定牢记老师的话,一定会坚持下去。传教士文献突出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中国文献记载则是批判的立场。两方面的记载都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对这个人物的评价都有一些有失偏颇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两方面的文献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求得对庞天寿这样一个动荡时期的人物更加公正的历史评价。
第三,我们考证史实过程中,西文文献可以补充一些证据。我举两个例子,也都是我写过的文章。我在读葡萄牙文献时发现一个人在崇祯朝历局里工作,后来回到他的家乡武昌,把天主教带到武昌,建立了传教驻地,而且一家人都领洗入教了。西文文献记载这个人洗名叫Jacob,而且还写出了他的姓,就是一个U;还说崇祯十年(1637),他弟弟中了进士,所以他才会觉得北京有人了,就不用他了,所以才选择回武昌协助建立教会。西文文献就有这么多线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就要去中国文献里面找这个人。我翻查明代进士题名录,在崇祯十年考上进士的300多个人中找籍贯是武昌的,发现一个叫邬明昌的人。我又到《崇祯历书》里找姓邬的,果然找到一个叫邬明著的,也来自武昌!这样中西文献一下子就对应上了,邬明著和邬明昌肯定是两兄弟。邬明著在历局里面工作,邬明昌后来考中进士,然后邬明著回到了他的老家武昌去,并邀请传教士前往开教。西文文献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否则我们也不知道邬明著是一个教徒,且对天主教的传播还发挥了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金声,陈垣、方豪和黄一农先生对金声都有研究,大家都推测他是一个教徒,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都只能说金声很有可能是教徒,因为要谨慎一点。我读西文文献时,发现一个名叫Agostinho Kim的教徒,而且其所有经历跟金声一样。既然找到了洗名,则金声入教即可确证。西文文献有时能提供意想不到的证据,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因此迎刃而解。
这三个例子都要求我们中西文献互证,这是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文献互证,很多学者都曾强调过,陈寅恪先生“三重证据法”,其中一个就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那就是中西文献互证。傅斯年说,假如有人问整理史料的方法,我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是涉及你研究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史料你都要比较一下。西文文献作为一类文献,就是要用来与其他的文献记载互证。
第四个例子是数年前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的博士生刘耿做的。他葡文很好,他的研究使用了很多葡萄牙文献。他写了一篇论文叫《从王国到帝国:十七世纪传教士中国国体观的演变》,这篇文章是针对欧立德的观点写的。欧立德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新清史领军人物。他在中国好几个地方都发表一个演讲,叫做《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后来他的演讲内容发表在2014年的《读书》杂志上。他认为,中国从王国跃升为帝国,与满清入关后建立多民族联合政体的大清国有关。换句话说,明朝以前都是王国,清由于是多民族国家,所以是帝国。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新清史一个重要的观点——清国不是中国,就多了一个证据。刘耿系统梳理了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中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各种称谓,用大量证据证明了“欧洲人指称中国确实存在一个从王国转变为帝国的过程,但是,该转变并非与明亡清兴同步,转变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清帝国的建立,而是与传教士对一脉相承的中国认知的深化有关”。这便否定了欧立德的结论。可见,西文文献的引入,加深了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纠正了一些带有预设性质的看法。
第五个例子关于清代中国官方对外国人的态度。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论著都说,中国官老爷对外国人都是很歧视、很傲慢,甚至很粗暴的。美国学者范岱克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黄埔与广州贸易》(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该书使用了大量的西文原始档案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本书各章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案例都表明,中国官方对他们的外国客人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包容。”我一看到tolerance这个词,一方面非常感动,另一方面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识。19世纪西方人武力攻打中国,一个原因是“你们歧视我们,一直是中央帝国高高在上的样子,对我们不包容”,但是范先生用大量的文献看到在黄埔口岸、在广州,很多外国人,中国官方对他们都非常包容,非常客气。偶尔会发脾气,但是实际行动上对他们都很友好。这与我们以往的认知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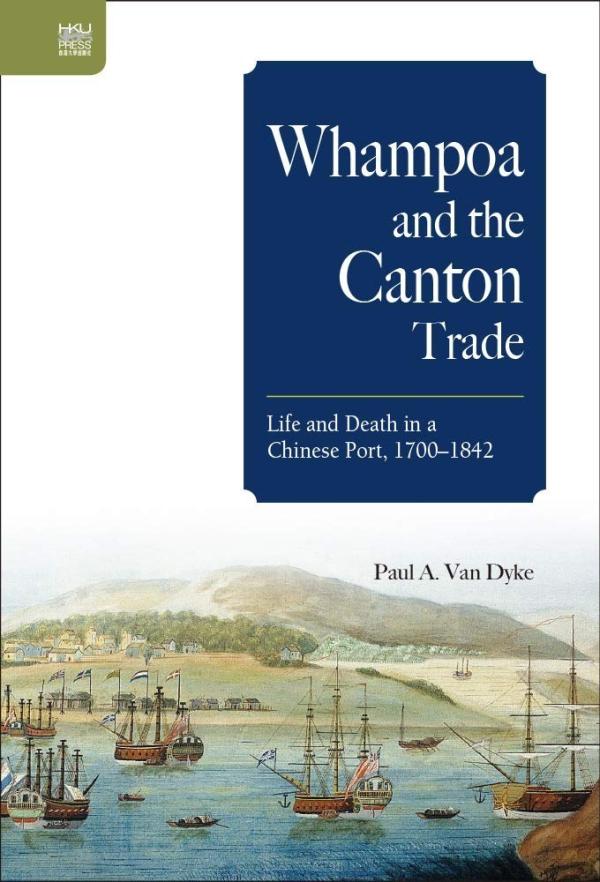
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
这两个例子说明通过大量西文原始文献的分析,我们有可能推翻流行的观点,获得新的认知。但是西文文献的价值仅限于此吗?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海量的西文文献,是否有可能为我们带来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我就是不满足于西文文献仅扮演查缺补漏这样的一个角色,尝试谈谈其在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方面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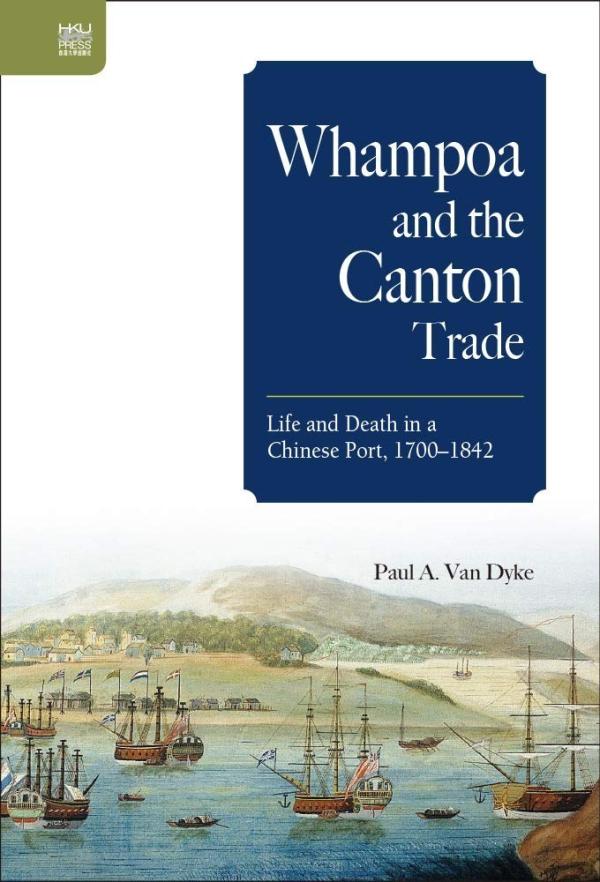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