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沈从文痛苦而又决绝地告别文学,投身于文物研究事业。他的文学著作因与时代“游离”而销声匿迹。他自己也屡次声明,我的作品过时了,不值得再提。但他的作品价值还在,还有人记住它,特别在海外,还得到重视和研究。
一次,黄苗子告诉他,在国外,一位研究他的学者得了博士学位。这时,“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这个极其生动的细节,真是点睛之笔。这个小个子、说话轻轻的、总是笑眯眯的低调老人,知道自己的人生塞满了货色——他在岩石和冰层中一级一级地凿出令人头晕目眩的阶梯,直达顶峰。唉,天才的卑谦,等于骄傲!
“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从湘西脱离旧军队,呆头呆脑跑到北京,异想天开地想当一个作家。许多年后,他写信给学生汪曾祺说:“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多大的口气啊!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后面的括号里他又添上一句:“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真是太“狂妄”了!
晚年沈从文
但是接下来,他就行动起来了,不可思议地行动起来了。“在北京零下二十八度严寒下,一件破夹衫居然对付了两个冬天,手足都冻得发了肿,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还时常流鼻血;他不断地写,写,写。终于“这序幕的春云渐展”,有文章发表了,一本一本地出书了。尽管稿费版税低得可怜,可他仍然庄严认真地工作着。他觉得,“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想记录突过契诃夫”;“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
沈从文有着苗人血统的“野性”,感悟“生命”“人性”的敏锐天赋和独特视角,遣词造句、行文布局的不同凡响,赢得一批“欧美派”学者的认同和赏识;更重要的是,他有读者。
但在规整的文学园地里闯进一个异类,批评之声不绝:“有魔术的多产作家”——“你就是写得多嘛”。“前进派”的批评则是,“与人民脱节。”他多数时间是沉默,沉默里满是骄傲的不屑。但在私下里,面对亲爱的人,他是恣意的,发出生命本能的呼喊。1934年回乡探母途中给张兆和写道:
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
多么“骄傲”的“不骄傲”啊!
1930年,沈从文给大哥沈云麓信中说:“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形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1942年则说:“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
大约在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批道:“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1948年夏,沈从文一家与朋友在颐和园度假,小儿子沈虎雏对父亲说:你比不上托尔斯泰。沈从文说:“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小虎雏“因为礼貌关系”,不便说“吹牛”,就吃惊地说:“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沈从文见小虎雏正在看他的《湘行散记》,便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年青”,也就是“永生”的意思。
届时,时局动荡;在香港,郭沫若等人对沈从文的围攻已经开始。但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对过去和未来没有茫然,没有动摇,依旧坚定,依旧“傲傲然”。
“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他投身于文物研究,已经不再是作家了,作品也被焚毁,文学史上即使偶然提及,也只是几句丑诋。但他曾经辉煌的文学创作仍然纠缠着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摩挲叹息,孤芳自赏,挑起犄角,沉吟不已——莽莽苍苍中,他是“明白”的,从而高昂。
1953年,开明书店销毁沈从文已印、未印的书稿及纸型。他非常痛苦,“在床上听悲多纹”,给大哥写信:“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
1956年12月10日,沈从文出差在长沙,写信给张兆和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可惜可惜!”《三里湾》是当时写农村合作化的风行小说,沈从文“花了六毛三买一本”;但一看,只能连连感叹。
1969年沈从文以老弱病之身,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迁徙六次,受尽折磨,高血压、心脏病、肾结石三病并发,差一点“完事”。经过不断请求,1972年2月终于获准回京治病,他又投入文物研究。当年7月22日写信给小儿子,讲了生活和工作的各种情形,忽然笔锋一转,骄傲地说:我过去“十年的低头苦干,结果就把一大群善于诪张为幻的‘作家’远远的抛到后边”。
1977年12月7日,给小儿子信中又说:“间或翻翻自己四十年旧作看看,如同看契诃夫、莫泊桑作品,料不到竟是自己一篇篇写出,且又一本本印成过书,在国内曾于某一时占压倒趋势的。”
汪曾祺与沈从文合影
沈从文也关注新文学的发展,时常发出尖锐的批评。1959年3月12日,给大哥写信说:“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正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1961年初,他住在阜外医院,集中看了一些作品,便大大地评论起来:“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统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看到几个短篇,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没有办法看下去。”
当时红极一时的《林海雪原》,他委婉地批评:只是“惊险”,“是《七侠五义》的习惯”。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有的是纷呈故事,“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至于诗……看不懂,无意思,不知说些什么事情。”他还批评文学评论、电影、电视,于是总结道:“我觉得这一切综合作成的影响,是不怎么好的。”
1974年10月24日,给小儿子信中说,我“过去四十年前,一个人可以用十年功夫,把作品支配以百万计读者的感情和信仰,现在尽全国名作家的努力,加上最高的称美,面对千万读者时,还是起不了应有作用”。
据著名作家林斤澜回忆,大约1960年代初,他与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寂寞,就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一些活动。一次青年作家下乡下厂后谈体会,最后主持人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他知道话不投机,还是不说为好——沈从文纵然肺腑间感受着天涯酸楚,脑海里翻滚着“警世宏论”,但仍像老憎入定,没有动态——其中的坚持和傲慢,别人当然懂。
就在1961年住在阜外医院那次,沈从文向张兆和发出这样的疑问:“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张新颖教授指出:“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的质问了。”1974年沈从文给小儿子写信又重复了这个意思:“搞文学的大都只注意到上面的意见,可不大注意到读者的情绪和要求。”——沈从文毕竟老辣,他是什么人啊!轻轻一点,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
沈从文曾孩子气说,“因为批评家过多,要求又过窄”,小说“只好让人去作了”。但文坛状况使他失望,像山中老虎看到猴子称王,他的手又痒了起来。1961年,禁不住对张兆和说:“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
——放弃文学,一直是沈从文不能愈合的伤口,一把火红的刀子。文学的魅惑一直没有消散,一直蠢蠢欲动。沈从文相信:树叶虽已飘落,风儿会把它送上天空,还会高高地飞翔……
1951年10月,沈从文去四川参加土改。他离开了风暴中心,为能参与历史进程,呼吸新鲜空气而振奋;特别是他爱过、讴歌过的河水山壑、僻野乡土,那些气息、声音,那些吹拂着的风,使他又激动起来。
船到汉口,沈从文给两个儿子写信:“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在巫山码头,面对雄奇景观,沈从文告诉张兆和:想在沿江小村镇“各住一二月,对我用笔极有用……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将“成为一种历史”。
沈从文与张兆和
到了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起伏的丘陵、返光的梯田、袅袅炊烟、褐色土地、淡绿色甘蔗林、透明潮湿空气,以及老妪、小孩、“白布包头蓝长衫”,“一切如童话中景象。”沈从文激动地写道:有些人物“已活在我生命中,还要活在文字中”;“我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者。”
1957年11月20日,沈从文致信大哥表示:“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还能写大作品。”
1963年入秋后,沈从文有一次南方之行,在长沙想起二千年前两个古人:
同样的阴沉天气,贾谊以卅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
他写信给张兆和:“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
即使在湖北干校那么艰苦环境里,他感到“生命可用已有限”,写信给年轻朋友徐城北说:“我也想到争抢时间”,“写廿卅个新型短篇,试试看,能不能突破自己过去限制,而且作来必超原来外面要求。”
他还有一些创作计划,想写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烈士的长篇小说(已酝酿准备了十多年),把不完整的长篇《长河》写完;还想写第二部自传性小说和回忆录等等,但“怕出问题”,终难下笔。惟一完成的反映土改的中篇小说《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因一些段落背离了时风,重现了往日的风采,也没有拿出来;直到他去世后,家人才发现。张兆和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
他给张兆和信中有许多创作谈。1970年9月10日在湖北干校,他忽然意识到,这些随手写出的感想,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因为许多是从个人长期实践中得来的”,“即或不尽合拍,也能具一格”,是有价值的。所以嘱咐张兆和不要毁掉这些信。
沈从文开口即称自己是“乡下人”。1933年主动为萧乾小说集作序,其中写道:“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哦,给“乡下人”画像,无意中给自己戴了一顶桂冠。
我的“个人目的远得很”
沈从文的后半生,在文物研究领域矗立起一座高峰,这座火山从新的地方又爆发了——他是感性的作家,居然能把抒情气质、诗意情怀与科学条理完美结合起来,创造得仍然丰富辉煌。汪曾祺曾经为他担心,“后来发现他‘另有一功’。”沈从文也是得意的。
当年他告别文学,决绝地到历史博物馆去——那是一个“冷”地方,他说“好像进了棺材”——的时候,刚从精神崩溃中平复过来,不免显得萎顿自卑,谨小慎微。但他的内心里没有惆怅,仍然刚健,还是一片生发气韵的热土。他认为,文物研究“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具有学术革命意义”。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下一代“作个礼物吧”。
漫长的日子开始了。他“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暧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未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下雨,即披个破麻袋”;“至少得有十二时在外”。在午门“灰扑扑”的库房里,他“有时拿手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像大盗杰西”。冬天库房里不能烤火,“穿堂风吹过”,冷得“黑抹布冻成冰疙瘩”。沈从文时常忘了吃饭,被锁在里面。——就这样,他摩挲了数不清的“花花朵朵,罈罈罐罐”,看了“过十万绸缎”。
他还走出办公室,主动到陈列室当“说明员”,一共十年时间。一个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做一个年轻人做的事,熟人见了不免“凄然”,只能偷偷躲开。西南一个老朋友来看他,见他正“弯着个腰声音嘶哑哑的”在讲解,“便红了眼”;沈从文反过来安慰了许久才了事。工作了八九个小时,送走观众,沈从文累得“胸部和腰部都如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但沈从文不以为苦,却“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汪曾祺语)。
就这样,他从古文化的实物中、讲解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崭新启示,开拓出文物研究新路。
而他旧日的同道,“都正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沈从文清楚,他们紧跟时风,完了;守住自己,也完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实在更无根基”。
他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实际上“我却脚踏土地过日子”——他沉默工作,内心满溢,他的头颅还是昂得很高。
更严峻的考验还是历史博物馆的人事关系紧张。他被视为“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不仅不被重视,还受到压制、冷落、侮辱、恐吓、“作践”,甚至训斥。
在1957年,沈从文给作协的一个报告里埋怨:“‘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
1950年代,馆里还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展出的八九是沈从文买的“废品”,其中有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四块钱买来的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的整匹暗花绫子。更想不到的是,领导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沈从文哭笑不得,但又“格外开心”——为同事的“恶作剧”、更为他们的学术眼光浅薄叹惜。这个故事,沈从文难以淡忘,曾多次提及,1974年写信给张兆和说:我的“工作正在实现中,而用得上买的那些‘废品’”。我不会对某些人“使用小手法陷害而难受”——他傲气地说:我的“个人目的远得很”!
在历史博物馆,他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为了一张照片,多年的老朋友、现任馆长韩寿萱正告他,这是损失国家文物,是违反宪法的!沈从文被迫写检讨,承认“对文物不知爱惜,造成很多损失”。偶尔,沈从文到文物局去看新收购的文物,被怀疑“打小报告”,有人隔墙威胁:“向局里乱谈馆中事,就是‘超级’。”沈从文再也不敢去了。他“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1975年春,沈从文向朋友抱怨:单位里有些人,“只乐意把我轰走”。
张新颖教授对此十分感慨,他这样说:“环境和条件的极端苛刻”。沈从文自己也说,这是“一种更加艰苦十分的战斗”,“就是一种战争!”我就在“那么一个寂寞环境和简直前途无望的工作上,钉住不动了”。他后来则说:“我是傻娃儿拾豆子——认准这块风水宝地了。”
——环境如此的“低气压”,沈从文当然会有内心的“风暴”,会有晦暗、脆弱和惶惑;但号角的召唤,他是一直听着的,因此总会有最热烈的心跳,总能跋涉昂扬,“百年长勤”。
这是多么强大的、悲壮的“沉淀力”和“排除力”,使他自我克服,自我战胜——高处的旗子仍然在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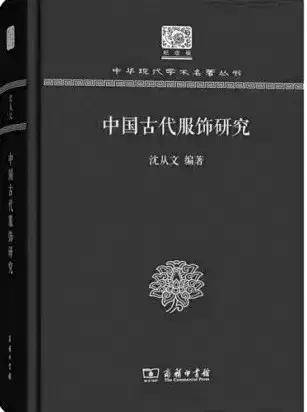
1974年,沈从文已经72岁了。他找到馆长,流了泪,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粗粗列举了二十五年所做的工作:
中国历代服装研究;绸缎史;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乐伎演出的发展史资料等等。
到他去世,还在漆器及螺甸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等领域取得了专门性研究成果。而他经历十七年、往前推则是约三十年,过程曲折跌宕、离奇诡谲,得以系统完成的开创性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商务印书馆2011年编辑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
该丛书展示了从晚清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及海外华人的学术名著,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雄壮的学术检阅。——沈从文应该宽慰,也应该骄傲。事实上,他对自己的文物研究,在各类文字中都表现出了自信和俯视式的“傲气”。
“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
沈从文坚定地相信,自己会出全集。
1947年后,在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边城》封面上,他留下这样的字迹:“第一版留样本,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原文无标点)
1949年8月15日,沈从文写《一个人的自白》,一开首就表示,是在“求生的挣扎和自杀的绝望”中留下的绝笔;“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这就是“全集”了。但那是什么时候啊!

沈从文和王㐨
1975年8月15日,整日埋首于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郑重托付给王㐨,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语气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平静自然,没有一点商量的意思——在万马齐喑,雾霭漫漫,世事秩序的流变中,他确信着永恒。此时还在“浩劫”;王㐨怕遭不测,在衣箱里做了夹板,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王㐨懂沈从文。这个1953年沈从文在午门陈列室认识的志愿军军人,后来成为沈从文最亲密的助手和最信赖的挚友。他低调、睿智、勤勉、忠诚,成长为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应当与沈从文一起“永生”。
沈从文这个自信的预见,在他去世五年后实现。1993年11月7日,83岁的张兆和与北岳文艺出版社签署了《沈从文全集》出版合同,这是我国第一套正式按照版权法签约的文学和学问大师的全集。经过张兆和全家以及沈从文几位助手的艰苦努力,2002年32卷的全集成功问世。
“梅兰芳依旧只有一个”
1962年1月5日,沈从文写信对张兆和说:有种人才“不是可以从人力加工得到的。正如梅兰芳一样,新的方法或许可以教育出许多不同接班人,但梅兰芳依旧只有一个”——这是“以人说己”,是夫子自道;是沈从文很重要的自我评价,极其骄傲的生命表白。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文学上,沈从文具有对世界独特的极其敏感的天赋、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和独特的复杂经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认为:他的文学成就超过鲁迅。他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而痛哭,还异乎寻常地透露:“如果他不在1988年去世,那么我肯定他一定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另一种乡愁》)沈从文“只有一个”。他站在了世界文学的高端。
在文物研究领域,一个举世作家在“花花朵朵,罈罈罐罐”中,沉溺了近四十年,用独特的视角和理解、姿媚转胜的文字撰写心得,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偶然,汪曾祺说“世界文学史上似乎尚无先例”。——他也“只有一个”。沈从文也登上了物质文化研究的高端。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