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德国哲学有巨大的直接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德国哲学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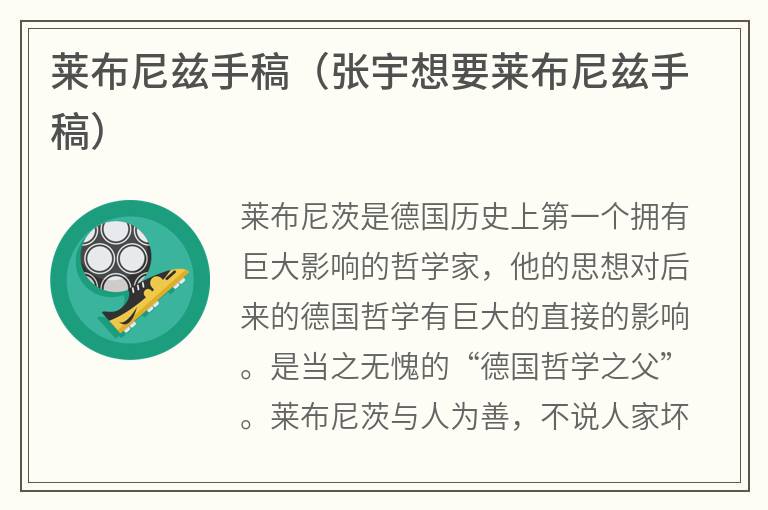
莱布尼兹手稿(张宇想要莱布尼兹手稿)
莱布尼茨与人为善,不说人家坏话。他相信,即使从最无知的人身上,也能学到东西。
他是帝王的高参,柏林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狄德罗曾这样评价莱布尼茨: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比较时,就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扔了,在世界上找个不起眼的地方躲起来,然后在那里安静地死去;莱布尼茨的思想是无序的死对头,任何最混乱的东西在他的心灵中也会变得井然有序;在他身上,两种几乎是无法相容的伟大品质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发现的精神和方法的精神。
从小开始,莱布尼茨就酷爱读书,还自学了几门外语,15岁的时候就进入了莱比锡大学,学习数学,同时还钻研哲学和法学。1666年.他想在莱比锡大学申请法学博士学位,但校方竟以他年龄太小而取消了他的资格。但临近的阿尔多夫大学接受了他的论文,授予他博士学位。所以仅仅20岁,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席位。他离开莱比锡后,在纽仑堡参加了一个炼金术团体。
1667年,他成为德意志帝国朝廷参议。
1672年,莱布尼茨受派前往巴黎执行国家战略使命,并在巴黎居住了4年。他被邀请参加了数学团体。法国在数学领域当时居领先地位,已经出现了大名鼎鼎的笛卡尔、帕斯卡尔、惠更斯(Huygens)。莱布尼茨有幸结识感更斯,并对笛卡尔哲学有了直接的认识。在伦敦,他和牛顿的合作者建立了联系。在海牙,他见到了斯宾诺莎。由于与世界上最有数学天赋的知识分子相识,莱布尼茨蕴藏着的数学才华被激发了出来。1675一1676年间,他提出了"无穷小算法",在巴黎期间,菜布尼茨还发明了一种能做加减乘除及开方运算的计算机,比帕斯卡尔仅能做加减的计算机有很大进步。
莱布尼茨注意到"无意识",他认为内心的许多体验并没有经过反思,我们没有察觉出内心的变化,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精细了。这启发了弗洛伊德和的精神分析。
1.莱布尼茨的本体哲学
莱布尼茨接受了原子和虚空的观点,他觉得物质中还有积极的推动力量,即它的智慧,莱布尼茨称做"力"(神秘的力)。
"力"属于形而上学领域,因为它无形(不像其他物理的因素那样被感知)而又可以理解,也可以说它是莱布尼茨理论模型的雏形。它是潜在的能量或"隐得来希"(Entelechies),它派生出多样性."隐得来希"可以类比为物质中的欲望情感,也就是"灵魂"。莱布尼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物质中的"精神"力量,它是不可分的。至于"隐得来希"的诞生,莱布尼茨求助于奇迹,认为它有创生、有毁灭。
巴门尼德否认真正的虚无,只承认存在,消失和呈现只是现象,从来没有真的毁灭。莱布尼茨看来,众多单子不仅有程度(级别)的差别,也有种类的差别。但是在哲学意义上,它们又是无差别的。
他说:它们《指单子―引者)可以被称做形而上学的点,有某种像似生命本性的东西,它们有知觉。为了表达宇宙,数学的点就是它们的观点。物理点只表现为可分的,数学点是不可分的)。
菜布尼的解决方案是,每一个精神(单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是自给自足的,完全不依赖其他的单子。自言自语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真正的哲学精神。所有单子,不论是人还是物,都有或显或隐的"精神"。藏在最隐蔽处的梢神也被叫做死。
他认为死一样的睡眠应该是无梦的,在这里记忆应归于无。这时单子无任何遮盖,完全赤裸。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持续很久,灵魂从深度睡眠中苏醒过来,灵魂比赤裸的单子多了点什么。莱布尼茨认为动物与人不可同日而语。他与笛卡尔一样,领悟到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自己在感觉,在思考.而动物不能。
莱布尼茨认为,最高等级的单子有自我意识,宇宙强调的是秩序,而不容忍混沌和隐晦。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莱布尼茨首先提出生物的进化,他认为一种动物只能通过自然的方式产生和消灭。
在数学上,莱布尼茨最先发明了标记微分与积分的符号。
在逻辑学上,他提倡了符号逻辑。
在语言学上,他提出发明一种普通性的语言。所有这些成就,都与他提出的符号语言有关。莱布尼茨企图用这样的语言系统记载哲学与科学。
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莱布尼茨称,大多数献身于数学的人都不太喜欢形而上学,因为他们发现数学是清晰的,形他说:"虽然我是那些非常努力为数学工作的人之一,但从我青年时代起,我就不断地思考哲学.因为在我看来,通过清楚的证明,可以有一条道路,在哲学中建立靠得住的东西。"
就是说,在最根本处,科学要依赖形而上学作最后的解释。而形而上学则是隐晦的。自柏拉图以来,所谓"第一哲学"并没有真正的进步,这又与哲学概念有关,对不懂哲学的人来说,哲学概念是晦涩的。对哲学无知的人不能理解哲学概念,对形而上学的偏见从数学延展到其他学科。莱布尼茨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接近科学的术语代替哲学术语,比如不说"实体",而说"原因"、"主动"、"关系"等等。
他称赞笛卡尔为形而上学带来了变化,即用一种怀疑眼光使精神离开感性的事物、但遗憾的是,笛卡尔没有坚持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隔开,从而断定物体的本性在于广延。莱布尼茨绝对不赞成哲学的隐晦性,他说:"在我看来.形而上学甚至比数学更需要清晰性和确定性。"
"能"和"力"的概念,天才的莱布尼茨把它视为藏在物体内部的精神创造力。它们最初被创造出来时,其哲学愈义远大于其具体科学的意义,它们首先是哲学或自然哲学的概念。
莱布尼茨在1706年写了一篇书信体的短文《评普芬道夫的原则》:普芬道夫的著作是否可以作为在政治和法的领域教育青年的范本。
讨论的焦点是关于自然法的问题,莱布尼茨在表面上批评普芬道夫,其实是攻击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观念。在莱布尼茨看来,法律要有牢固的基础.他说:.我希望更牢固的东西,它将给出清晰而富有成效的定义.从正确的原则中得出它的结论......这个稳固的东西将按照秩序建立起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
莱布尼茨认为,只有自然本体的理性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举止是正当的。普芬道夫强调效果.如果某种观念只是藏匿在心灵中,而没有外在的表现,就与自然法相悖。莱布尼茨关于自然法的见解实际上就是关于法的哲学,是立法之本,而普芬道夫排斥关于法的哲学,把自然法与人的行为混在一起。
莱布尼茨说:"自然法写在我们的心灵,我们有一顺充满自由思想的灵魂,一个总是倾向于公正的心愿。"公正的观念(它是近代国家与法的理论基础)被他视为神圣的(或者说是先验的),归结于神。"自然法"绝不仅仅是局限于法律的概念,它还涉及到政治、国家、道德、历史等等领域。莱布尼茨提出要改进教育,让美德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有鲜明的爱与恨.法的惩罚作用只是为了明德。如果我们听霍布斯的,在我们的土地上只会有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内战。于是和平成为紧迫的问题,必须剥夺所有人对所有事务的权利一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愿望转交给国家,或一个君主。
莱布尼茨一生大部分时间的正式职业是图书馆员(从他在30岁时接受汉诺威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皇家图书馆馆长职位直到去世)。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资料并不陌生。
1707年,著名的耶稣会士白晋(Bouvet)神父就曾把这些材料送给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熟悉的两部有关中国的重要论著,即龙华民(Longobardi)神父写成于1625年、发表于1701年的《论有关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圣马里(SainteMorie)神父写于1637一1643年间、于1701年出版的《论中国传教团的几个重要问题》。莱布尼茨在自已的著作中对以上的材料曾经做过详尽的分析。他也知道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有关这场争论的其他主要官方文件,比如康熙皇帝的通谕、罗马教皇的教谕、严家乐(Maigrot)主教的训令等等。
莱布尼茨还有另一个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就是他与在中国的某些传教士的往来信笺,白晋神父在信中向莱布尼茨介绍了《易经》的内容。莱布尼茨在许多通信中还得到大量二手材料,尤其是有关中国语言的材料,这些见于他与布尔格(Bourguet)、德博斯(DesBo,-se,)、吉马(Gima)等人的通信中。他在去罗马的途中,也曾会见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比如1689年见过吉马迪(Grilnaldi)神父。
莱布尼茨的基本想法是:基督教要获得统一,首要的任务在于建立真正的宗教。唯一道路是理性的神学,因为只有普遍的理性才是所有人思想统一的基础。神学与理性应该和睦相处,不能把神学放在理性上面,宗教不属于狂热,而属于理性。理性是上帝的恩赐。理性的神学也是自然的神学,因为理性之光也是自然之光。
莱布尼茨写道:"寄居在上帝知识中的自然哲学、心灵和精神哲学,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自然之光。然上摘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后,自然之光不仅在开启了的神学中传播,而且充当着法学大厦不可动摇的基础,即自然法、人权、公法、政治法的基础。总之是所有社会法的基础。"①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自然神论蕴含着理性神学的认识,超越西方神的启示阶段:或许耶路撒冷也不是世界中心,各民族的历史(像一个个单子)有平等的尊严,都是人类家园的一分子。
莱布尼茨渴望世界宗教、政治的统一。
莱布尼茨经常说中国思想中有他诉诸的自然宗教和历史。中国人的自然宗教中隐藏着关于上帝、灵魂、精神的知识,自然哲学也相信一个善良智慧的神,即相信神的善、智慧和能力是理性或自然宗教已经教给我们的信念。这样的观点在西方叫做"万物有灵论"或"自然神论"。
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先生的信》,在此信中这样评价中国的"理":"中国人赋予理以真和善的性质,就像我们在形而上学中给予存在的性质......这个理自身内和外含有理性的切声音和法则,并在时间中拥有一切,从未停止活动和产生的过程......这就是说理、太极或上帝有理智的本性,它能预见一切,创造一切。"
他在信中说:"我看不到中国人有我们的哲学家在他们的学派中传授的所谓原始的物质,后者是一些纯粹消的东西,没有规则,没有形式......"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并不认为物质是先于规则的浑浊一片,而是理的派生物。
莱布尼茨甚在信中重申了朱熹的立场:个别的理是一个更大的理的表现。同样的理在个别中也不应该是破碎的,而是一个整体。单子论不就是这样吗?每一个单子自身都是一个整体,它反映整个宇宙或神。他在信中说:"在我看来,在这里特殊的理并不是精神的原始实体,而是一般的精神实体,或者说是隐得来希。就是说,它具有活动性和感受性,是如同灵魂一样的活动规则一切事物只有通过同一道理、同一原始精神,或者说赋予一切完美性的上帝的分殊才能有活动性,才有它们的隐得来希、灵魂、精神。"
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与黑格尔明显不同。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莱布尼茨把中国人的思想融合在自己体系中的做法是"令人讨厌的"蒙昧倾向。
莱布尼茨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建立一门这样的普遍语言,他认为人所拥有的逻辑和上帝是一样的,原始语言应该是一种最完美的哲学语言,他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语言(由于以上说到的原因,莱布尼茨放弃了拼音文字的方案):能表达普遍的理性,为神和人共同拥有。莱布尼茨怀疑希伯来语,他对托马森(Thoma,sin)神父说:"认为所有语言与希伯来语言的联系都是和谐的,这也就是为了证明整个人类都来源于亚当,这是各种语言达到和谐的一件伟大事业,但是我怀疑这个父亲,...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莱布尼茨认为希伯来语不能担当起普追语言的重任。他认为在语言问题上存在着"神学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就是,似乎上帝已经拥有人类共有的"普遍性语言"。
莱布尼茨的理想是把有不同句法组成的表面上的语法还原为一种对一切语言都适用的深层语法或逻辑。对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汉字就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这些不是字母组成的字体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一个对象。
传教士们对汉字的构成方法极感兴趣,认为汉字的学问不在于说话而在于书写。就像祈尔歇(Kircher)神父说的,中国人似乎有两种互相独立的语言―书面语和口语。按照他的统计,口语用"词",很少.大约1600个词(勒孔特神父甚至认为只要330个词就够了),所有这些词都是单音节词,然后利用少数几个音调的变化派生出更多的词。由于方言混杂,由口语判断词义是困难的,所以中国人在言语的清晰表达上是困难的。
莱布尼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汉字是理性的语言,因为汉字不是由字母组成,汉字可化简为笔画。莱布尼茨甚至说汉字比同样是象形文字的古埃及文字更抽象,更像是一种哲学语言。他说:在我看来,埃及文字更大众化,太拘泥于像动物之类的感性事物......而中国文字也许更具有哲学性质,这样的理智是由汉字中的顺序、数量、关系给予的,进而只具有一些独立的特征。"
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更符合他要建立的逻辑。在他看来,由于汉字的字形摆脱了发音,更具有独立性,从而保证了汉字的稳定性和严格性。他说:"说话是借助于语音给它说到的思想一个符号,书写是借助永久性线条使说话有了根基。就像汉字所表明了的,不一定非要把这些线条与一个声音联系起来......汉字参照的绝不是它的发音,而是事物同样的本性。"
莱布尼茨认为口语出于热情,是隐喻活动的场所,最容易把词与它的原义混淆起来,从而成为语言腐败的一个温床。他在1679年6月24日写给埃索尔(EI,hol:)神父的信中认为,文字的真正价值是符合它所代表的事物的本性。他认为基本的汉字就有这样的特性。莱布尼茨还往意到了汉字基本的笔画和笔顺,这与他想建立的普遍语言的设想有直接的联系。他说:"汉字有理由成为一种普世的文字,它的书写形式将被所有人理解。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同意用一种文字指谓事物,不同民族的说话还是可以不同。例如汉字读大,尽管其他民族对大有不同发音,但对它有同样的理解。"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易经》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白晋神父于1701年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中国的《易经》。白晋神父的目的是向莱布尼茨说明中国有"科学",但都是像《易经》一样以象征形式出现的。他说:"所有这些是它们的历史和神话的离惫和虚构,我们要想很好地知道它全部令人惊叹的诡计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通过准确地分析使用这些垂本象征符号的原则来获取它的秘密。这些原则也是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星象学、音乐、形而上学、物理学等的原则,在它的基础上展开了中国古代的体系和经书的真正的宗教。"
白晋神父在信中向莱布尼茨介绍了六十四卦。他向莱布尼茨表示,这样的划分方法实际上就是二分法,其中一条完满的线(一)可以表示为"0",而断开的线(一)可以表示为"1"。这样,(易经)的基本图形就和莱布尼茨所设想的普谊语言―应用的数学化逻辑(现代数理逻辑的雏形)相吻合了。白晋神父认为中国人早就知道了事物"二分法的系统",他认为二分法是全部科学与哲学的基础。
莱布尼茨对白晋神父的想法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他不怀疑是中国人发现了"二分法",而且他也非常赞同白晋神父从(易经)中作出的与上帝创世说相一致的结论:上帝是1.他从虚无(o)中创造世界.而世界的起源遵循1、2、4、8、16、32、64....的原则。莱布尼茨承认这是一种中国古代就已经掌握了的非常先进的科学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有了完整的自然宗教体系(阴阳五行说)。
莱布尼茨从《易经》的数学语言"中发现了他的数理语言:"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在[宗教]虔诚上,而且在科学方面都大人超越了现代的中国人。"他在给白晋神父的回信中说:"二分方案的用处在于安排观念,我们的神启也谈到它。经验使我意识到二分法对于概念形成的极大用处......这种二分法是神秘的,躲藏起来的.它也给我们一种深入了解中国人的途径:对中国人来说,二分的意向揭示出自然哲学与神学最重要的真理,能更便捷地踏上神启之路。"
莱布尼茨把《易经》的道道看成是一种特殊神秘的"逻辑符号"。西方人建立的数学理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相信逻辑推论的证明,而《易经》中的数字排列关系隐含着直觉中的"真理",“阴”与“阳”基本上就是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版。他曾断言:“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如今在德国图林根,著名的郭塔王宫图书馆(SchlossbibliothekzuGotha)内仍保存一份莱氏的手稿,标题写着“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其手稿标题全文是:《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无非都来自上帝。》,而且莱布尼茨自己写给若阿基姆·布韦的信中莱布尼茨写到的是:“第一天的伊始是1,也就是上帝。第二天的伊始是2,……到了第七天,一切都有了。所以,这最后的一天也是完美的。因为,此时世间的一切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因此它被写作‘7’,也就是‘111’(二进制中的111等于十进制的7),而且不包含0。只有当我们仅仅用0和1来表达这个数字时,才能理解,为什么第七天才完美,为什么7是神圣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第七天)的特征(写作二进制的111)与三位一体的关联。”在莱布尼茨看来,《易经》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书,是哲学、科学、数学和数理逻辑的源头;
1700年莱布尼茨说服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于柏林成立德国科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莱布尼茨:中医是科学之首,中医是最能代表这个“活水”的,所以它展示着“道”——科学之母——的机理。他在1671年说:“即便中医的规则显露出某种(像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愚蠢和荒谬,但它比我们的(欧洲医药)强多了。”一年后,莱布尼茨致信东方学家斯皮泽尔(GottliebSpitzel),写道:“来自中国的最有前途的东西就是她的医学”(themostpromisingthingtocomefromChinaisitsmedicine)。除了传播基督教,传教士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中国的医学。最需要的就是医学,因为它在自然科学中是最重要的(引者按:莱布尼茨看重中医具有有机整体的性质)。……而且,所有的物理科学乃至医学,都是以神的荣誉和人类至善为其终极目标的……中医不仅被视为自然科学,而且它是通向神的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匹特曼教授所说:“西蒙·米尔斯(simonmills)注意到……‘活力论’(vitalism)酷似……莱布尼茨和怀海德的‘有机论’(organicism),后者指各个层面的实体与其他部分都是休戚相关的。这也相似于史末资(Smutts)的‘整体论’(holism)。……关于它们(活力论—有机论—整体论)的起源,米尔斯解释,那就是中医的基本原则——道,它也是世界的起源(theoriginoftheworld)。”
利玛窦的同仁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9年)感悟:“中医与其他中国科学一样,都是讲究‘道’或‘天人合一’等基本哲学观念”。中医源自古老的经典,临床经验很丰富,使用植物制剂和烧灼等方法。
1682年,克莱耶编辑出版了《中国医学手册》(SpecimenMedicinaeSinicae),把其中的内容归功于“住在广州的博学的欧洲人”(卜弥格)。此书出版后,引起了欧洲医生的极大兴趣,但因内容尚不全面,因此有人对它的版本提出了批评。四年之后(1686年),纽伦堡发表了《医钥》(MedicusSinicus),内容比前一本书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所引用的资料仍来自于卜弥格的《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1813年,汉学家雷慕莎根据卜弥格《中医大典》节选出书。
卜弥格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脉经》和《脉决》等中国医学典籍。他在南明永历皇帝的朝廷,也从一些中医师那里学到许多中医临床的知识。他在1658年向欧洲人介绍说:“现在,我们向你们,最有名的医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在《医钥》等著作中,卜弥格站在“道的哲学”的高度,对于从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循环和宇宙运转、一年四时对人体机能运转的影响,到脉诊治病和各种中医处方和药物的运用和功效,都予以详述。
卜弥格对于中医最为推崇的就是脉诊技术,他写道:“它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技术,和欧洲的不同,它不仅要说明病情,而且能够预料它的发展和后果。”他认为脉诊治病的方法,在中国许多世纪以前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使用;中国的医生通过诊脉不仅能够了解病情,而且能够准确无误地预示它以后的发展。
卜弥格理解:人体内的气和血在人体内的十二根经中,24小时成周期地不断循环;由于这种循环,便产生了脉搏。这种循环也和天的运转相对应。脉搏和呼吸的次数成一定的比例。如果不成比例,人就处于病态。
卜弥格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论述,他认为每个器官都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肺和大肠属金、肝和胆囊属木、肾和膀胱属水,心和小肠属火,脾和胃属土。它们的活动和一年不同的时节有联系,人体内的十二根经将这些器官和有关的脉连在一起,脉搏反映在两只手的寸、关和尺这三个位置上。每个器官都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好恶,从脉上可以看到通过经络连着它的器官的健康状况。
研究卜弥格的学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曾经说过:“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当航海民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人从卜弥格那里,对于中国医学、中国动植物和矿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弥格乃是向我们提供这种知识的第一个欧洲人。”
国耶稣会士刘应、白晋、赫苍璧、巴多明、韩国英等人,都经常使用此书。耶稣会士在17—18世纪翻译《本草纲目》。1735年,杜赫德在《中华帝国通志》中介绍了中医,其中包括赫苍璧翻译的晋代王叔和《脉经》和《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巴黎国立图书馆保存有一部中医著作译稿,共分两部分,一为脉学,一为本草,是《本草纲目》的节译,其中介绍了序及每卷之内容,还提到了人参、海马等中药。
1687年,旅欧华人沈福宗被请到牛津大学,帮助弗洛耶(J.Floyer,1649—1734年)整理中文书籍。由克勒耶整理出版的卜弥格的著作《中医示例》,介绍了中国古代脉学。后来成为弗洛耶研究的基础。1707—1710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二卷本的《医生之脉钟》。
弗洛耶受到了中医哲理的影响,他把脉搏和人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即通过人体的小宇宙来体现脉,脉是小宇宙之和谐或不平衡的指示器。弗洛耶说:“我将首先证明中国人确实在脉学上具有伟大的知识,在把脉艺术的基础上,他们建构了行医的做法。……我将证明中国人已经发现真正的把脉艺术。”他还认为,中医的成就是不能被现代学术进步所超越的。他坚持捍卫中国传统的医学思想。
1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人痘接种法。它包括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痘衣法是把天花患者的衬衣,让被接种人穿用,使其受感染而产生免疫力。痘浆法是用蘸有疱浆的棉花塞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使其感染。旱苗法是将光圆红润的痘痂阴干研细,用小管吹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后来经过逐步改进,人痘接种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不断得到提高。文献记载表明,到17世纪时,人痘接种法不但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1688年,俄国曾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术。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土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医生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而且效果显著,就让医生也给她的孩子种了人痘。此后她又专门学习了人痘接种法,并把它带到英国去,得到了英国国王的赞同,于是人痘法接种法很快盛行于英国。另一方面,根据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记载,人痘接种术也通过一些在中国经商的英国商人和旅行者,直接传到了英国,并在英国皇家学会进行了交流。根据皇家学会档案记载:1700年英国著名医生、皇家学会会员马丁·李斯特收到一封从中国寄来的信。信中描述了鼻息传种天花的方法:“打开天花患者的小脓疱,用棉花轻微吸沾一点脓液,并使之干燥……然后放入健康人的鼻子里,此后被接种者将轻度感染,然后痊愈,从而获得很好的预防效果。”后来再由英国传到欧洲各国、北美和印度。
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又直接由中国传入日本。可以说,在人类抗击天花的斗争中,“人痘接种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世界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结语
2022年二月十五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