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继《南京城市史》(南京出版社2008年7月版)之后,知名学人、南京地域文化研究专家薛冰先生,又以七十万字的《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九州出版社2024年5月版),再一次令书林人士啧啧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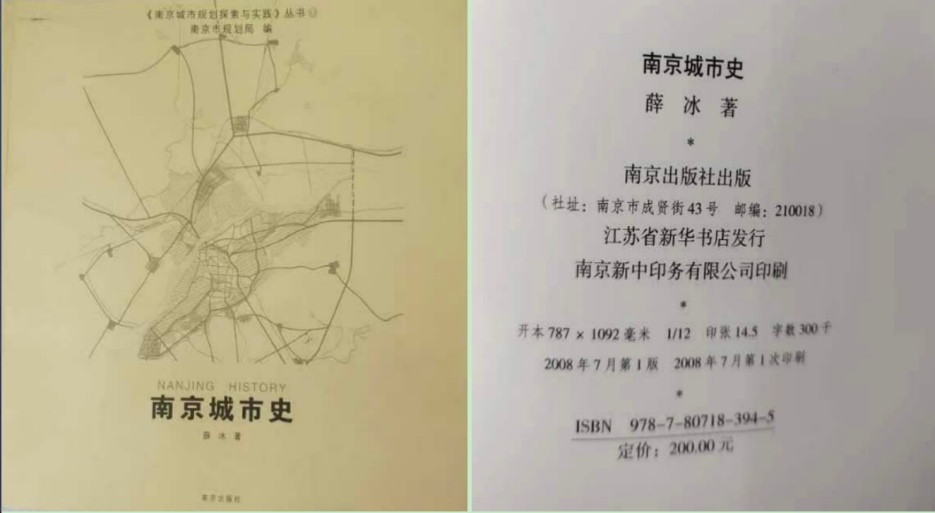
有关本书写作缘起,薛冰先生在其自序中交代说:
拙著《南京城市史》问世不久,就有读者提出,书中仅限于城市空间的发展变迁,对社会人文诸方面未能充分阐述。就城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十几年来,我时时处处留心搜集南京人文资料,比较文献,分析史事,发现问题,梳理脉络。曾经活跃于南京的重要人物面目渐渐明晰,曾经发生在南京的历史事件因果渐渐清楚,一幕幕活剧时时勃勃于胸间,激发我将它们写出来。
《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共有17章,分为上、下两册,精装出版。上册有九章,依次是《从先吴文化说起》《南方三国演义》《秣陵:王气之谜》《东吴:古都初建业》《建康风云》《骑鹤上扬州》《魏晋风流与南朝文运》《唐人眼中的金陵》《承唐起宋》。下册包括八章,依次是《宋、元沧桑变》《江东文运》《大明基业》《留都南京》《应天经济》《明人文事》《江南风流》及《凤凰涅槃》。
由作者篇章标题和自序可知,薛冰先生写作的,是一部具有其浓郁个性特点和独特人文视角的“讲史体”作品,而非经院派的高头讲章,因而文笔明白晓畅,知识可读性强,是该书最基本的文体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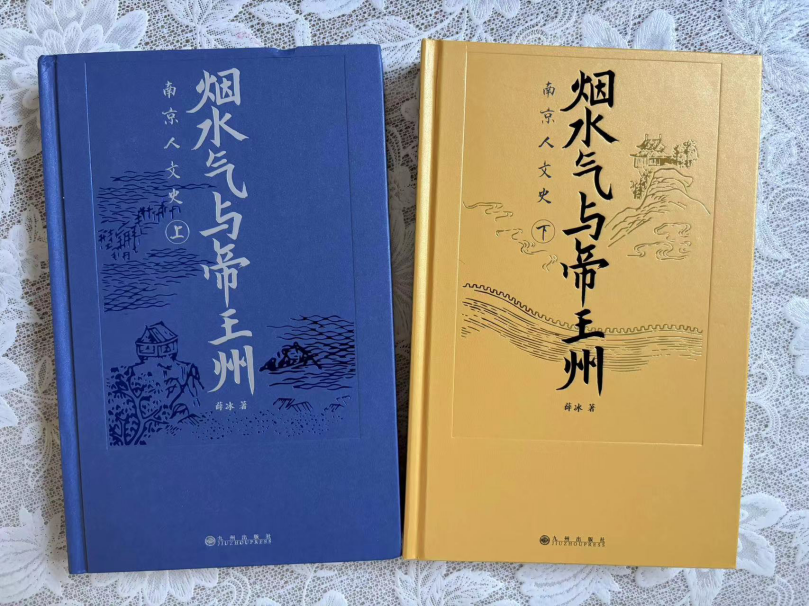
本书在写作上更为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著作者以问题为导向,尽力探求南京地方史事的此因彼果。他阐述了长干古城被发掘出土的重要历史意义,回望了它如何由一个兵卒驻防的军事之城,日益发展壮大为人口辐辏的商贸之市。他梳理了这个“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四条发展主线,一是兴衰无常的“王气”,二是古今贯通的“文脉”,三是南北往来的“商贸”,四是地秀人美的“佳丽”,并把追溯和阐发的重点聚焦在“文脉”上。
书中写道,自齐代诗人谢朓(464-499年)《入朝曲》中吟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名句,这十个字便成为后世公认的“南京文化符号”。而不同于“金陵王气”的虚幻,“帝王州”却“是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也曾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推手。”但就总体而言,相比“金陵帝王州”及“江南佳丽地”之类的说法,薛冰先生显然同朱自清(1898-1948年)等前辈一样,十分领受和极其服膺“六朝烟水气”这一历史文脉标识。
所谓“六朝烟水气”,其说或始于吴敬梓(1701-1754年)在《儒林外史》第29回中的一段人物对话,此后“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之说,遂成为与“皇亲国戚,尽显富贵奢靡之风”相对而存在的一种地域性民风。其文脉雅韵,极具审美价值。而薛冰先生在题名本书时,特意把“烟水气”置于“帝王州”之前,正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人文价值观。
须知,“三山怀谢朓,水涘望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继谢朓之后,曾有无数诗人骚客莅临南京,留下墨宝华章,争竞文采风流。但直到唐开元十四年(725年),青年诗人李白(701—762年)首次莅临之后,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底蕴,才随着其游历的屐痕,得到了充分的诗情诠释和演绎。
如果说甫至南京,李白迫不及待地登临瓦官寺高阁四望,吟出的“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筝……”(《登瓦官阁》),还是初读金陵之后的写实之句。那么,随着游历的深入,其怀古幽情在不断凝聚,酒酣诗兴在不断升华。于是“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金陵三首》其一)的感怀,“天地有反覆,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金陵白杨十字巷》)的悲悯,以及“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留别金陵诸公》)的礼赞,跨时隔空千余年,仍有绕梁之余音。
“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因仰慕谢安(320—385年)、王羲之(303—361年,一作321—379年)当年登高望远的超然风度,李白还萌发过择址其地、营造家园的想法。虽然后来因故未能如愿,但他在南京期间所写70余首诗歌,却成为留给世代南京人的厚礼,渐化为地域文化自信的文学资源之一。或如清人陈文述(1771-1843年)在《秣陵集》中所言:“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著。”
由越城而金陵、秣陵,由秣陵而建业、建康,由建康而江宁,为努力探寻南京地域发展历史的若干真实面相,薛冰先生不仅厚积史料,研读不辍,而且重视对历代南京地图与历史地理变迁关系的分析和比较,重视实际地域的调查和考察,从而形成了若干独特的认知,这也是本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能够给予读者的重要思想启迪。
他在书中写道,在朝野素有仁爱亲善名声,又主编了《文选》问世的萧统(501-531年),在英年早逝之后,被后世视为善于读书的象征性人物,“江南各地建有多处‘昭明太子读书台’,甚至有萧统在镇江招隐山编纂《文选》的传说”,但事实上,他不可能把东宫藏书三万卷和一群文士都带到镇江去,所以编纂《文选》的工作,只能是在东宫完成的。此外,萧统的死因,有史料记载,是因为大通三年(531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但他指出“此说诚不可信”,因为“南京虽在江南,三月亦无芙蓉可摘”。
他还指出,随着江南成为国家经济重心,产生于晚唐,兴盛于北宋的先进雕版印刷技术,也在南京取得了辉煌成就。大抵到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金陵人文日益昌盛,并发展成为明代重要的图书编辑、出版和发行中心之一。而《十竹斋笺谱》,则成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巅峰出品。
他强调,自宋代以来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不能只以汉民族为中心,更不宜只以朝代兴分割,无视其间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先后兴起的少数民族,同样有自己的‘自古以来’。同时,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兴盛过程,就是多民族交汇融合的过程”。
“市井坊间,尽染六朝烟水气/布衣将相,合书千载大文章”;“半壁门东,回照诗书礼仪/两弯淮水,摇来灯影桨声”,是矗立在城南、门东箍桶巷口的牌坊楹联。回望来路,我注意到,薛冰先生因参与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而在其知天命之年,从南京地方文献的积极收藏者,蝶变而为地方文化的杰出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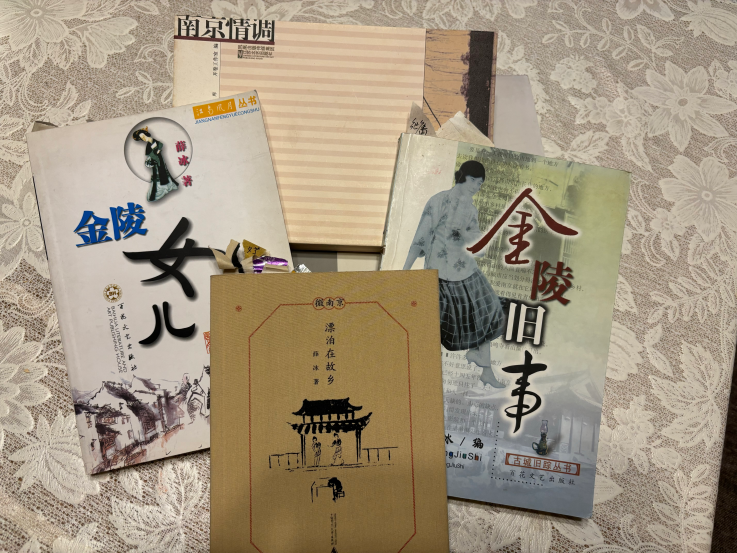
“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李群玉《秣陵怀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烟水部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吴梅村《元武湖》)……南京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座历经劫难而浴火重生的城市。无论是久居本土的人士,还是做官为学的外来寓公,大凡在这一片神奇土地上生活过的读书人,面对“金陵王气”“六朝烟水”“明初雄都”“江南佳丽”等等都市气象,从来“不乏书写南京的热情”。薛冰先生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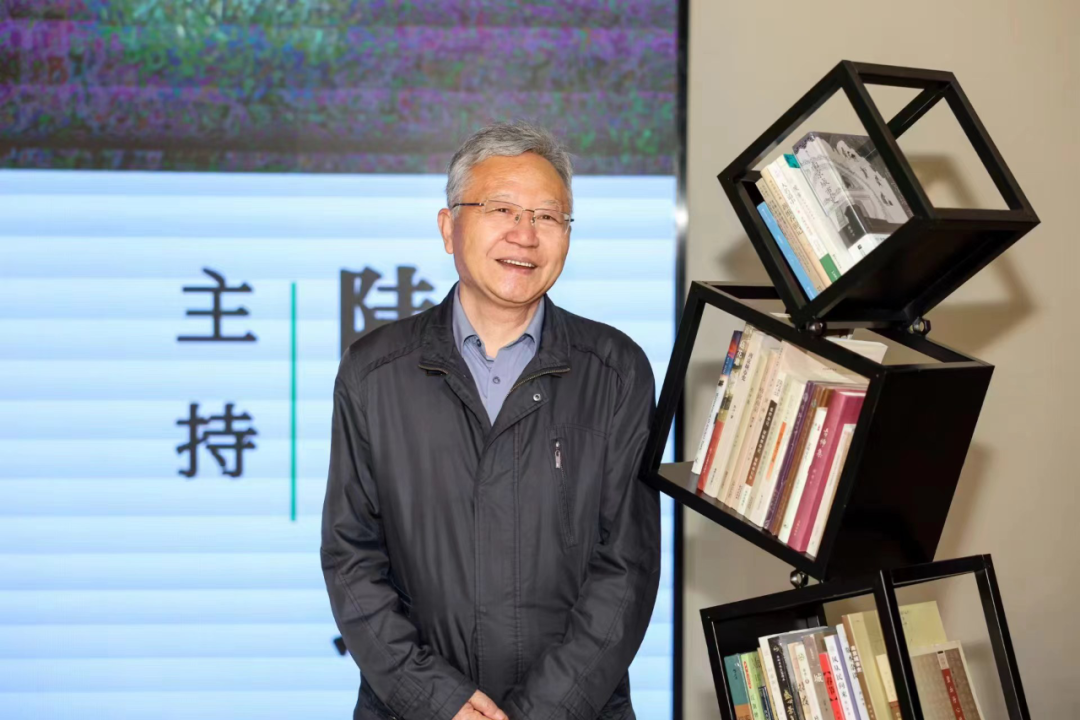
我注意到,他《漂泊在故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版)中的自述, 1950年两岁时,他随其父母来到南京居住。上小学,读金陵中学了,然后就被十年“文革浩劫”裹挟了。先是下乡务农,然后回城做工厂干事。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四年后得以进入江苏省作家协会,先后从事作家通联和《雨花》杂志编辑工作,直到以一级作家的资格荣休。他说,数十年来先后编写的《金陵旧事》《南京情调》,以及《家住六朝烟水间》《金陵书话》《金陵女儿》等书,正是自己对长期生活的这座城市——南京城的“回馈”,这份厚重的心意,令人敬重。
(2024年5月16日,写于金陵江淮雁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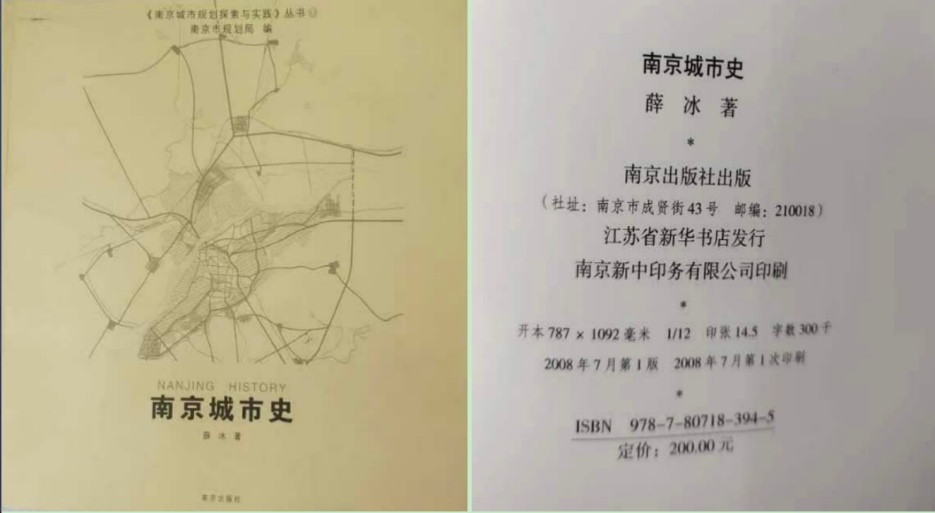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