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广东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
“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界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亲爱的读者,这段半文半白的话,是我从广东法政学堂的章程里摘录下来的,如果你仔细研读,就会从中读出办学者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尽管强调规则与平等的法律精神与“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格格不入,法政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夏同龢“普法于国民”的努力近乎于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但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就算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仔细检视这颗种子萌芽的艰难历程,或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迪。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办学
上百地方官被迫入读
有意逃学者乌纱难保
要追溯广东近代法律教育的源头,咱们还得提一提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广州同文馆。我们以前说过,官方之所以开办同文馆,就是为了培养信得过的外交人才。而要与洋人打交道,就必须了解国际法,所以,广州同文馆也开设了《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课程。不过,这些课程经常被视为“西艺”的附庸,开课时间很短,没多少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而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小官员,除了一小部分热心洋务的人,更将其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
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地方官接触舶来品
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办,却使全省大小官员再也不能小看这些“西艺”附庸了。1905年,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读书人顿失晋身之阶,科举正途失去了昔日金子招牌的效应,再加上时值清末新政,办理警政、管理中外商务、铁路和矿业等新兴行业,都需要全新的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未所有”,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两人的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了,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
5个多月后,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开课招生,全省大小官员开始不得不与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一大堆从没听说过的新名词打交道了。小记我本人是学法律出身的,以我自己经常熬通宵学习这类课程的经验来推想,当时那些读惯了四书五经的旧式官吏,一看到这些新名词,肯定大多眼冒金星,想拔腿就跑。
地方官逃学受严罚
成绩优异者可升官
可他们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根据当时官方的规定,广东大大小小过百地方官,上至道府、下至知县佐杂,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否则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如果该来的不来考,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课,都要记过停职,随即强迫入学,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不过,有罚就有赏,按照规定,如果学员成绩优异,就有机会升官,或者换一个油水更多的岗位,如果是候补官员,那也可以优先安排差事。就这样,面对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全省大小官员只好勉为其难,开始学习各类让人头晕眼花的中西法律课程。
学堂课程庞杂艰深,管理规矩也颇为严格。学堂章程开宗明义,称“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则之中”。再往下看,不敬师长,蔑视学科、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听课不抄讲义、提问不守规则,乃至在课堂内谈笑吸烟,都要记过,记过就要扣分,扣的多了,就要勒令退学,仕途必定大受影响。难怪《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四辑)刊登的一篇题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的文章写道,学生在课堂外见到洋教习,都要鞠躬行礼,见到华人教习,则要作揖,如果在课堂内,等老师入座后,大家一起鞠躬行礼。这些斯文有礼的场景,大概都要拜那严格的管理规定所赐了。
校长
状元东渡 立志普法于民
归国办学 苦心经营六年
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的影响不容小觑。据相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广东各地方法院,从院长到检察长,再到各庭庭长,几乎都是从广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可以说,它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亟须的法律人才。我们都知道,一所学校要办好,必有一位灵魂人物。早期广东法政学堂的灵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监督夏同龢。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这个立志“普法于民”的近代法律教育先行者,曾是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状元。留学归国后,他在法政学堂苦心经营六年,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
成绩优异打动日本著名法学家
说来有趣,夏同龢是1898年、也即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但翻开他应对殿试策问的文章,通篇尽是“致治之道无过于法祖”、“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这样的语调,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压根就是个反对变法的守旧派。这么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何以在数年之后作出自费到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的决定呢?要知道,他那时已是官至四品的翰林院修撰,又是状元出身,这自费留学的举动算得上惊世骇俗,因而上了当时《东方杂志》的“头条”,被誉为“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其志量加人一等”。这巨大转变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呢?从其活动年表上看,夏同龢中了状元的第二年,即到广东游历,在这里认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并结为一生挚友,随后他又前往澳门,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推测是这次广东之行改变了他的思想,却也不算毫无依据。
夏同龢只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了一年,但他优异的成绩令当时的法政大学校长、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十分深刻。1905年7月,日本《法律新闻》刊载了夏同龢接受记者采访的笔录,他在其间表达了“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立自强”的救国理念。当年,8月29日,夏同龢编著的《行政法》得以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从此,戊戌状元夏同龢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
办校外补习班普及法律思想
1905年年底,夏同龢学成归国,接受两广总督邀请,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从此开始了“普及法律思想”的实践。他主持制定学堂章程,将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他从日本聘请多名学者,来学堂执教,在法政学堂自编的月刊《法政丛志》上,常有外籍教员和学生就法学前沿问题展开的精彩答问,颇有教学相长的味道;他期待通过学校教育,使“官绅和谐,推暨于民,或从此一线”,这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实现“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的理想,他甚至还办起了“校外补习班”,从而出现了“校内千余人,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非常繁盛”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夏同龢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从此离开广东法政学堂,法政学堂之后也更名为广东公立政法专门学校,翻开了新的篇章。不过,他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成了广东亟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一个昔日拒“变法”于千里之外的传统读书人,最后却成了将舶来的法律教育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从外表上看,这样的转变十分戏剧化,但究其原因,不过是他从未放弃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求真探索的努力而已。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样的品质总是稀缺而宝贵的,这也是我愿意把夏同龢与广东法政学堂的故事写下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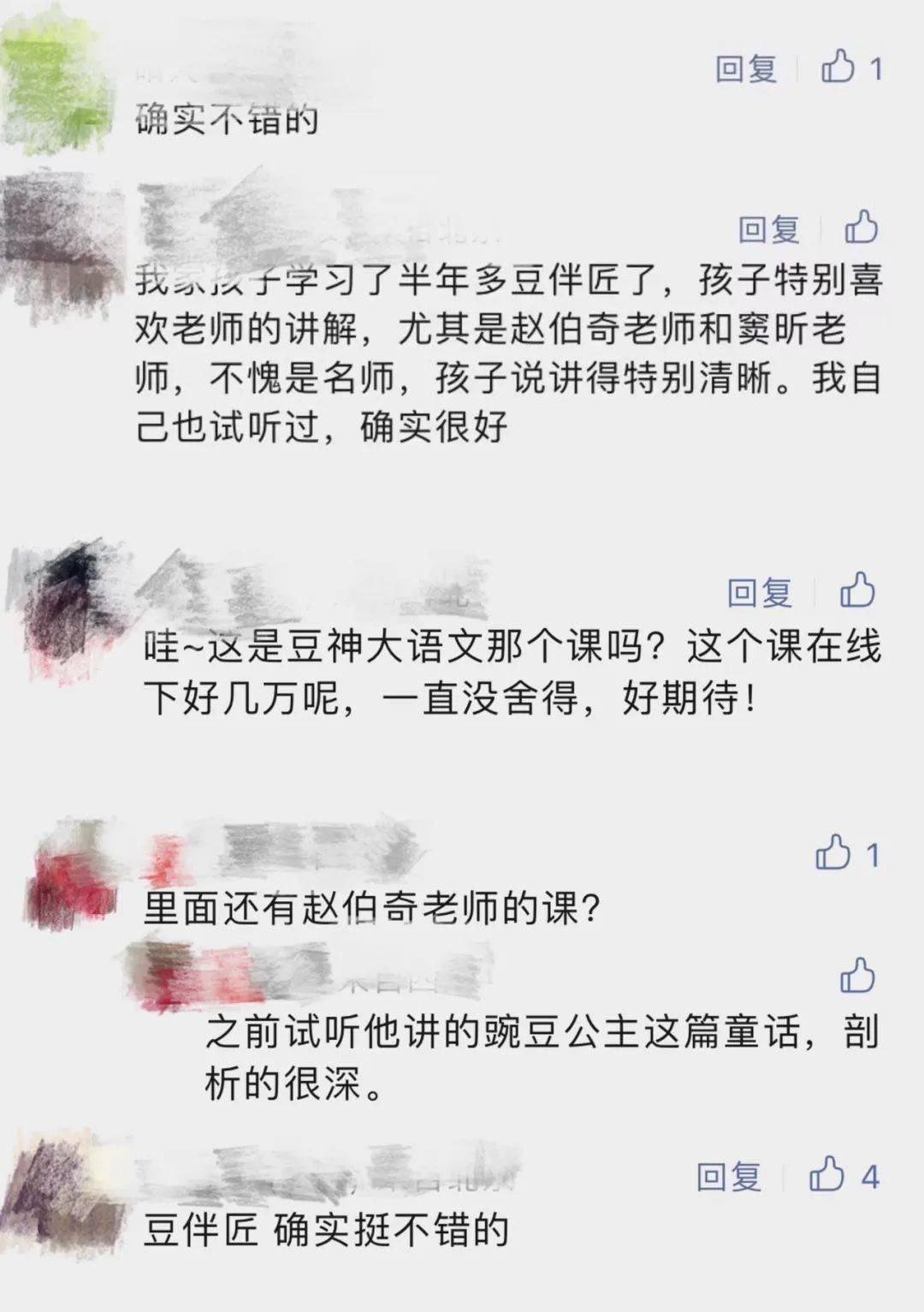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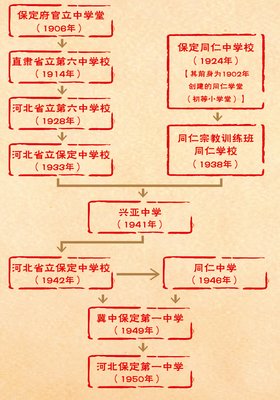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