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26年26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有关会务工作,从未中断!
他,11年11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没有缺席!
时光荏苒。37年来,在时空的变换中,他的角色也在不断变换,但不变的是与政协的情缘。

△常荣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我与人民政协的缘分,肇始于全国政协五届五次全体会议。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后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作为小组秘书,为当年11月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第五组——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服务。后来,我到大会联络组从事联络工作,直到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26年26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有关会务工作,从未中断过。从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荣任全国政协委员至今,11年11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没有缺席过。从2013年3月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以来,也逾6年时间了。人民政协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可谓念兹在兹,不离不弃。岁月悠悠,37年弹指一挥间,但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小组秘书工作的经历,虽然“当时只道是寻常”,但“沉思往事立残阳”时,更能体会到那段经历的温润和泽被我后来工作、人生的点点滴滴。
15名委员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缩影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历史专业。写毕业论文时,我选择的是关于辛亥革命方面的题目。为了写好论文,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书籍,还基本通读了全国政协编辑的几十辑文史资料选辑,摘抄了不少资料卡片,对许多历史人物印象很深。担任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组小组秘书,仅看小组人员名单,就有了一种历史就在眼前之感。随着接触增多,书写历史的人,被写入历史或将要被写入历史的人,从史书史料中走出来,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走出来,从耳闻中走出来,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史实史料一下子鲜活起来,学史的收获顿时灵动、厚实、多彩起来,让我仿佛走进了那段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
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组共有15名委员,当时平均年龄78岁,最长者为现代实验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唐钺先生,时年91岁高龄;最小者为物理化学家、高分子物理学家、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先生,时年65岁。最晚离世的也是钱人元先生,2003年12月因病去世,享年86岁。虽然15名委员已先后离世,但哲人其萎,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静如水,其虚如谷,丰碑犹在,风范长存。
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时有委员1988名,二次会议时增补111名,三次会议时增补97名,四次会议时增补70名,五次会议时增补2名。在2200多名委员中,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的15名委员占比很小。15名委员职业不同,经历迥异,性格禀赋不尽一致,年龄跨度达26岁,但15名委员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缩影。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建树和成就,让人高山仰止,很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的贡献,让人永远铭记。
15名委员中,简单加以划分,国宿耆老者有叶道英、朱洁夫、吴世昌、梁漱溟等诸先生。他们的道德文章、嘉言懿行,岁月虽邈,常记常新。
叶道英先生是叶剑英元帅的弟弟,1949年前曾担任广东省财政厅税务专员、香港大道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参事、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他用一口粤味普通话娓娓道来:年龄大了,但要鼓起精神,做实干派、促进派,壮士暮年,雄心不已。吴世昌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家、红学家、词学家。精通文史,学贯中西。“九·一八”事变后,他率先在燕京大学贴出《告全体同学书》,点燃学校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并被选为燕大第一届学生抗日会主席。1962年,他毅然辞去在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任职,带着家人于国家困难时期回国,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吴世昌先生在《红楼梦探源》英文本五卷成书时曾赋七绝五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红楼梦探源。其中一绝有言:“朱墨琳琅满纸愁,几番抱恨注红楼。脂斋也是多情种,可是前生旧石头。”反复吟诵,别有滋味。
学界泰斗者有王力、冯德培、郑易里、赵宗燠、俞大绂、钱人元、唐钺、曾世英等诸先生。他们在中国本学科中开门布道的鼻祖地位,指点江山的巨擘作用,文采泱泱,成果累累,至今在学术界仍有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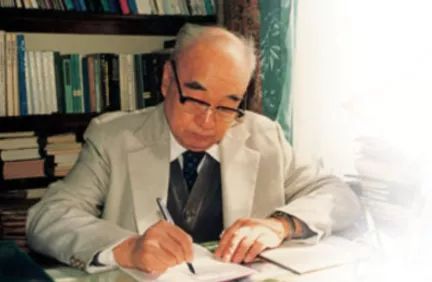
△赵宗燠
赵宗燠先生是著名的化学工程专家,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能源研究、有效利用和节能、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独步一时,曾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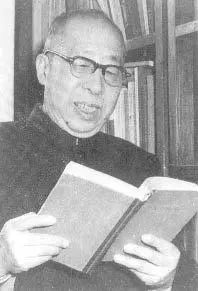
△俞大绂
俞大绂先生不仅家世显赫,一族之中有多位名闻华夏的人物,他本人更是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风云人物者有刘定安、李铁铮、倪征燠等诸先生。在辛亥革命、民国乍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新旧杂糅,风起云涌,顺历史潮流而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者,逍遥观望者,先顺而后逆者或先逆而后顺者,不同的脸谱,不同的角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或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或成为阻力之一。能成为全国政协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的一员,无论贡献大小,都是历史发展推动力的组成部分。

△李铁铮(上图左侧第五位)
李铁铮先生是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外交家,民国时曾驻外任大使、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兼大使衔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身从事研究、教学。1964年回国任外交学院教授,1976年再赴美国,1978年再度回国直至去世。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时,李铁铮先生手持拐杖,虽瘦骨嶙峋,却不怒自威,清癯的脸上写满了历史沧桑的风云和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睥一言,显现出外交官和大学教授的风范。

△倪征燠
倪征燠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大法官,是与中国20世纪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土肥原等十恶不赦的日本战犯时,倪征燠先生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深入搜集侵华日军的罪证,用道义、担当和学识,挽狂澜于既倒,令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历史铁证如山,一举扭转审判初期中国方面有冤难伸的被动局面,使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为国家讨回了公道,为民族赢得了尊严。慈眉善目与凛然正气,折冲樽俎与冲冠一怒,温文尔雅与严慎不苟,这些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气质,倪征燠先生将之和谐有序的融为一体。
小组名称的变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阐释的家国情怀,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期间,被无党派爱国人士组这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丰富而生动地演绎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同时,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为进一步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前,召开了一系列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并组成调查组赴一些省市就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在入党难、安排使用、工资待遇、夫妻两地分居、住房困难、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政策落实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期间,无党派爱国人士组在进行小组讨论时,委员们既对知识分子春天的到来欢欣鼓舞,又为进一步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为年龄五十岁左右、工资五十多块钱、住房五十来平方米的“三五牌”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而鼓与呼,为他们面临的教学科研任务重、基层党政工作任务重、经济负担重,工资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三重两低”问题而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落实对中年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有些地方和单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口惠而实不至;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年年的拖,使党的好政策减色、逊色。他们还对有的人、有的地方未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仍作为团结、教育改造对象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有的委员说,我家九口人,三间住房,书桌都没地方放,只能把书籍资料堆在床下,在床上搞研究。老专家尚且如此,遑论中年知识分子了。有的委员说,家中三个大学生,一个五年毕业,一个六年毕业,一个六年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工龄短、工资低,工作十分繁忙,生活十分拮据,不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困难和问题,教育、科研工作将会后继乏人。一群老年知识分子,对教学、科研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为保护中年知识分子、发挥好中年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感同身受,言辞恳切。
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命题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修改政协章程。由于历史的影响,当时的宪法、政协章程沿袭了一些“文革”时期的提法。委员们在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时,有的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有的手持放大镜,有的眼镜几乎贴着文件,在逐字逐句的阅读斟酌,提出修改的建议。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的15位老人,也同共产党人一样,最讲认真,其认真、较真的态度,至今令人难忘。他们对“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两个不同表述的直拗,则反映出他们对过去同共产党一道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民主自由、争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经历的珍视。在他们看来,“民主人士”当然“爱国”,在“爱国”的基础上争取民主、进步,追求真理,政治上“民主人士”高于“爱国人士”。此外,他们还认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组15人太少,应该“开源扩军”。回头看看,他们的意见应该起了作用,一至四届时,都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五届例外。六届一次会议时,这个小组的名称确实由“无党派爱国人士小组”改回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组”。一届时无党派民主人士有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二届时亦是10人,三四届时20人,到六届时小组委员人数由五届的15名增加到48名。他们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对节能、环保等方面问题,较早地提出意见建议,可谓础润知雨。他们老成谋国,悉心国是,具有很强的委员角色意识,即使会期较长,即便岁高年长,除抱病遵医嘱不得不休息外,自始至终坚持与会并认真履职尽责。
梁漱溟为何两次离开民盟?
宋人黄庭坚在《东坡先生真赞》中写道:“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党派爱国人士组这群学养深厚、阅尽人生的老人,在小组发言和会下交谈中,有宏论、有诗作,有正说、有调侃,有天真、有淳澹,但没有怒骂。岁月积淀,厚积薄发。谈天说地,皆有深意;信手拈来,总有珠玑。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两次发言谈为何离开民盟。第二次小组讨论时,梁漱溟先生说,我在第一次小组讨论发言中讲了我为何离开民盟的事,但其中有不少的遗漏,需再作补充。在两次发言中,他将自己的经历理出了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由乡村建设起家,希望从乡村自治体开始,逐步建立英国式的宪政国家。乡村建设在广东、河南、山东的实验以未果而告终。后来,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与青年党、民社党、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救国会“三党三派”结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和成立宣言起草者。抗战胜利后,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在国共和平无望后,特别是因政治上的分野,认为中国不能搞两党制、多党制,只能一党制的思想,与许多人的想法产生了较大分歧,故而离开民盟,成了无党派的一人。
从文史资料中了解到,梁漱溟先生1938年到延安考察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在就梁所著《乡村建设理论》进行长谈时,毛主席不赞同梁的“改良主义道路”,梁也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两人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最后梁也认可毛主席“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的意见。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他与毛泽东主席多次长谈、交流思想,是熟稔的老友。而到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则让人难以理解地“面折庭争”,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考量毛主席的“雅量”,并将军“您若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在记录梁漱溟先生的发言时,我对这样一位一生写满政治风云的人士在小组讨论时反复讲“为何离开民盟”一事颇为不解,随着在中央统战部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经历的积累,逐渐明白了梁先生的深意,谈摭掌故,以清视听。梁漱溟先生是1947年风云变幻时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离开民盟,定义是“离开”而不是其他。
在第一次小组讨论时,王力先生对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表示拥护和赞成,他谈了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认真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积极参加政协协商和协助落实有关政策、努力开展人民外交等五点认识体会。随后说,昨晚写了一首七律,祝贺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诗曰:
照人肝胆仰高风,国运兴衰荣辱同。大计协商筹善策,宏谋共议奠新功。云鹏展翅声威振,天马行空气势雄。屈指廿年成伟业,二番产值祝农工。

△王力
王力先生,广西博白人,语言学家。他编写的《古代汉语》四册,是大学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籍。我的书柜里,至今还放着他这套书,并不时拿出来翻阅。吟诵赋诗后,他还幽默了一句:按以往经验,我的诗在简报上登出来时往往会错几个字,登诗的小组简报清样是否可让我先看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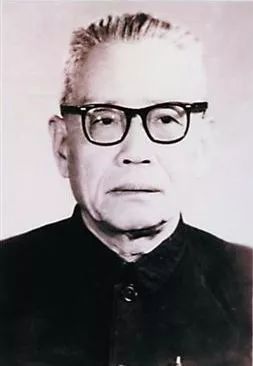
△曾世英
曾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图学家、地名学家。83岁高龄的曾世英先生,一头黑发,身板挺直,精神矍铄。他在发言中说,地图工作当然有保密的问题,有的保密属政策性的,有的属技术性的,有的属知识性的。但保密不能无边无际,更不能对外不保密对内却保密,单位之间相互保密。否则,不是有利于工作而是妨碍工作。一番保密工作要利于工作的发言之后,话锋一转,他突然说道:我经常蒙受不白之冤。在大家错愕之时,他悠悠道来,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因为头发不白,不像80多岁的老人,还时常给别人让座。“闻弦歌而知雅意”“不白之冤”,似别有含义。
时光荏苒。重拾37年前的记忆,回想37年来的经历,我从最初作为小组秘书为委员服务到后来自己作为委员履职尽责,再到政协机关工作既为委员服务又履行委员职责,在时空的变换中角色也不断变换,但不变的是与政协的情缘。有幸从不同的角度亲历和见证了人民政协事业在党和国家大局中,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阔步前行的壮美历程。人民政协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人民政协制度展现出的蓬勃生命力,足以告慰包括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小组15位委员在内的所有前辈和先贤。今年恰逢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让我们共同期待和祝愿人民政协把握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文史旨趣,历久弥新;家国情怀,历久弥深。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