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史论丛》(下简称《论丛》)创刊于1962年。至今(2016年)已走过五十多年的历程,出版达一百二十三期,是享誉海内外学界的国学名刊。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论丛》是1963年,那时我刚念高一,功课不甚紧张。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去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上海旧书店门市部,书架上就有一本1962年第一辑《论丛》(创刊号)。拿在手上一翻,直排繁体字,不仅文章的题目(如《卜辞金文所见的社会经济史实考辨》等)看不懂,作者(诸如平心、杨宽、蒙文通等)也从未听说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论丛》,印象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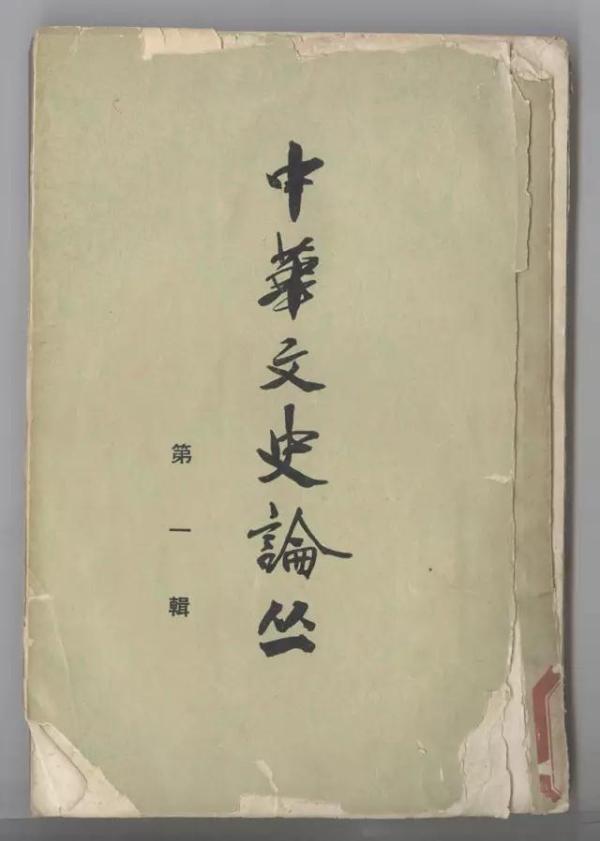
《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创刊号
1966年,摧残文化的“文革”发生了,风雨如磐,百花凋零,不知全国尚有几家社科类刊物能蒙钦旨准允出版。《论丛》的停刊是必然的,这一停就是十二年,直到1978年才复刊出版。在复刊的最初几年(约1978-1986年)中,《论丛》犹如积蓄多年一朝喷发的火山一样,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好文章,迅速重新赢得学界的称赞。这在客观上是因为禁锢思想的坚冰打破了,百家争鸣的氛围重又出现,学者又能自主思考,平等发言;主观上是由于富有战略眼光的资深出版家钱伯城先生重主其事,积极策划选题,发掘稿源,慎重编审的缘故。然而经济运行又有本身的发展逻辑,在越来越走向市场化的时代,当《论丛》依托的母体——上海古籍出版社受出版大气候影响举步维艰时,《论丛》自然也陷入了困境。1987年至1997年,《论丛》只能不定期出版,有几年甚至每年只能出版一二辑。自1999年始,因有二编室主任张晓敏的强力参与,2000年始划一版式与定价,每年准时出版四辑,每辑20万字,以书代刊,一度局部地挽回了《论丛》的声誉。可是数年后,张晓敏(已任副社长兼副总编)不再分管《论丛》,《论丛》所刊文章论题渐趋狭窄,亮点不多,学界渐有微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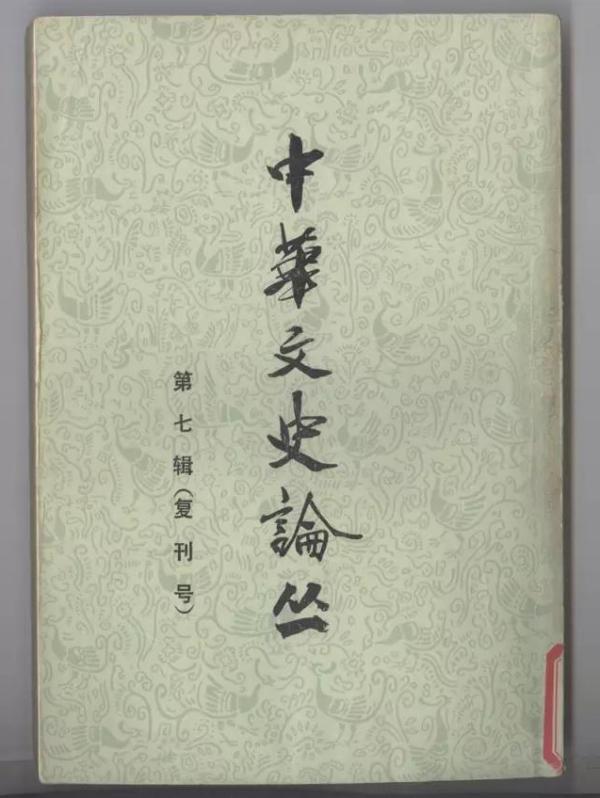
复刊第一期
2004年,我去昆明参加唐史年会。本届年会改选理事会,张国刚出任会长。张国刚是杨志玖先生的大弟子,上世纪90年代,他在德国波恩大学执教多年,曾帮助本社联系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的出版事宜,与我多年书信往还。1999年,他回母校南开大学执教,2003年刚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老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名震四海,建国后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现在又重建了文科,其中以历史系师资实力最强,有李学勤、葛兆光、李伯重、秦晖等执鞭,张国刚的加盟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正思有一番大的作为。张国刚和我面谈时,直率地批评了《论丛》近年来的质量下降,认为这是个海内外瞩目的品牌杂志,不能愧对前贤所创的祖宗家业。他说,办刊好坏直接依赖稿源,以书代刊不能进入国际视野,不利于吸引优质论文,故当务之急是恢复刊号出版,尽快争取进入CSSCI(中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系统,谋求大的发展。他表示,清华历史系有兴趣参与《论丛》的改刊和编辑(即和本社合办《论丛》),并可作出经济支持。张国刚的一番话虽然不免刺耳,但总体讲得在理,我答应向社领导汇报,作出回应。那时我还在四编室工作,负责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我没有想到,张国刚的建议会改变我的后半生编辑生涯。
回沪后首先向分管的副社长兼副总编张晓敏汇报,并由他转报总编辑赵昌平。他们二位都已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学界对《论丛》现状的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赵总与葛兆光相识二十余年,对清华历史系的学术阵容有相当的了解,先天就有一定的好感。但兹事体大,不仅关系刊物的走向,还牵涉办刊的“主权”问题,谁都不能贸然决定。除了社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外,还得听取各编辑室主任的意见。
当年本社领导班子成员有五位:王兴康(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兼党委书记)、赵昌平(总编辑)、张晓敏(副社长兼副总编)、高克勤(副总编)、刘玲田(副社长兼党委副书记)。大体说来,赵、张倾向于同清华的合作,王、高、刘持保留态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本社仅有一个刊号,自2002年起,本社用这个刊号与上海微型小说学会(江曾培任会长)合作办了一本名为《微型世界》的小故事杂志(月刊)。应当公允地讲,《微型世界》编辑部的四位编辑非常敬业、能干,他们白手起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杂志几乎垄断相关市场已达几十年(《故事会》每期发行100万册,全年总码洋1亿元以上)的棘石缝中,强硬地使《微型世界》冒出头来,所出各期《微型世界》生动活泼,雅俗共赏,开始有不俗的口碑,每期也能发行达1万册,这是甚为不易的。他们正期盼着社里的更多支持,以巩固阵地,徐谋发展。只是本社只有一个刊号,继续用于《微型世界》,《论丛》就只能依然以书代刊,如果用于《论丛》,刚创办三年的《微型世界》只能停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局面就是如此严峻。
不久,讨论解决这一难题的中层干部会议召开了。我在会上概述了清华方对改变《论丛》现状的意见。五编室副主任李鸣认为,停办《微型世界》太可惜,而《论丛》又确需刊号出版,主张向上级主管部门再申请一个刊号,两种刊物并行办下去。李鸣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国家对刊号控制极严,申请新刊号是不可能的。他的提议没有可行性,但这也说明《微型世界》在同仁心目中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微型世界》编辑部主任章行事后评议:“如能申请到新刊号,我们还开这个会干什么?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刊号,才要讨论给谁用。”真是一针见血。一编室主任曹明纲不赞成与清华合办《论丛》,他说,本社包括《论丛》的作者向有五湖四海之广泛的传统,不专挂靠一个高校、一个系。譬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有汪辟疆、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等与本社长期合作并在《论丛》发文,如与清华历史系合办《论丛》,似乎成为同人刊物,势必不利于调动其他高校作者的积极性。曹的意见反映了本社同仁对《论丛》品牌的爱护珍惜之情。当然,对《论丛》的现状不满意,期待改进是与会者的共识。
《论丛》的现状可能改变的议论不胫而走,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插曲。《微型世界》的名誉主编江曾培闻知后,向前任社长李国章关说,请老李转告王兴康续办《微型世界》,如有困难,微型小说学会可每年补贴20万元。就当年物价水平言,一年20万元的补贴不是个小数字。那时本社财政情况不好,尚欠银行贷款数百万元。对于一向身体力行谨慎节俭、量入为出的当家人王兴康来说,每年20万元补贴是不小的诱惑,何况本来就面临刊号归谁使用的两难选择呢。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深感压力之重,深恐《论丛》改刊之议将付诸东流,难以实施。一次午饭间隙,邂逅赵昌平,我对他说:“现在只有你能力挽狂澜了!”赵昌平的学养、见识与威望在社内是首屈一指的,他从1994年就担任本社总编辑,连任至此已逾十年。我相信只要他下定决心,事情尚有可为。
不知道经过几多权衡、斟酌,社领导班子的最后决议艰难地产生了。主要内容为:一,停办《微型世界》,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刊号转给《论丛》使用;二,婉拒清华方的合办建议,《论丛》仍由本社主办;三,取消《论丛》的主编制,原由李国章、赵昌平任主编,至2005年第八十辑终止,成立京沪两地学者为主体的编委会,再产生执行编委,负责主持具体的日常事务;四,改刊后的《论丛》仍以季刊出版,每年四期。
这时已经是2004年的10月,张晓敏尚未调离本社。一天,张晓敏告我赵总的意见,拟由我担任《论丛》的专职编辑,年终考核以社内编辑平均奖计。我听后吃了一惊,说实在的,我虽然自昆明带回学界改革《论丛》现状的建议,并赞成恢复刊号出版,但从未有过染指《论丛》编辑的念头。我是学历史出身,不仅不懂文学、哲学,也没有编辑学术杂志的经验,只知水之甚深,何况《论丛》起点甚高,改刊后学界必然期待也高,这样的一份综合性国学名刊岂容我涉足,深恐力不胜任,有负厚望。于是我告张晓敏,容我想一想,过几天再答复。
连续几个晚上,我辗转难以成眠,挥之不去的始终是《论丛》这块金字招牌的吸引。我想起1963年在上海旧书店初见《论丛》的创刊号,也想起1981年我还在华东师大念书时,谢天佑、王家范两位老师在《论丛》上发表《评〈淮南子〉的无为思想》,连我们这些尚未入门的在读学生都觉得不简单,可见《论丛》影响力之大。我也想起近年来《论丛》的被学界诟病,等等。《论丛》是前辈们创制的宝贵的铜镜,为何不去拂掉它的尘垢使之重光呢?自1982年我当编辑至此已二十余年,积累了一些学术圈内的人脉关系,也有了一些编辑经验,社领导既有意让我试试,何不下定决心接受这场挑战呢?《论丛》的改刊虽是社领导的决策,毕竟由我带回了学界的希望与诉求,从这点上说,我也可算是“始作俑者”。一旦付诸实施时,似乎不应超然物外,袖手旁观。我并不企求发财,能有编辑的年平均奖已使衣食无忧,为何不敢一试呢?要做就一定得做好,先不夸海口,低调应试,但心中应有个标杆,这个标杆就是当年伯希和主编的东方学杂志《通报》!这样一想,我就决心“下海”了。由张晓敏陪同,我向赵昌平表示同意接手,赵总当场就讲了一句勉励的话:“只有你能做。”这未免使我受宠若惊,当然也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非做好不可也。
以后的几天里,我拟出了《论丛》改刊的工作设想,请赵总审阅。此时张晓敏调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由王立翔(原二编室主任)继任本社副总编,分管《论丛》。2005年1月上旬的严冬时节,赵昌平、王立翔和我三人赴京。先是与清华方葛兆光、张国刚、李伯重会面,介绍了我们对《论丛》工作的设想,包括仍由本社主办,改以刊号出版,成立编委会,实行执行编委制等,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当天下午与第二天上午,我们邀请了在京的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开了座谈会,宣布《论丛》即将恢复刊号出版的消息,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他们是从海内外学术双向交流,汉学国际化的大趋势背景理解这一举措的,他们贡献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以后均被改刊的《论丛》所吸取。
自北京返沪后,赵昌平、王立翔和我三人商定了《论丛》编委会构成人员名单,以京沪两地学者为主体。北京邀请了李伯重、李零、李学勤、秦晖、徐公持、陈平原、陈来、陈高华、张国刚、葛兆光、葛晓音、荣新江、阎步克、罗志田,上海邀请了王家范、朱维铮、周振鹤、陈尚君、孙逊、章培恒、葛剑雄、熊月之、刘永翔(均按繁体字姓氏笔划排序),又特邀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莫砺锋、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邢义田、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以及当时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陆扬任编委,三年一个聘期,并明确编委的主要职责是对《论丛》的编纂大计和具体执行提出意见,为《论丛》撰稿、组稿和审稿。
编委会成立后需要决定执行编委人选。社领导拟由张国刚和我两人担任。我与国刚很熟,他聪明热情,有学术判断能力,尤其是不惮繁杂,勇于任事,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当我把社里的意图告诉他时,不料国刚却另有见地。他说,你我两个都是搞历史的,而《论丛》是文史哲并重,应当有研究文学、哲学者参与担纲,建议以葛兆光为执行编委。这番话说得诚恳恺切,足见他的心胸宽广,为《论丛》考虑得周到。但是国刚的慷慨热情、当机立断,为杂事而不吝付出,又是其他各位所不及的,故而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向赵总汇报,赵总当即就给葛兆光打了电话,征得同意,执行编委便由张、葛、赵、蒋组成。
接下来的事就是正式上报各级主管部门,报告是高克勤执笔的,写得朴质坦诚。《论丛》的积稿也转交给了我。差强人意或已应允采用者均在第80辑(2005年出版)刊出,所以那一辑字数超量。我本以为,刊号是本社自己的资源,转一下应该很快就会得到批准,不料竟等了2005年整整一年!期间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桂晓风、邬书林分别到上海视察工作,我们都向他们汇报了,请求早日批复,但都无大效。后来听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说起,更改期刊刊名、构成内涵等,走完报批这一套程序,需有一年等待时间的准备,这就使我们很无奈。
2005年我已是《论丛》的专职编辑了。在等待刊号批转的时间里,积极地组稿、审读并处理前任遗留的积稿,忙得不亦乐乎。赵总认为改刊是一件大事,需要写一篇庄重的改刊词。但我觉得,1962年创刊号的《〈论丛〉编例》与1978年复刊号的《编者的话》,对《论丛》的宗旨已作了平实又恰切的阐述,似乎无庸再费词章表达。我的意见是以《〈中华文史论丛〉恢复刊号出版暨约稿启事》为题,低调地向学界表白改刊缘由。至于刊物今后能否重新赢得学界认可,并不在于改刊词写得如何汪洋恣肆、激荡人心。说实话,这方面我是有点私心的,我对办《论丛》没有经验,唯恐画虎类犬,事与愿违,不敢写改刊词,高调托大。赵总同意了,于是我写了《改刊与约稿启事》,赵总作了仔细的推敲润饰,并加了“本刊谢绝商务广告与出资刊文,以严肃学术,崇高品格”一句,这真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后被媒体记者广泛揄扬,成为《论丛》标志性的宣传语。直到今天写这篇回忆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改刊后的《论丛》继承了创刊以来一贯的传统,唯学术是举,没有收过任何一篇文章的分文版面费(今后并将一如既往),刊发的每篇文章我们都支付了稿酬,全部盈亏经费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自负的。
2006年《论丛》开始恢复刊号出版,由于准备充分,在第1期(总81期)、第2期(总82期)上汇聚了诸多名家的精心之作。第1期的作者有吕思勉(未刊遗稿)、葛兆光、陈平原、柳立言、陈弱水、张国刚、周勋初、莫砺锋、李零、周伟洲、蔡美彪等,第2期有李学勤、朱维铮、陈尚君、朱瑞熙、陈高华、贾晋华、朱鸿林、陈广宏、陈得芝等人文章(均按发表顺序排列),学界反应强烈。社长王兴康说,看到目录就觉得“眼睛一亮”。其实我并没有追求荟萃名家,完全是《论丛》蓄势待发的改刊品牌效应所致。友人王君曾提醒我,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尽聚名家于一炉,恐后事难继。这使我省悟,办杂志犹如万米长跑,不能竭泽而渔。诚如《细胞》杂志总编艾米丽•马库斯所言,期刊编辑必须保持公正且稳定的标准,这是“杂志长期发展和成功背后的关键因素”(引自《光明日报》2013年11月30日)。《论丛》不骄不躁地高品位运行着,至改刊第二年年底(2007年)就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指导委员会审定,入选为CSSCI来源期刊,自2008年至今已连续四届八年(2008-2015年)始终在列,保持在同类刊物排名前十位的核心期刊阵容之中,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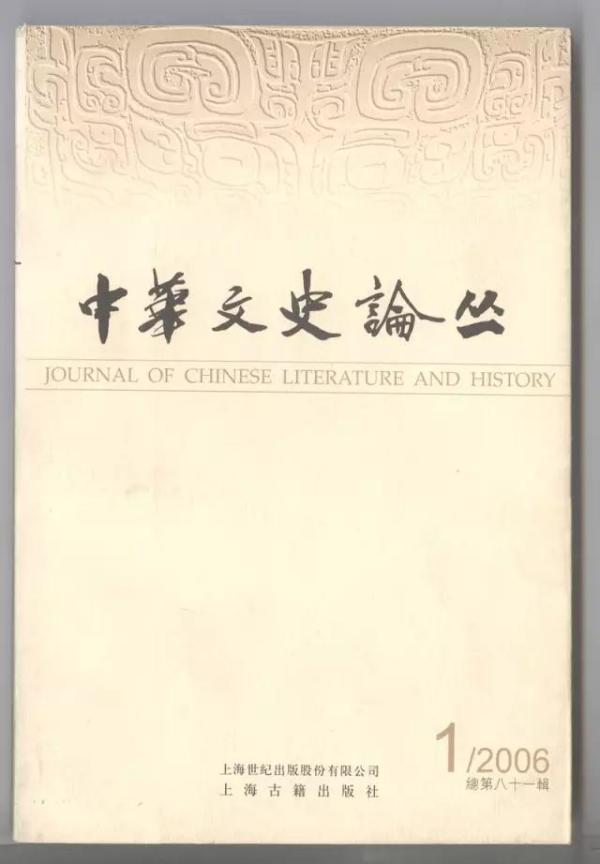
改刊后第一期
回忆《论丛》的这段改刊经过时,我不由得想起许许多多前辈、同行的关注勖勉,他们话虽不多,但以义相励。有的话也许他们讲过自己都忘记了,但我却铭记于心,不能释怀,今略述数则于此。首先是陈高华先生,2005年我们筹组改刊,我打电话请他出任编委,他一口答应,说“我觉得很光荣”,又说:“我相信有你在,就一定搞得好!”这真使我有知遇之感。几年来,不管困境与顺境时,都常常想起他的话,告诫自己不能辜负前辈的期许。又有荣新江,在改刊刚起步时,他告诉邓小南,虽有很多编委,“其实就他一个人(指蒋)在干”。多年后,在北京地区编委开会议论《论丛》得失时,他说:中华的《文史》编辑一直在换人,而“《论丛》最主要的是有蒋公在”。我在此述及他的这番话时,不是自我标榜矜夸,而是提醒“肉食者”保持责任编辑的相对稳定连贯对一本学术杂志的重要,同时也有悬鞭自警,夙夜在公之意。又如周振鹤,有次我跟他说起办《论丛》遇到的困惑与彷徨时,他说:“一个人一生能做成一两件事就不容易了。”顿使我如醍醐灌顶般猛醒,应从大处着眼,不能动摇。再如钱伯城先生,改刊数年后,他对我说:“《论丛》现在有了个好的主持人,你要坚持。”他的话尤使我想起《论丛》创刊、复刊、改刊的来之不易,更不敢懈怠,要对得起读者与作者的期待。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文末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看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今日再读此文,感同身受。
《论丛》改刊已达十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叙述这段经历,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作为本社六十甲子诞辰的纪念。《论丛》还在继续出刊,诚如诸葛武侯所言:“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现在,《论丛》已有了新生力量的参与,北大历史系毕业的硕士胡文波自2008年下半年加盟,至今实足做了八年多的编辑工作,成长很快,使我欣慰。也许再过些时日,我能为文,冷静客观地述评改刊后的《论丛》编辑与发文的得失,以为后来者的殷鉴。
(本文原题《一份学术名刊的艰难改刊》,原载10月18日《中华读书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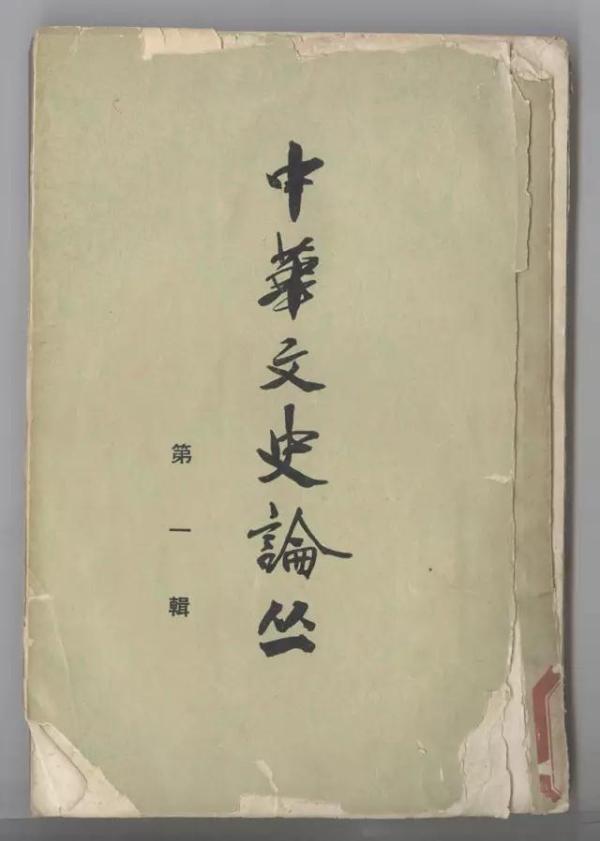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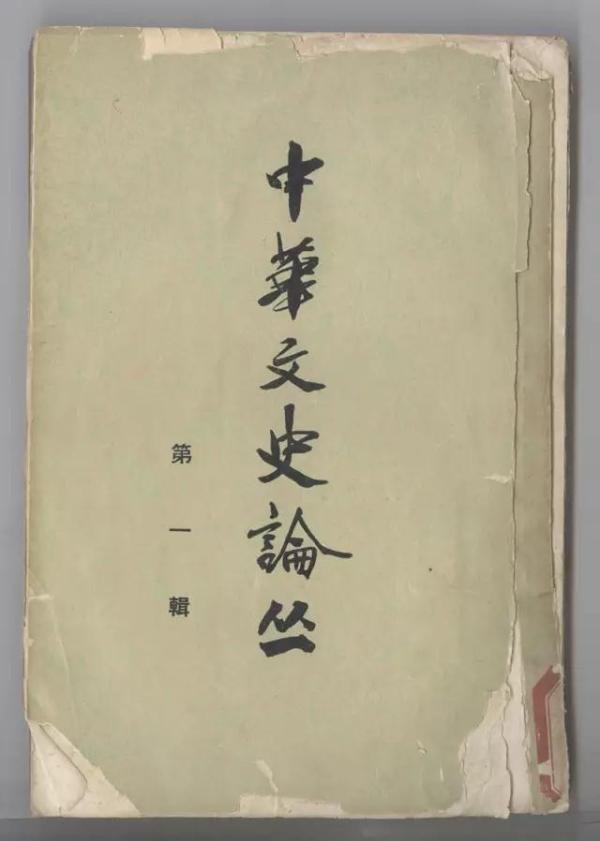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