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郭锡良
采访人:雷瑭洵
采访时间:2020年9月15日

图一:访谈间歇
受访人介绍:
郭锡良,1930年生,1958年北大中文系汉语史研究生毕业。现为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论文一百多篇。
采访人介绍:
雷瑭洵,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史。
雷瑭洵:郭先生好!适逢先生九十寿辰,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郭先生笔耕不辍,今年出版了《汉字古音表稿》单行本,重新修订了《汉字古音手册》,一直处在学科研究的最前沿。今年又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我们想请您来谈一谈您的求学、治学经历,以及中文系语言学科发展和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些情况。

图二:2020年9月20日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庆祝郭锡良先生九十华诞学术座谈会
郭锡良:我的祖父名叫郭光璧,是清末的补廩秀才,辛亥革命之后又上了湖南第一师范,与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同在师范二班,毛泽东是预科六班。我从四岁多就跟祖父母一起生活,从那时起,祖父就教我念《三字经》,之后又教我念《五字鉴》,也是押韵的,不过那时候我年纪小,五个字一句的我都念不好,祖父就把《五字鉴》改成了“四字鉴”。之后又教我《左传》,还有《幼学琼林》。过去上私塾强调背“四书五经”,我就跟着祖父背过一遍《左传》,因此作为同龄人我的古文功底比较好些。
1939年祖父去世,1940年我上了高小,1942年上了中学。读过岳云中学、赵氏三忠中学、南华中学等校。我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抗战期间要躲避日寇,学校都不得不停办,前后达三学期之多。在中学时,我的数学成绩比较突出,英语作文比赛还得过奖,后来就想报考理工科。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社会比较动荡,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基本没有学。
1950年春我在老家衡山望峰桥,种了六亩多地,学会了犁、耙、耖、耥。7月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到长沙考大学。就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的大教室里,把八个书桌拼起来当床,挺过炎热、多蚊的夏夜。先报考了华北十七所院校的联合招生,没有考取。接着又考了湖南大学和湖南农学院,当时因为高三缺课太多,担心理工考不上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报考了湖南大学中文系。后来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我不想学农,就进入了湖南大学。第一年还在复习数理化,想在第二年继续考理工。后来在班主任的教育下,开始改变主意。到二年级听了系主任谭丕谟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反而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因此读了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还有文艺理论方面的书都看了不少。三年级时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变成了理工科大学,中文系合并到武大。1954年夏天从武大毕业,保送到北京大学当语言学研究生。

图三:郭锡良先生在湖南大学(三排左九)
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队伍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在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十五个人,分成汉语史五个人,现代汉语五个人,语言理论五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我本来是想搞文学的,不过当时要服从组织分配,只好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我之外还有向熹、祝敏彻、齐冲天、孙宝琳。三个来自北大,两个来自武汉大学。
雷瑭洵:当时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
郭锡良:当年在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跟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说跟抗美援朝有关。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实际上是中苏合作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中国军威大振;从而也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1953年10月,苏联派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来到北大,开办四年制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学校匆匆地从中文系、东语系、西语系等几个系里抽了15个四年级的学生,就对付过去了。1954年又要建立汉语史这个学科,要招汉语史的副博士研究生,由胡乔木代表中央,决定把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来。
中山大学办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1953年毕业了一个班,人数在十个人左右,因此就把中山大学的整个系就调到了北京大学。当时一起调过来的教师还有岑麒祥、周达甫、黄伯荣等五人。王力先生到北大后,中文系设立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招收了语言学的研究生班。王力先生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招收了五个汉语史研究生。

图四:访谈现场
雷瑭洵:当时汉语史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怎样的呢?
郭锡良:王先生非常重视胡乔木交给他的任务,他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的重视,有很多人来听,有下一级的、外校的、进修教师,有一百多人。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
1955年上学期,除了1954年的三门课外,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
1955-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这个学年,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1956-1957年,有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语言学”,陆志韦先生开“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导读”(周达甫先生翻译之后作为讲义印发),金鹏先生的“汉藏语概论”,朱德熙先生后来在马学良他们主编的《汉藏语概论》序言里面说,6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过一次这个课,其实最早不是袁家骅先生,应该是金鹏先生。还有郑奠先生的“古汉语语法修辞学概论”,后来他还正式出版了这方面的专集。
本来还安排了两个课,一个是周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个是李荣先生的“《广韵》研究”,没来得及开出。等我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后才开出来,由我来担任助教。
这就是王力先生给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排的重要的课程,也是王力先生对培养汉语史研究生做的认真考虑。就我所知,这样的师资阵容和课程设置,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图五:王力先生与郭锡良先生
雷瑭洵:王先生当时是怎么做指导的呢?
郭锡良: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们在法国最早的两个语言学博士(另一个是刘复),也是我们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而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赵元任、李方桂很早就出国了,罗常培先生又比较早地去世了,所以20世纪领导中国语言学的主要领头人就是王力先生。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的培养计划设计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
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件事:他开设了一门课,叫做“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个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是有很大帮助的。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我跟着王先生三十几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导。
还有就是1959年王先生讲“古代汉语”,我做助教,以及后来参加编写《古代汉语》教材。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主要讲短篇散文,放得很开,常常拉得很远,讲得不是很成功。魏先生之后是杨伯峻讲,实际上是讲他的《文言语法》,带一点短的文章,讲几篇文章,这也不太成功,学生反映不佳。王先生是古汉语教研室的主任,他就只好自己来开古代汉语课。他一开课就建立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系。他这个课一开,就在第一教学楼一层最大的那个教室,不但是整个教室坐满,走道和门外都坐着人听课。王先生让我带着刚从武大、川大毕业的赵克勤和陈绍鹏三个人当助教,辅导课由我来讲。我还记得第一次到三十二楼去辅导,那时候是57级的四个班,晚上到二楼一间寝室坐下,队伍排得很长。同学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我都一一答复。然后有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齐桓公伐楚》中的“寡人是问”怎么分析,我回答说:“‘寡人是问’就是‘我问这个’,‘是’是前置宾语。”他立即问:“怎么杨伯峻不是这样解释的?”我说:“哦,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儿,他的语法体系受叔父的影响较多,我是按王力先生的体系分析。”几个学生同时惊奇地问道:“你是哪里毕业的?”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本科由四年制改成了五年制,没有毕业生;他们知道从外校分了几个毕业生来,他们的提问是要为难辅导的。“我是北大的啊。”“哎,怎么不认识你?你住哪里?”“我住在19楼。”“啊!研究生毕业!”楼道里的队伍也就散了。这说明王力先生的培养计划和指导帮助我顺利地过了一关。
雷瑭洵:您在60年代先参与了《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后又主持编写了一套《古代汉语》,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经历呢?
郭锡良:王力先生从1961年开始编《古代汉语》,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极“左”路线已经有所调整,提出全国要编文科教材,中文系就要编“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七门课的教材。“古代汉语”还是重点课程,教学计划提出要开两年半,目的就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周扬明确地点名叫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

图六:《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组成员及审阅者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分别为:萧璋、叶圣陶、王力;第二排左起分别为:吉常宏、赵克勤、马汉麟、祝敏彻;第三排左起分别为:郭锡良、许嘉璐、刘益之)
郭锡良:当时成立了文科教材编辑室,由冯至先生当中文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丁声树、季镇淮是副主任,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十多人是委员,我是秘书。《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以王力先生在北大的“古代汉语讲义”作为基础,先由王力先生拟定出一个详细的提纲,编写组成员根据提纲分工编写。编写组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的人员构成,两老(王力、萧璋)两中(刘益之、马汉麟)五青(吉常宏、祝敏彻、郭锡良、赵克勤、许嘉璐)一共九人。1961年8月报到,没有休假,加班加点地干。工作程序是先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经全组传阅,把意见写成标签贴上。然后王力先生召开会议讨论,对这些分歧进行解释或者解答,最后由他下结论。这个过程对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十分有益。王先生怎么样分析意见,怎么样下结论,这是我得益最深之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要查阅很多资料,才能真正读懂,才能注释精当。每一节通论,都要反复推敲,才能站得住脚,写得精要。
在1987年全国的第一次的高校教材评审上,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得了特等奖。中文系有两个特等奖,1988年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教材授奖仪式上,费振刚代表《中国文学史》,我代表《古代汉语》去领的奖。

图七:学科教材特等奖颁奖合影
(第二排右五为郭锡良先生,右四为费振刚先生)
郭锡良:说到这里,我还想要说一件事情,当时冯至先生是文科教材中文组的编审组长,也担任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审。他看过我写的《古代汉语》的稿子之后,让我帮他看一遍《中国文学史》的稿子。我这个人从来大概就是有一点不知高低的,所以我也不管编者是谁,就在上面提出意见。《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冯至先生就一定要把400块钱的审稿费给我,我坚决不要。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工资只有七十几块钱,听说你母亲病了……”当时我的母亲住了两次院了,我欠了不少账。我真心非常感谢冯至先生,我一辈子都感谢他。
在“文革”中,王先生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要把他打成美国特务。文革后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系里让我负责古代汉语教学小组,当时王先生的《古代汉语》没办法用作教材,只得匆忙挑选了一些篇目凑成一本文选,教了一两届。1975年,我提出要为学员编写一本古代汉语教材,就招了一个古代汉语进修班,有刘宋川、许青松、吕坚等几个进修教师,还有一些刚留下来的老师,借“开门办学”的名义,拉到校外编了一年,搞出了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后来文革结束,高校恢复招生,教材编写成了教研室的迫切任务。不过当时教研室很多成员的积极性还没调动起来,我借着这个机会,努力团结教研室,多写多做。实际上上册主要是改编出来的稿子,中册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都参加了一些工作,蒋绍愚做的多一些,下册仍有三分之一是我写的。那时候我一心扑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上。最终这本教材在1979年完成,1981年出版。这本书也获得了全国首届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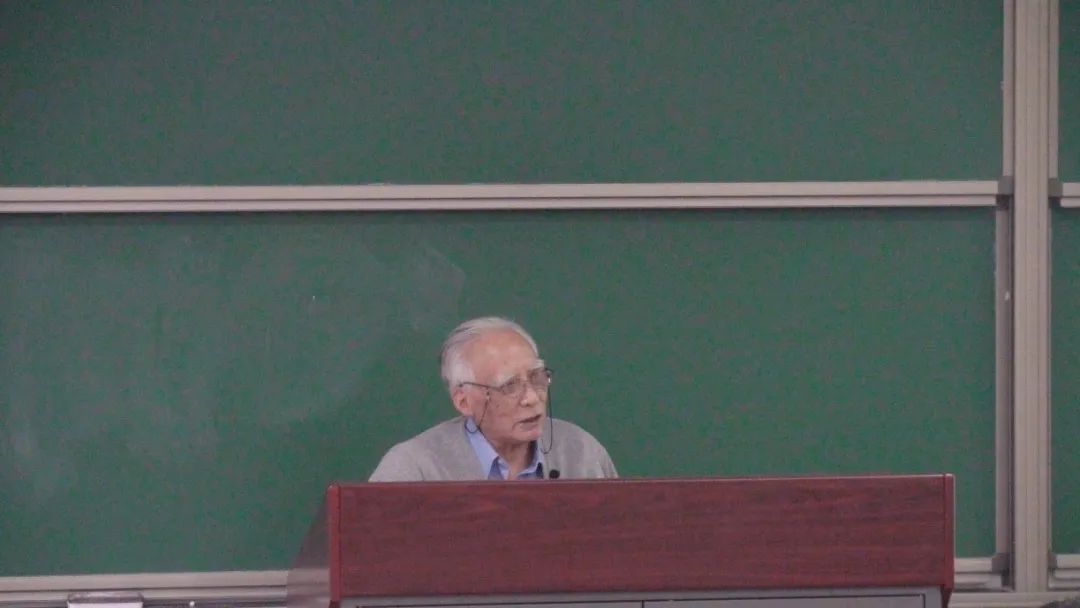
图八:郭锡良先生在课堂
雷瑭洵:您在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主任,现在古代汉语教研室开设的很多课程,比如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古文字学”这样的课程,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去设计的?
郭锡良:我先讲一个故事,大概是在批了胡适、胡风,打了右派之后,还在批右倾时,极“左”路线把中西文化一股脑打入了封、资、修泥坑。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杨晦先生,我留系工作之后当中文系分管研究生的秘书,分管研究生。批的时候,文史楼的大门口贴一张大字报,一边是文学的书籍,一边是语言学的书籍,一只大公鸡两只脚分别踩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书籍上面,名为“有鸡联系”。因为杨晦先生提出语言跟文学是有机联系,有一些学文学的人不想学语言学,学生去反对他,就贴了大字报。我有一次就跟杨晦先生去汇报研究生的情况,汇报完以后就笑了。我说:“杨先生,文史楼的前面贴了一张大字报你看到没有?”他说:“是什么?”我就把这张大字报一讲,他就对我说:“不是有机联系是什么?还好笑呢。”我说:“不是好笑,是那张画画得好笑。”杨晦先生说:“有什么好笑的,学语言的不要学文学吗?学文学的不要学语言吗?”我其实不是同意大字报上的意见。这个故事可以说明,杨晦先生坚持一个重要认识:搞文学不懂语言学,也就是不懂古代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就落实不了字词句,变成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正如我在《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一文中所指出的,短短的一首二十字的绝句,蔡某却犯下许多低级错误。
2000年我从中文系退休,现在的一些情况已经不太清楚了。从人才培养上,我能感觉到王先生的一些想法:中文系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必须是古今中外都通的,不但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王先生的这条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作为大学的教师,连四书五经都读不懂,甚至连看都不看,这样行吗?咱们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都要去做大学老师,因此需要给他们讲这方面的知识,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搞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现在我们的语言学专业的本科生大多数都要读硕士、博士,在培养本科生时,尤其是我们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的本科生,这一些课也都应该上。
我管教研室的时候,在本科生教学上,除了继续开设“古代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汉语史”这一类基础课之外,还提出要开设一批原典精读课。

图九:郭锡良先生夫妇与学生们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刘子瑜、徐寒玉女士、郭锡良先生、易福成;第二排左起:金树祥、孙玉文、邵永海、杨逢彬、卢烈红、张猛)
雷瑭洵:您桃李遍天下,在培养研究生时都有哪些理念呢?
郭锡良:培养研究生呢,我一般要求比较严。1979年我跟王力先生招了五个汉语史的硕士生,也就是宋绍年他们那一班。我要求研究生必须听哪些课,要求必须通读《说文解字注》,还有《马氏文通》,这些都是经典。要多读书,现在有的人,也不爱读书,就好找一点西方的什么理论,然后自己提一点新的所谓看法,这种缺乏根基的创新实在是不值得鼓励的。
我自己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整个不超过二十个人,这其中也包括外国留学生。其中也有个别的后来不搞汉语史了。当时我给硕士生就定了四门课:古音学、《说文解字》、《马氏文通》、古文字学。要博古通今,同时要求文学也要通,文史哲都要通。要落实字词句,就得知人知世。只有博古通今,在方法论上面才能够走王力先生的道路,这样的研究就可以上道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搞文学的先生,对这个方面重视不够。

图十:2013年古代汉语教研室迎新年联欢会(第一排左起:孙玉文、宋绍年、郭锡良、唐作藩、蒋绍愚、张联荣、张猛;第二排左起:刘子瑜、宋亚云、胡敕瑞)
雷瑭洵:您对汉语史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期许或者是展望?
郭锡良:我觉得前面那些年,一直受到文革的影响。最近这些年,我看到了我们中文系现在有《论语》导读、《孟子》导读,先秦的这些书籍的导读课,这是向好的方面转。
现在中文系确实有一种“厚今薄古”的势头,对于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都考虑得比较少。我们古代汉语教研室,在我做教研室主任时就提出要15个编制,最多时到了13个,可现在只有8个教员了。古代汉语包括的学术范围很广,文字、音韵、词汇训诂、语法修辞还有文学语言史。我很担忧,要是这样下去,不少学校都可能超过我们。中文系古典这一块,都处在危急的关头,这不是危言耸听,希望能够秉持博古通今的理念,用周扬的话来说,“今”不到一百年,“古”则有几千年,不要拿一百年不到的“今”去压过几千年的“古”。
如果大家要搞汉语史的学问,力气就一定要放到古代文史哲的典籍,包括小学上。从《尔雅》起,历代小学名著,清代的从顾炎武起的七家,包括后来的章炳麟、黄侃、钱玄同的一些著作都要读,这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现在连一个《新华字典》都收了一万两千字以上,《现代汉语词典》更有一万三千多字,如果作为汉语史研究生,要看得出来他们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要吸收西方影响。

图十一:郭锡良先生与采访者
雷瑭洵:您在中文系学习工作已经60多年了,您觉得中文系有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如果用一两个词来说中文系的精神,您大概会选什么样的词?
郭锡良:中文系的精神,就是前面我讲的意思。中文系大多数教师还是博学多识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雷瑭洵:好的,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郭先生。
这是“中文学人”系列专访的第4篇文章
往期回顾:
助理采访:李泓霖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