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鲁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年12月出版),岳永汉口述,林瑞五整理,原标题《我在日本做苦力》

正文
我叫岳永汉,幼名岳山,今年七十四岁,住鲁山县马楼乡马塘庄村。曾被日军抓至日本东京南诺诺坞当了十个月的苦力。日本投降后,又回到祖国。
我于一九二一年出生,自小随父亲在家种地。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去宝丰县走亲戚,路过闹店河时,被中央军十三军抓去当了兵。家里人还不知道音信。当兵驻地在郾城、漯河一带。一九四四年春,麦梢快黄时,部队在漯河南门外和日本鬼子碰上了。两相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枪声紧紧松松,不知打死了多少鬼子兵,也不知自己人牺牲了多少,反正双方伤亡都不轻。在漯河东寨墙边起,俺这一部分四百多人,被日本人抓住当了俘虏。先是被关押在郾城监狱住了四五个月。看守都是日本人。他们怕俘虏们暴动,开始一星期未给粮食吃,监狱院里的草、树皮都让给啃光了,饿死、害病死的不计其数。后来,他们用秫秫、小谷子熬成稀米汤让喝,我勉强没被饿死。才住到郾城监狱时,一天下午两三点钟,一个站岗的日本人,用刺刀刺着玩,猛不防照着一个俘虏的腿肚子就刺了下去,谁知刺住了大腿上的血管,血流如注,当即就死了,惨得很。
之后,我们又坐火车被押到山东济南城新华院。在新华院,住得挤不下,日本人就用竹杆别着让侧身睡,翻身都翻不过来,一吹熄灯号,就得睡,睁着眼也打,解手得排队。有的俘虏拉肚子,坚持不住,拉在了门口,日本门岗竟让舔起来,就这样污辱中国人。冬天,下多厚霜,冷得很,只叫穿一个裤头跑操。看管严得很。
在新华院住了大约十来天,又坐火车到青岛,以后开始坐船,坐的都是三层舱、两层舱,地方小,闷得很,很多人头晕脑涨,看管人也不叫出来。同行的总共两只船在海里走了两天后,另一只不知啥原因,沉了下去,一船人都死了。我们这一只又拐回来,停了一天,又走了,这次,我们在海上整整坐了十天十夜的船,到了日本。
到日本东京正南两站地一诺诺坞,在码头上,作装卸轮船的苦力。装卸时由日本警察看管着,稍微不慎就挨骂挨打。实行的是换班制。每班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两班日夜不停。那里天天下雨,只要一见云彩就下雨,当地人都穿一种草拧的透空鞋。我们是不能来回去找那种草的,也没技术和时间,更没钱买。只有赤巴脚扛麻袋包。冬天下半尺深雪,还是赤脚干活。脚常常被冻得红肿。特别难忍的是一顿饭六两馍,馍是用秫杆、稻草、黄豆粉搅成的混合面蒸的。喝的汤是鱼骨汤,即煮鱼骨的水加点菜。终天饿肚子。后来发现卸的货中有玉米、黄豆,警察眼扫不见,就弄开抓着吃,再装口袋里些留着以后吃。然而,这些生东西吃少了还是饿,吃多了不消化,拉肚子。在日本过了一个春节。他们年关也敬神,敬神用的是蒸的大米面馍,苦力们饿得慌,也不知谁给偷吃了,他们让苦力们站成队,从排头用扁担一个一个打,审问。我个子高,站的是第一个,先打我。接连打了三个,他们看上百号人也不好问出是谁,才罢了。苦力们经常生病,病了,除难友们相互照顾外,别的没人管,死了用火一烧,骨灰盒一装了事,日本投降后,一部分骨灰盒他们让苦力们带回,可是,死去的同胞们,谁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呀,都扔到海里去了。那时,我也真想着难回来啦,啥时有病一死,落个骨灰盒就够不错了。
这里除看管我们的警察是男的外,其它做工的日本人中,几乎全是女的。住的人家也不见男人的影。男人们都打仗去了。住的地方门朝外,都没院子,设计的都是拉子门,手一拉就开,再一拉关上。他们对门户看管得不严。家家户户差不多都订有报纸,送报人送到谁家,不管家中有无人,手一拉送进去,再一拉关住。我们为获得外面的消息,只要看看身边没警察,就一拉一关赶紧取出报纸看。日本字和中国字有不少差不多,开始我们看不懂,但看得多了,意思也就领悟了不少。有一次我们看过后领悟出:中国苦力再叫干七天就叫回国啦,心里高兴,又一想这是为啥?一定有大事。后来在码头上观察,发现日本人行踪异常,不象以前那么嚣张了。我们一商量,说一天也不能再干了。先出去三四十个人看看,回来再说;谁知这三四十人一走,后边的人也坐不住,跟着就都出去啦。也是被日本人压迫、惨害得久了,出去后,我们先砸开了他们枪支仓库的门,机枪、手枪、子弹尽其所拿,临时推举出连长,排长,总指挥,与日本人战开了,逢了日本警察就打。整整打了三天。当地人跑得没了一个,日本警察也被打得不知去向。后来,来了美国的部队,叫去俺的代表,说德国垮台了,长崎、广岛扔了两枚原子弹,日本投降了,正在谈你们回国的问题,但是一切事情得有纪律。并将我们挑头打的,胸前戴有牌号的二十名劳工暂时拘留了起来。怕我们再出去闹事。两天后,在日本做苦力的四千多名中国人回国,我们被放了出来,也随着回来了
回到青岛,国民党九十四军将俺接住又当了兵。到天津又干了几年。一九四九年春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我想着几年没回家了,老想家,回来看看,一到家事多,也不想再去了,就在家一直种地。我还想着叫日本人赔偿我的损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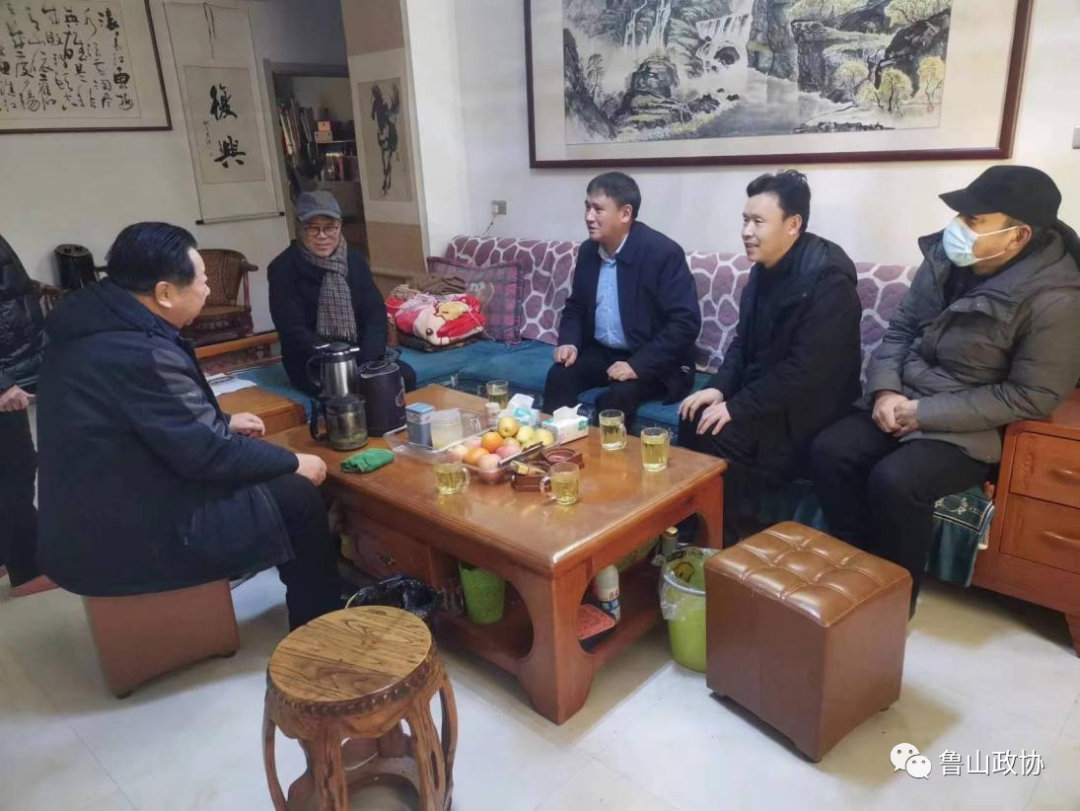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