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363031535
投稿信箱:wszs@263.net.cn
新浪微博 :@文史知识杂志
官方网站:中华书局/文史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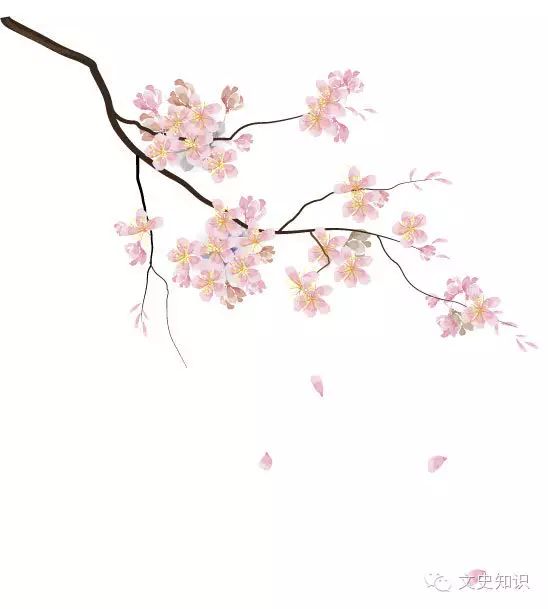
元代的离婚与再嫁
一
中国封建社会“离婚之原因,依礼与法,其要有三,曰违律为婚,曰义绝,曰七出。三者而外,更有以其他原因而离异者,随代多有”(陈鹏《中国婚姻史稿》,606页)。“违律为婚”就是“依律不合作婚,而故违者”(《唐律疏议》卷14《户婚》)。唐律所定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十二条,这些条文多数在元代仍起作用,如同姓结婚、有妻更娶、居父母夫丧嫁娶、奴娶良人为妻等。至元八年(1271)二月,“中书省奏定民间婚姻聘财等事”,其一是“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这项规定便在“依律不合作婚”之列。其他如同姓结婚、奴娶良人为妻、居丧嫁娶等违律为婚判处离婚的条文,后来亦陆续公布。“义绝”指夫对妻及其亲属有打、杀、奸等行为,或妻殴詈夫之亲属、与夫之亲属通奸、妻欲害夫等。从元代具体案例来看,定为“义绝”的行为有将妻转嫁卖休、逼令妻妾为娼、男妇告翁奸、翁调戏男妇、女婿虚指丈人奸女、殴伤妻母、夫虐妻损伤身体、强奸妻前夫男妇等(《中国婚姻史稿》,608—611页)。“旧例……犯义绝者,离之,违者断罪”。“旧例”指的是金朝法律,元朝政府对此是认可的(《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七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离婚条件,“旧例: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嫉,七恶疾。虽有弃状而有三不出之理。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而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即不得弃。其犯奸者不用此律”(《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七出”最集中地表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条重要的法律,历代相承。但是,从现存元代文献来看,以“七出”为理由判决离婚的事例为数甚少。“违律为婚”和“义绝”两类案件很多。
此外,离婚还有其他原因。比较常见的,一是夫逃亡听离。至元八年(1271)二月“中书省奏定民间婚姻聘财等事”中规定:“一,为婚已定,若女年十五以上,无故五年不成(故谓男女未及婚年甲,或服制未阙之类,其间有故,以前后年月并计之),及夫逃亡五年不还,并听离,不还聘财”(《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校注》,162页)。一是夫犯罪听离,但限于未成婚者。“诸女子已许嫁而未成婚,其夫家犯叛逆应没入者,若其夫为盗及犯流远者,皆听改嫁。已成婚有子,其夫虽为盗受罪,勿改嫁”(《元史》卷103《刑法志二•户婚》)。元朝法典《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收了四个案例,三个案例是“定婚未嫁,其夫作盗”,允许离婚,另行改嫁。一个案例是男女成婚“已有所出,虽曾作贼经断”,不许离异(《校注》,164—165页)。但更多的是夫妻不和导致离婚,大多都是男方提出的。当时把离婚称为“休弃”、“休妻”,说明是男方的主动行为,女性是被动的一方,双方是不平等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为了另娶赵盼儿,便把原来妻子宋引章休了(关汉卿作,《元曲选》,193—205页)。亦有女方要求离婚之事,则多因男方贫穷之故,在赘婿婚中时有发生。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中,刘二公嫌女婿朱买臣贫穷,“不肯进取功名”,便要女儿玉天仙提出离婚(作者佚名,《元曲选》,859—881页)。《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朱太守风雪渔樵记》都是文艺作品,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提出离婚,都要经家长同意:“又嫁女、弃妻皆由所由,若不由所由,皆不成婚,亦不成弃。”(《通制条格》卷3《户令•嫁娶所由》)。“所由”即所主、所从,指家长。
二
凡离婚都须立休书。元朝政府规定,“若以夫出妻妾者,分朗写立休书,赴官告押执照,即听归宗,依理改嫁,以正夫妇之道”。也就是说,离婚后男方一定要给女方“休书”,经地方政府核准,才算完成(《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休弃•离异买休妻例》)。女方提出离婚,也要男方出具休书。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为了娶赵盼儿,便将妻子宋引章赶走,给了她“一纸休书”。休书上有周舍的“手模印五个指头”。后来打官司,休书成了重要的物证(《元曲选》,203—205页)。杂剧《渔樵记》中,玉天仙向朱买臣索要休书,上面写道:“任从改嫁,并不争论”,并有“左手一个手模”(《元曲选》,868页)。应该指出的是,大德七年(1303)发生一起离婚案件,“东昌路王钦因家私不和,画到手模,将妾孙玉儿休弃归宗。伊父母主婚,将本妇改嫁殷林为正妻。王钦却行争悔”。刑部认为,“王钦虽画手模将妾休弃,别无明白休书,于理未应。……今后凡出妻妾,须用明立休书,即听归宗,似此手模,拟合禁治”。中书省批准(《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据此可知,原来用“画手模”休弃妻妾的做法是流行的,到大德七年才被禁止,要求必须“明立休书”。元代休书的文本已不可见,推测大德七年前的休书应是在纸上写明休妻或妾,写明“任从改嫁,并不争论”,画手模(五个指头)为证。大德七年后的休书则写明休妻或妾,除上述文字及本人手模外,还应有相关人氏的签名或手模,并经官府印押认可。《救风尘》、《渔樵记》中的休书是前一种,如在大德七年以后,就不能在打官司时作为证据了。
元代文献中常见“卖休买休”字样。丈夫以休弃为名卖妻称为卖休,他人出钱要丈夫休妻称为买休。至元八年(1271),御史台的一件文书中说:“陕西道按察司申,‘体知得京兆府一等夫妇不相安谐者,卖休买休。’若不禁断,败坏风俗。”(《通制条格》)这是因夫妻不和引发用钱买卖妻子。杂剧《救风尘》中,妓女宋引章被周舍诱骗成亲,屡遭毒打,写信回家向姐姐赵盼儿求救。赵盼儿对宋母说:“妳妳,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宋母回答道:“他说来,有打死的,无卖休买休的。”(《元曲选》,198页)赵盼儿的意思是将银子给周舍,让他休妻,以此使宋引章获得自由,即买休。这对周舍来说就是卖休,但周舍坚持不肯“卖休买休”。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史台的一件文书说:“山东廉访司申:‘去岁灾伤,百姓饥荒,以致父子兄弟离散,质妻鬻女,不能禁止。又有指称买休,明受其价,将妻嫁卖。’礼部议得:‘父子夫妇,人伦至重,比年阙食,往往嫁卖,俱系违法,拟合禁约。’都省准呈。”(《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卖妻妾》,《校注》,194页)这是因贫困收钱卖妻,却用休弃的名义。桂阳路谭八十一“为过活生受,写立休书,得讫谭四十三财钱,将妻阿孟转嫁与本人为妻。据谭八十一与本妇已是义绝,又系卖休买休,俱各违法”。地方官府判处“谭四十三与阿孟离异归宗,其谭八十一元受财钱依数追没相应。各人罪犯已经钦遇释免。别无定夺”(《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休弃•离异买休妻例》)。在这起案件中,谭四十三是买休,谭八十一是卖休。无论是夫妻不和或是贫穷导致的卖休买休,都是用钱赎买的,女性完全成了商品。
三
离婚的妇女以及夫死的寡妇,都会面临再婚改嫁的问题。从秦汉到宋朝,尽管有人提倡守节,但妇女再婚为社会所认可,再嫁妇女一般不受歧视。到了元代,一则是前代社会风气的延续,二则是受蒙古收继婚的影响,女性再婚改嫁现象,无论在北方或是南方汉族居民中间,都是普遍存在的。大德七年(1303)江南行御史台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风俗浇薄……夫亡不嫁者,绝无有也。”(《元典章》卷42《刑部四谋杀一•误杀•打死强要定亲媒人》)这是江南的情况。至大四年(1311)上都留守的一件呈文中说:“妇女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乃至齐衰之泪未干,花烛之宴复盛。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官民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北方的情况。元末诗人陈高感叹道:“烈女无异志,兹事今罕闻。风俗日以降,朝寡暮求姻。”(《汪节妇诗三首》,《不系舟渔集》卷3,《四库全书》本)可与以上文书相印证。郑州(今河南郑州)妇女尹氏的例子很可以说明问题。郑州霍耀卿,妻尹氏。“至元间,尹氏夫耀卿殁,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妇之行一节而已,再嫁而失节,妾不忍为也。’姑曰:‘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独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尔。’姑不能强”(《元史》卷200《列女传一》)。从这段婆媳对话可以看出,妇女再嫁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为社会舆论所认可,并不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元代的日用类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刊载有妇女再嫁的《聘启》和《回启》(《别集》卷3《婚礼门》),另一种日用类书《事林广记》载有《夫亡无子告据改嫁状式》(至顺本《别集》卷4《公理类告状新式》),这些文字格式堂而皇之出现在当时流行的日用类书中,正是再婚普遍和社会舆论认可的明证。大剧作家关汉卿的《望江亭中秋切鲙》中,官员白士中娶寡妇谭记儿为妻,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社会各阶层女性都存在再婚现象。富贵之家虽然衣食无虞,但夫妻生活是人类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要求,而且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寡居有诸多不便,特别是容易受人欺凌,因而即使是富贵人家的离异女性或夫死寡妇亦很自然向往再婚。元末陶宗仪在他的著作《辍耕录》中记录叶县军人李清之妻张春儿殉夫事,为之感叹道:“春儿生长寒微,不闲礼节,而知夫妇大义如此。顾世之名门巨族,动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岂不为春儿万世之罪人也与!”(《辍耕录》卷20“夫妇同棺”)另一位元末文人孔齐说:“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妇女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兄弟以不分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此论若浅近,然实痛切,盖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终,阴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怀不平,未若此言之为愈也。”(《至正直记》卷2“妇人不嫁为节”)可见名门巨族的女性企求再婚亦是普遍的。《望江亭中秋切鲙》中改嫁的谭记儿,原来便是学士的夫人。她说:“我想做妇人的,没了丈夫,身无所主,好苦人呵。”于是,“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了罢”(《元曲选》,1657页)。至于贫困的家庭,寡妇生活更是备极艰辛。当时有人说:“妇人之苦,莫苦于家贫、子幼而夫早丧。”(梁寅《刘节妇传》,《石门先生集》卷3)元、明之际著名作家宋濂说:“呜呼,妇之青年丧夫最号多艰。傥居贵富,家有仆媵足以备驱役,阖庐足以蔽风雨,粟帛足以供衣食,犹可自安。苟或茕茕吊影,室如悬磬,忍寒夜织,机声与候虫齐鸣,达曙不休,自非铁石心肠,未必不为之动也。”(《王节妇汤氏传》,《宋文宪公全集》卷27)宋濂笃信理学,写了不少颂扬妇女贞节的文章,但他不得不承认守节对妇女来说是很艰难的事情。上述夫亡无子申告改嫁的《状式》中写道:夫亡无子,“当目户下别无事产可以养赡,委是贫难生受。若不具告给据改嫁,情实寡居过活生受”。这种因贫困而被迫改嫁的状况相当普遍,所以才会列为一种《状式》。应该说明的是,女性再嫁一般并不需政府批准,但对于夫亡无子的人户来说,妇女再嫁就意味着这一户在户籍上消除,所以要经官府核准。
四
元朝政府尽管提倡贞节,但对妇女再婚一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只对几种情况加以限制。一种是服内改嫁。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妇女在夫死后需要守制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守制期满后,便可改嫁(《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嫁娶•舅姑不得嫁男妇》)。如在守制期改嫁,就要断罪判离。至元十五年(1278)漳州路(路治今福建漳州)妇女杜阿吴丈夫在正月十二日病死,二十八日便改嫁他人。被告发后,判决杜阿吴“杖断七十七下,听离,与女真娘同居守服,以全妇道”。后夫、媒人分别断四十七下、四十下(《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服内婚•焚夫尸改嫁》)。后来类似的案例,改嫁妇女杖断六十七下,离异。媒人等亦断罪(《元典章新集》《户部•婚姻•服内成亲•夫亡服内成亲断离与男同居》,《至正条格断例》卷8《户婚•居丧嫁娶》)。“守服”就是守制。另一种是朝廷命妇,至大二年(1309)九月,元武宗在立尚书省的诏书中宣布,对官员父母妻子行封赠之制(《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封赠•流官五品以上封赠》)。至大四年(1311)上都留守上言:“见今尚书省奏准封赠流官父母妻室,颁行天下,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吾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立为定式。如不遵式,即将所受宣敕追夺,断罪离异。”他的建议得到礼部和中书省批准施行(《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官民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延祐三年(1316)中书省颁发“封赠通例”,其中规定:“妇人因夫、子得封者,不许再嫁。”(《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封赠•流官封赠通例》)到了延祐四年(1317),又有监察御史提出,“除蒙古人外,汉人职官正室如系再醮失节之妇,不许受封。庶几士夫之家敦尚节义,妇人女子亦知有耻”。亦经皇帝批准施行(《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封赠•失节妇不封赠》)。不许受封妇人再嫁和不许再嫁之妇受封,实际上是一回事。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朝廷一再重申不许命妇再嫁,仍有命妇公然反对:“某帅妻诣官自陈,愿上所受封,比齐民得自嫁。”(程文《节妇汪夫人传》,《新安文献志》卷98,《四库全书》本)这位“帅妻”是很有勇气的。当然,她敢于这样做,主要还是当时再嫁在社会上并不受歧视。
此外,朝廷还不许几种妇女再嫁。一种是交趾(今越南北部)出征军人的家属。至元二十六年(1289)广南宣慰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出征交趾军人多有隔绝溃教,各家为见久不回还,父母将各军妻小改嫁,以致分居,殆失人伦,咨请定夺。”礼部认为,“出征军人未知存亡,抛下妻小,其父母不合一面改嫁,合咨本省改正。仍将主婚人等断罪相应”。中书省批准这一意见(《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军民婚•出征军妻不得改嫁》)。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对于其他地区出征军人家属也应是适用的。还有一种是两广官员的遗孀。大德三年(1299)广东道廉访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切见广东烟瘴重地,北来官员离家万里,不伏水土染病身死者不可胜数。抛下妻妾不能守志,改适他人,将前夫应有资财人口席卷而去。亡殁官员骨肉未寒,家私人口已属他人。况在广亡殁官员老小,出广已有应付站船定例,如蒙行移合属,严加禁约,今后在广仕宦官员,若有身故抛下老小,听从本处官司依例起遣还家,不得擅自改嫁。如有违犯事发到官,断罪听离。前夫家私若有散失,勒令陪偿。”礼部同意这一建议,中书省批准(《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官民婚•广官妻妾嫁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规定是不许官员遗孀在广东改嫁,要将她们起遣回家,至于回家以后改嫁,则不在限制之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08年第9期
本刊刊发文章未经允许,不得以微信等形式擅自在网上传播,文章版权归《文史知识》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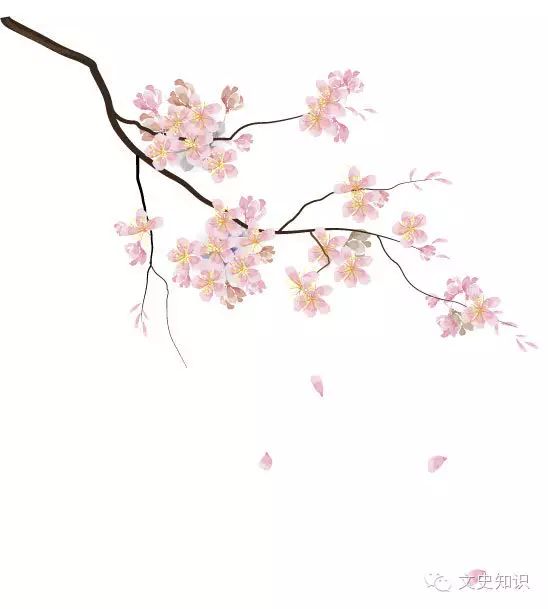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