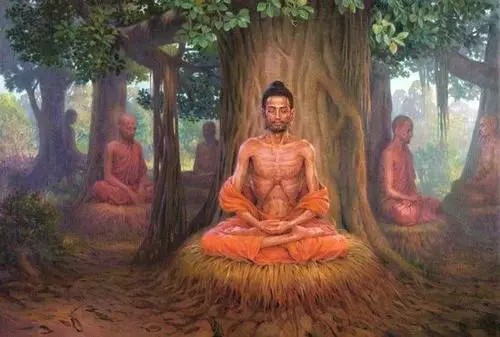
释迦摩尼正等觉后曰佛或浮屠
"浮屠"和"佛"都是外来语,指的都是释迦摩尼成了正等觉以后的名号。这两个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问题有很大的争论。另外,中文里还有有种种不同的译名,其中最古的译名有浮屠、浮图、复豆和佛。
梵文“Buddha”的内涵变迁过程。根据季羡林先生考证和分析,释迦摩尼成了正等觉以后的梵文叫做“Buddha”,是两个音节。初期译经的佛教徒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调,不会按中国的老规矩把一个有两个音节的字缩成一个音节,用一个中国字表示出来。况且“Buddha”这一个字对佛教徒是何等尊严圣神,他们未必在初期有勇气把它腰斩。季羡林从文字学方面考证为,梵文“Buddha”到了龟兹文变成了 put(u上平声)或put;到了焉耆文变成了pat(a上有两点),而我们中文的“佛”字,就是从就是从以上翻译出来的。而浮屠、浮图、复豆的来源是一种印度古代方言。
焉耆—龟兹文大致的区域是三至九世纪在我国新疆地区,十九世纪末发现于新疆的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这是一种印度婆罗米字母斜体,同于阗文字形相似,所记录的语言则属印欧语系Centum语支,旧称吐火罗文。对于世界语言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浮屠、浮图、复豆作为印度方言的例证之一,从佛经《四十二章经》上可以反映出来。梁启超先生认为《四十二章经》是部伪作,而许多学者并不认可梁启超的说法。汤用彤先生说“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像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次经,固有二译”。季先生认为其中一个译本当时很有可能是从印度直接翻译过来的经典,“浮屠”这个名词的形成就在这时候。到了汉末三国的时候,西域很多高僧和居士都来到中国传教,这时候,他们的本子不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的名字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考证“浮屠”和“佛”的意义所在。季羡林先生结合20世纪初的考古发现和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繁复的考证,发现了“浮屠”和“佛”在认知中国佛教的传播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解决了中国佛学史上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佛传入中国的两个阶段及路径,一个是传入的时间。第一个路径是从印度到大夏(大月支)再到中国 (Buddha—bodo,bodo,boudo--浮屠),时间大概在西汉汉文帝至汉武帝期间;另一个路径是从印度到中亚新疆小国再到中国(buddha—but—佛),也就是在汉末三国时期了。
对此,不知道各位有何看法?我觉得季先生的这些考证和分析还是比较充分,对于我们增长佛学历史方面的知识还是多少有些帮助的。不盲目排斥,多听人家之言,才是做学问的基本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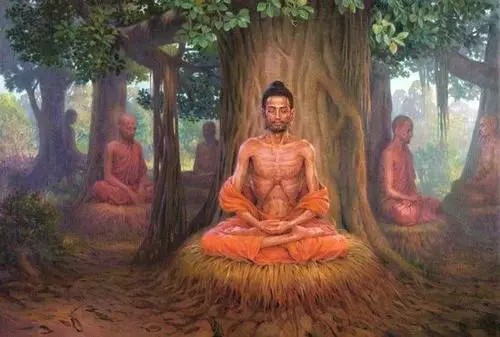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