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经典:
——评裴云龙《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研究:
南宋金元时期(1127-1279)》
文/翁源 刘成国

一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领域,对于唐宋八大家,尤其是北宋六家的关注,自明清以来数百年间不曾中辍,所得成果可谓汗牛充栋。[1]于此等成果丰硕之地再寻收获,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幸而新方法的引入为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途,自“文学经典”与“经典化”理论传入,国内诸多学者对推进这一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从个案分析到理论总结,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但目前应用“经典化”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问题的成果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研究的体系性尚不完善,且“与文学经典研究相关的理论与经验方法,一直未能完整、系统地应用于唐宋八大家散文这一重要的文学史领域。”(裴书页39-40)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裴云龙博士借助“经典化”理论的他山之石,将北宋六家散文的经典化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课题进行系统研究,《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研究:南宋金元时期(1127-1279)》即是这一开拓所得的硕果。 该书对唐宋古文经典体系的建构意义和生成机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堪称近三十年来以新视角审视北宋六家的最具系统性的成果。
是书作为郭英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于2020年出版。全书分四章,前有绪论,后附结语。除第一章外,其余各章节均已发表于《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总体上由点及面,从对北宋六家细致深入的个案探索,最终扩展到整个经典系统的建构意义与生成机制,各部分有机组合,描绘出北宋六家在散文史上各具特色又殊途同归的经典铸就历程。
新理念、新视角的引入容易产生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但如何驾驭西方舶来品为本土研究服务实是考验学者功力的肯綮。 裴书采取了回归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的方式,探寻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点及理论应用的可能性,有效调和了西方理论与本土文学研究。“经典”的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五经”“四书”体系逐步确立的过程,为“经典化”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案例。然而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与经书并不能够机械等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虽适用于经书所展现出的中国古籍走向经典的一般规律,但也存在更多具体且特殊的问题,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指涉的范围更加广泛、驳杂,传播经典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页7),且相比于一些经学著作明确被冠以“经典”之称,“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似乎只能做一种模糊的定性”(页8)。经过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散文典籍的初步回顾与审视,裴书首先定义了经典散文得以称为经典的特征:首先,“在历代文章选本和散文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次,除文学层面外,“在政治、思想、历史等多个文化纬度中都具有丰富的典范意义”;再次,能夠“为相应类别的散文写作树立范式”。(页10-11)以上三个方面兼顾作品外在经典地位的表现与文学内部丰富意涵和后世影响的经典性质的体现,以此为准绳筛选作品,能够脱颖而出者当为足以令人信服的经典之作。其次,通过考察儒家文学经典观念在南宋之前的演进,裴书从《论语》中拈出衡量文学价值的四重维度:知识、文化、情感、表达,总结了自汉至宋的文学经典观对四重维度的抑扬,尤其强调了两宋古文家与道学家在文化纬度上的分歧: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家的经典观,否定了经典文学能够“将今人引领至圣贤精神世界”(页85)的媒介作用,而文学的这一体现儒家最高价值观念的中介功能正是古文家标榜经典的重要因素。由此,裴书深入典籍,准确把握了“经典化”理论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契合点,使理论适应于实际研究,更贴合地为我所用。

在确定衡量经典的标准与分析纬度后,裴书分两章细致勾画了北宋六家古文的经典化历程,最后于末章对这一经典系统的建构意义和生成机制进行了总结。裴书认为欧阳修散文的经典化经历了“多维解读”,12世纪是解读转向的节点。随着理学对心性的讨论日盛,欧阳修散文中对心性论的回避成为理学家攻击否定的焦点,其经典的意义从“传承儒学道统精神的载体”(页111),一定程度上转向文化纬度之外的方面,而在理学语境下,“知识精英对欧阳修散文中所涉文法、知识的成分做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解读与剖析,也使其经典性得以产生的纬度得到明显扩展”(页134)。曾巩散文的经典化,裴书强调了朱熹的重要作用,将理学家对曾巩散文经典性的解读,归纳为表达纬度的“词严”与文化纬度的“理正”。“在否定语境影响下的经典化进呈中步入了文学经典的序列”(页173)是裴书对王安石成为散文经典代表作者之一的描述,裴书展现了南宋学者对王安石的激烈否定,同时挖掘了王安石散文中与理学思想契合的因素,但并未能圆融地解释这两种相反的因素如何促成了王安石最终能够跻身北宋六家,成为典范。对三苏经典化路径的解析,裴书聚焦了苏轼一家,另外讨论了“三苏”并称与苏学接受的问题。裴书特别指出苏辙在“三苏”经典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认为苏辙的散文反映了“‘苏学’与理学的折中”,且“将‘三苏’史论的学术成就提升至新的高度”(页218)。
最后一章裴书首先广泛地考察了南宋金元时期的文学选本和史论描述,较为全面完整地勾勒出经典系统的形成理路,客观反映了以欧阳修为主的“欧学”与以苏轼为主的“苏学”在此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另外,通过考察经典化推动者的文化身份,裴书又引入知识场域的理论,对北宋六家这一经典系统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深入解读。裴书将北宋六家经典的塑造,归因于“‘浙学’场域的学术追求与社会干预”(页263)和“朱熹后学对理学知识场的融合”(页275),最终得出结论“12—13世纪的理学精英在实践其儒学理念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将北宋六家散文建构为具有学术意义的经典系统”(页288)。
二
裴书充分挖掘了理学盛行时期六家散文在不同层面与当时士大夫追求的契合点,梳理出六家散文各具特色的经典化历程。裴书承认南宋时期的道学家“对古文家所接续的传统文学经典观起到了冲击、制约的否定性作用”(页102),但又将拥有理学身份的士大夫作为推动六家散文经典化的重要力量,如此似乎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裴书对这一矛盾进行了解释,如对欧阳修散文经典化的讨论,裴书指出南宋时期虽然欧阳修散文在心性论上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但其在知识纬度的丰富意涵正适合作为深入解析、理性探索的研究对象,而这一研究视角恰好切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既往学术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炼、反思的治学路径”(页131),因而在文化纬度承受强烈批判的欧阳修散文,于知识纬度和表达维度的典范性却得以强化,从而持续占领经典地位。再如裴书引入知识场域理论分析北宋六家散文经典系统的生成,从接受者的角度考察北宋六家散文的经典性,认为“浙籍学者对儒学经世性和史学的重视,契合了以欧、苏为代表的早期宋学的学术追求,形成了他们推动建立北宋散文经典体系的基础因素”(页275)。
以上探索有效结合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在追寻北宋六家经典化过程的同时,兼顾挖掘六家散文在知识、文化、情感、表达四重维度上的价值,探索文本价值与接受者之间的契合,从而合理地解释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但裴书对于推动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主力者身份的分析,似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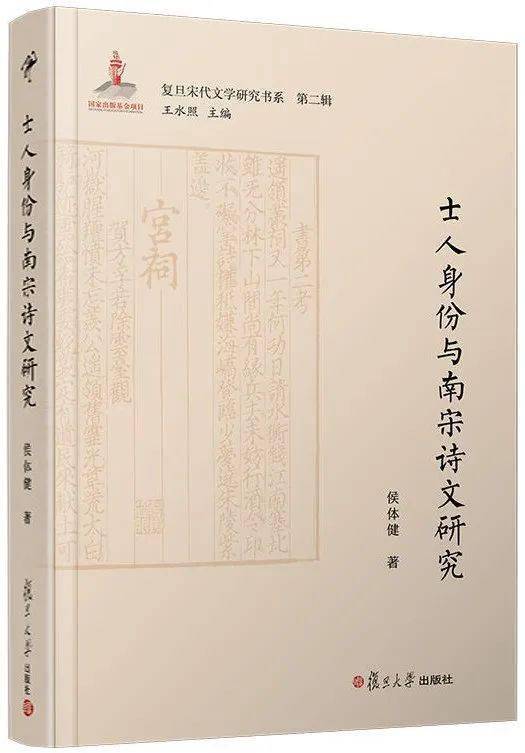
侯体健在《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中指出:“到了南宋,三位一体式的士大夫身份被逐渐解构,三种身份中的某一种,在南宋士人身上常被凸显出来。”[3]诚然,南宋绝大部分士大夫都受到理学的影响,但其对古文的批评是否出于理学家的身份值得怀疑。换言之,在古文批评中,南宋士人身上所凸显出的是何种身份值得更细致的探究。如南宋士人对欧阳修的评价。裴书在“基于儒学思想纬度的争议与调和”条中列举了杨时对欧阳修散文的否定,以及周必大、杨万里、陈亮、徐谊、王若虚等人对欧阳散文的辩护。(页111-119)尽管裴书特别强调了徐谊身为陆九渊弟子的理学家身份,但在总结时还是承认为欧阳修散文辩护的群体为“古文家思想的传承者”,并将这一群体与“尊奉程颐、杨时思想的理学家”(页115)相对立,可见在考察中,裴书并不坚持经典推动者的理学家身份。
具体考察陈亮对欧阳修散文的推动,可以发现陈亮标举欧阳修的散文更多出于官员身份对转变文风的呼唤,而非以理学学者自居。首先,陈亮对欧阳修散文的推举最根本在于对科举的不满,《书欧阳文粹后》陈亮坚定地叙述了变革科举文风的决心:
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始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是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4]
以上可见,陈亮对欧阳修散文的推举绝少含有理学的成分,首先选文缘起在于“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选文目的是为科考举子提供模仿的范本,以转变文风;其次以“通于时文者”为标准选文,学术追求并不明确纳入选文标准;最后选文的最高追求是追望“先王之法度”,有从变革文风上升至匡正政治的倾向,此点在陈亮《变文法》的策论中表现的更加明显[5]。由此裴书所引陈亮对欧阳修散文“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的评价,(页114)根本上不出于其理学学者的身份,更多是一位官员为变革文风的疾呼。
再考朱熹对于欧阳修散文的评价,裴书节引了《读唐志》和《白鹿书堂策问》两条材料,从而得出结论“在理学的视域中,朱熹有限度地承认了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维度的典范价值,在肯定的同时也坚持了批判的视角”。(页116)但笔者以为《读唐志》及《白鹿书堂策问》恰是证明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欧阳修散文在思想维度上的否定,《读唐志》开篇,朱熹即明确批判了欧阳修的文道观:
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岀于二也。[6]
“理一分殊”是朱熹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从“理一”的角度出发,朱熹批判了欧阳修将道德与文章分离的观念,主张“实于中”而“文于外”,文是修养达到一定境界后自然流出的产物。而《白鹿书堂策问》是朱熹以教师身份出给学生的考题,其意在引导学生思考,自然不会直白说明态度,但将上承欧阳修学术的王安石、苏轼与程颐对立,其中非议欧阳修学术的态度不言自明。另考朱熹《答吕伯恭》:
《文海》条例甚当,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种文胜而义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须如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子固《仙都观》《菜园记》之属乃可入,其他赞邪害正者,文词虽工,恐皆不可取也。盖此书一成,便为永远传布,司去取之权者,其所担当,亦不减《纲目》,非细事也。[7]
此段文字可见,朱熹极力抵制“文胜而义理乖僻者”,而对“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态度较为温和。由此,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具有强烈的卫道精神,对乖违义理的因素采取坚决地抵制,而对于文学方面,其作为文人的身份保持了对“虚文”的欣赏,在没有学术对立的前提下,给文学保留了生长空间。
综上分析,虽然推动北宋六家经典化的士人都兼具理学身份,但其对于文学方面的推动是否出于理学的背景值得更细致地探讨。
三
裴书将北宋六家散文作为整体研究,展示了六家作为个体以至整体在南宋一朝风云诡谲、五彩缤纷的经典化历程,令人读之酣畅,受益匪浅。但出于整体的考量和断代研究的限制,对推动具体作家经典化主力的判断疑有不准确之处。如裴书似过分强调了理学家对王安石散文经典化的推动作用,对王安石被标举为经典的时代语焉不详。
首先讨论理学家在王安石散文经典化历程中的影响。裴书认为虽然王学在南宋遭到非议,“但以朱熹、陆九渊、黄震、吴澄为代表的重要理学家却以多种角度、多种方式认可王安石文章与学术对于社会的正面影响和典范意义,并对王安石散文的经典价值有所褒扬”(页163)。依笔者之见,以上所举诸家对王安石的评价确非完全贬斥,但其同情和赞扬绝不出于理学的立场,相反,站在理学角度,以上诸家更多起到“反经典”的作用。裴书举朱熹《答汪尚书》以证朱熹对王安石的批判不及苏轼,而细检文本此结论实难以成立。《答汪尚书》一文是针对“蒙教喻以两苏之学不可与王氏同科”,及“以欧阳、司马同于苏氏”两个观点而发的议论,[8]朱熹鉴于世人“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9],故特以苏学为对象,对其进行抨击。抛开这一前提,朱熹对于苏学和王学的评价并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如十一月既望的《答汪尚书》:
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10]
朱熹认为苏学与王学均是偏离大道的邪说,苏学未遭到强烈反对不过是由于其学术没有经过实践,无以显示其祸害而已。

再看黄震对王安石的评价,裴书举《黄氏日抄·读文集》中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并举,而先于苏洵、苏辙,证明黄震对王安石的肯定。而细检《黄氏日抄·读文集》,作为学者的黄震对王安石的非议不在少数:
昔贾谊尝言《治安》于汉文之世矣,事理精确,议论伟然,文帝尚不为之动,况乎我仁祖重厚之德又过文帝,而荆公陋弱之论远惭贾生。薄而弃之,正不待食钓饵,而后知其诈也。奈何公清苦之行,该博之学,纳交韩吕,徉退求进,言不用而名益显。及神宗以锐意斯世之心而卒听之,公遂得以鄙夷当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朝廷竟以征诛为威,公亦卒为排逐而不变,悉如前日所言,悲夫。[11]
《进字说札子》《改三经义误字札子》皆无义理,公自沉溺罔觉耳。[12]
甚矣,公之好异论、疾正人,而不顾经训也。[13]
以上作为学者的黄震对王安石文中的议论多有非议,以“陋弱”形容其议论,贬斥其沽名钓誉,批判其解经议论“不顾经训”、“好异论、疾正人”、“无义理”,皆是对王安石本人及王学露骨的斥责,直接了当,不留情面。
裴书又举吴澄在《王友山诗序》中对王安石古文成就的高度赞扬,证明理学家对王安石的肯定。而观其全篇,此序标举出王氏一门的文学英才,称王氏家族“英哲萃于一门,出于一时”[14],意在借此称赞王友山诗上承先辈遗风,表里如一,不同于当时文风。由此,其对王安石的评价实有出于为褒扬王友山而刻意抬高的嫌疑。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吴澄除褒扬王安石散文外,也叙述了王安石文集的坎坷身世:
公绝类之英,间气所生。同时文人虽或意见素异,尚且推尊公文,口许心服,每极其至;而后来卑陋之士不满其相业,因并废其文,此公生平所谓流俗,胡于公之死后而犹然也?[15]
于吴澄看来,王安石文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值得称赞,但世人对其施政的不满,使得其文才惨遭湮没,对王安石文集于世不存的情况表示了同情。但此种同情显然出于文人身份的共情,非来源于其理学的背景。
以上足以反驳裴书所论理学家对王安石的认可。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在理学立场对王学采取的是绝对否定的态度,黄震在学理层面对王安石多尖锐的批判,吴澄站在文人的角度肯定了王安石在古文方面的成就,未曾涉及理学层面的评价。
其次讨论王安石散文被标举为经典的时间。据裴书统计,王安石散文在南宋选本中的地位并不凸显,且前已论述王安石散文在南宋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因而根据裴书的考察,很难说明王安石散文在南宋金元时期已经取得经典地位。天津师范大学李楠的博士论文《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研究》在更长远的历史视野中审视王安石文章的经典化进呈,指出了宋元时期熙宁变法对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的影响,将明代定为王安石文章经典地位的确立期。[16]笔者赞同此说。政治是影响王安石散文经典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拜相掌权,荆公新学曾一时主掌文坛,但亦是由于变法的失败,导致王学受到猛烈抨击,如前引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所言,时人多因厌恶王安石的政治作为同时贬抑其文章。而政治因素在经历改朝换代之后影响自然减弱,先前热烈的讨论恰为王安石散文赢得了高度关注,在脱离政治偏见后,其文章的积极意义得以重新光耀于世。如此似可以更切合地解释宋元时期处于否定语境中的王安石散文何以在明代得以跻身八大家散文的行列,成为经典。
最后,略谈经典化研究与接受史研究的区别问题。裴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为:
“经典化”研究的确应该在接受史的基础上展开,对标举经典、传播经典等因素的研究都属于接受史的范畴。然而,“经典化”的核心应是对文学作品经典属性的理解与定位,这一方面需要理解经典作品独特的个性品质,另一方面需要在后代的接受史材料中找到与作品经典性特质彼此契合或转移、偏转的因素。(页21)
以此看来“经典化研究”与“接受史研究”是两种自成体系,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研究方式,“经典化研究”不同于“接受史研究”的显著标志是“对文学作品经典属性的理解与定位”。笔者认为“经典属性”当指作品成为经典之后所具有的特性,对于非经典的作品而言,纵然有可取之处,似难称为具有“经典属性”。
裴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为“否定语境下的王安石散文接受”(页152),在成书以前,本节曾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题为“在否定语境中走向经典——王安石散文经典化历程及文化内涵(1127——1279)”[17],从“经典化历程”到“接受”的修正是否意味着裴书对王安石散文未能取得经典地位的默认?若同前所述,认定王安石散文经典地位的取得在明代,那么南宋金元时期王安石散文尚未取得经典地位,是否具有“经典属性”?如此,讨论南宋金元时期王安石散文经典化的问题是否能够成立?裴书选取1127——1279年作为研究的断限,原因之一是“南宋金元是理学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页17)。而前已述及,对于北宋六家的标举,南宋士人似不出于其理学背景,虽然理学与古文存在深层次的契合,但理学对于文章的发展更多起到阻碍的作用,因而关于研究时间断限的选择是否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拓展?
以上吹毛求疵的指摘于全书不胜枚举的创建新解而言充其量仅是白璧微瑕,无碍于本书突出的学术价值。裴云龙博士于宋元时期相关文献全面网罗,利用开阔视野和扎实的文献分析,细致梳理了北宋六家经典化历程,对推进唐宋散文研究贡献卓著,此作当堪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领域的优秀之作。
向上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1]如王水照《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浅论之一》关注到南宋散文对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代表作品的模拟、借鉴;许总《论理学与唐宋古文主流体系建构》、束有春的专著《理学古文史》等对理学思想在北宋六家散文接受史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描述或定位。
[2]个案研究有吴承学《: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刘成国《文以明道:韩愈的经典化历程》,倪春军《古今学记第一——试论李觏的经典化过程》等;理论总结有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等单篇文章的讨论,以及詹福瑞的著作《论经典》。
[3]侯体健:《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4]陈亮:《书欧阳文粹后》,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196页。
[5]陈亮在《变文法》中陈述:“纷纷之论既兴,则一人之力决不能以胜众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也。”(《陈亮集》第128页)明显意在以变文使异说咸汇于一,有辅助思想一统的倾向。
[7]朱熹:《答吕伯恭》,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4,《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76页。
[8]朱熹:《答汪尚书(七月十七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0,《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00页。
[9]同前,第1301页。
[10]朱熹:《答汪尚书(十一月既望)》,《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0,《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03-1304页。
[11]黄震:《黄氏日抄》卷64《读文集六·王荆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08册,第572页。
[12]黄震:《黄氏日抄》卷64《读文集六·王荆公》,第573页。
[13]黄震:《黄氏日抄》卷64《读文集六·王荆公》,第574页。
[14]吴澄:《王友山诗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48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册,第384页。
[15]吴澄:《王友山诗序》,《全元文》卷485,第351页。
[16]参见李楠《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研究》第二章、第三章。李楠:《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7年,
[17]裴云龙,韩婷婷:《在否定语境中走向经典——王安石散文经典化历程及文化内涵(1127——1279)》,《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 全 文 完 -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