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因为是上古,世界真的还很年轻,人在日月星辰之下,直立于大地之上,面对每一个日新又新的时日,做自己该做的事,后世的愁肠百结仿佛还不曾降临,很多唱出来的歌谣,都有着健朗开阔的气息。有时候,是《卿云歌》这样的坦然铺陈:“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有时候,是《击壤歌》这样的太平无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有时候,又是《伊耆氏蜡辞》这样的虔心祝祷:“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世间的一切都那样切身,自然生生不息的不仁还没有被指为敌意,辛劳的耕作也没什么值得抱怨的,人便也成了天地所生的草木,当春而发,经冬则凋,随四时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无心以枯荣。
不管是集日月光华于一人的政治人物,还是随着日升日落作息的农人,亦或是祝祷风调雨顺的祭祀者,虽然各有不同的方式,都无一例外地与劳作和时日有关——如同荷马史诗中的劳作是争战而赫西俄德的劳作是耕种。吴雅凌《劳作与时日笺释》写道:“从某种程度而言,学习自然神启的智识,就是学习认识时序女神,因为,她们‘时时关注有死的人类的劳作’,在人类城邦中起着再重要不过的影响。”或许可以由此推断,上面诗行里的健朗和开阔,并非只因为民风淳朴,而是里面有扎扎实实的劳作。那些始终缠在手上的事,无论是政务、祭祀还是耕种,踏踏实实调适了每个人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每天每夜的光阴,即便怎样艰难吧,对做事的人来说,可能并非灾难,而是安慰,就像《劳作与时日》里的诗句:“不论时运如何,劳作比较好。”
除了劳作与时日,开头的引文里还或明或暗地有着圣王或天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神)的身影。据说,《击壤歌》是“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上面没有全引的《卿云歌》,则是“舜将禅禹,于时俊乂(按才德出众的人)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伊耆氏蜡辞》出现的前因,是“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即求索众神而尽祭之。为什么“不识不知”之后,非要有个“顺帝之则”,无神无王的自在不好吗?神和王是一个安稳的人世必需的吗?
《老子》通行本第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经典系统解“域中四大”,各有侧重——王弼致思于玄理:“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言道则有所由,有所由然后谓之为道,然则是道,称中之大也,不若无称之大也。无称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无称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河上公似乎更强调修身之一面:“(解前句‘远曰反’谓:言其远不越绝,乃复反在人身也。)道大者,包罗天地,无所不容也。天大者,无所不盖也。地大者,无所不载也。王大者,无所不制也。”李约则将修持与治国结合:“道者,清净自然之道也。德者,以法久而失,修而得之谓之德也。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谓域中四大焉。盖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
四大之中,道和天地都有极高的概念级别,怎么推举都不会有人起疑。最难解的,其实是“王”,怎么就跟道、天、地放在一起了?这疑问不是现代才有,历来的解说多致力于此,大概正说明了人们早已心生疑窦。有人认为,王应该跟道和天地一样,胸怀阔大,善于容纳人的缺失,“能包裹之也”;有人则理解成权力的当然,“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有人确信这是王者的尊贵,以其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还有人解为王居天地之间,可以从中燮理。徐梵澄《老子臆解》,大概是感受到三权分立的时代气息,因而独出新意,认为对王尊重的同时有所限制:“‘国中有四大’(按帛书本“域”作“国”),‘道’为首而‘王’居末。盖先秦诸子,必有所秉以凌驾统治权威者。虽孟子亦以晋、楚之富为言,以‘天爵’与‘人爵’抗衡。他如阴阳五行灾异之说,皆所以怵人主者也。老子于此说‘王’之大,尊之矣,然而末之也。”
这些解说,让我们不得不考虑,老子将王作为“域中四大”之一,是不是暗示着一种人类的基本境况?或者更广泛地说,人无法脱离共同体而生活,政治是属人的必然命运?《人间世》里,庄子借孔子之口讲,“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的说法是,“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进一步推论,“域中四大”中的道、天、地、王,是不是概述了人类生活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把人必须效法的天,不得不依赖的地(隐含着与天地密切相关的神),需要认知的世界运行方式,以及无往而不在的君王,用极简的方式提示了出来。这真是非凡的洞察力,非大哲人不办,怪不得徐梵澄说,“其思想组织之精严若此,此老子之所以可贵也”。
当然,以上所论,只是与人相关的一个事实,远远不是全部,否则,对自己文字“损之又损”的老子也不用写五千言了对吧?即使把讨论局限在“域中四大”,仍然题有剩义。比如,《劳作与时日》开始讲神话的时候,起首就是“神们藏起了人类的生计”:“这里的神话叙事起始于掩藏真相,呼应《神谱》中的说法。普罗米修斯反宙斯,一系列计谋的秘诀就在掩藏。”这是不是说明,人除了对神至诚的祈祷,隐秘的反抗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王,作为民的人,是不是也需要有掩藏的举动?这问题涉及太广,暂且按下不表,我想说的重点是,前面的歌诗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好像要说的都已经说了,可仔细琢磨起来,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隐藏在文字里面,我们还没有触及。这个隐藏起来的东西,会是什么呢?这疑问在心里存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翻看《尚书大传》,读到了《卿云歌》可能更早的前因——
维十有四祀,钟石笙管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见于钟石。
“维十有四祀”即舜在位第十四年,这就让人意识到,文中的乐声之变,天气之感,舜帝的点头笑语,都隐藏着一个记录者。上面所举那些如日如月的赞美也好,太平无事的坦然也罢,包括虔心的祈祷和郑重的嘱咐,甚至是体道者的传心之言,在著述成为人人可能的事情之前,都需要一个审慎的传言者。这个传言者,起码在上古,并非恭谨如仪地写下帝王的起居注,而是要有与言说者同等甚至高于他们的胸怀和眼光,能够在每个日常里辨认出那些称得上重大的内容,然后用恰当的方式记载下来,把空间里的精华携带进时间。我们今天能有幸领略那些伟大心灵的从容举动,读得到“非一人之天下也”这样气象万千的壮阔之言,端赖于那些聪明睿智的传言者。这个把人世间的卓越镂刻在文字中的记录者群体,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应该就叫做“史”。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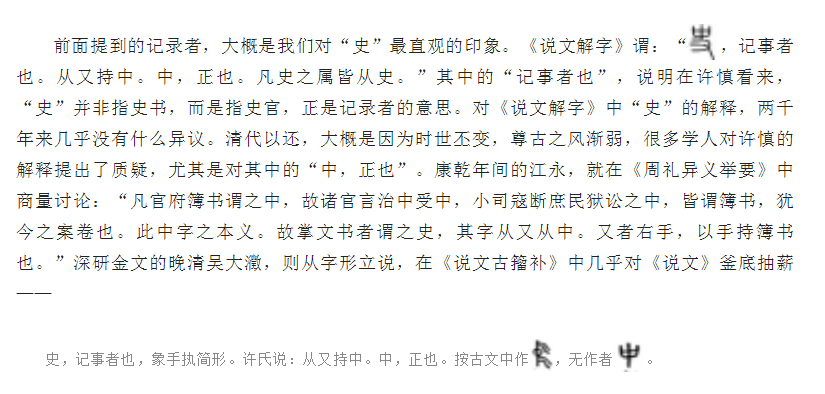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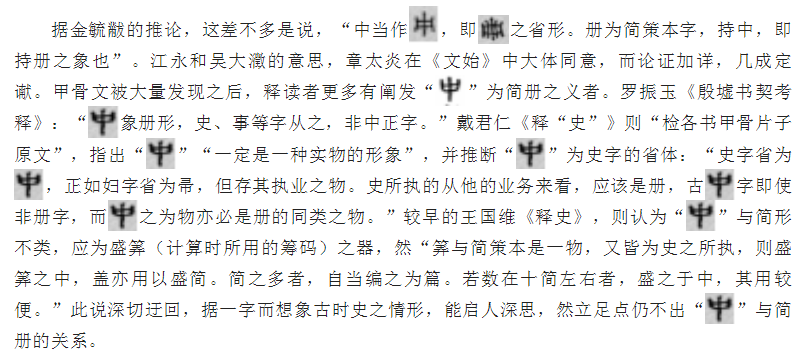
我们心目中的记事者,又有一层记载过去之事的意思,那么,记载当下之事者,是否也可以称为史呢?1940年代,在《中国史学之起源》中,朱希祖反复申明:“记事者,即后世之书记官,此为本谊;历史官之史,乃引申谊。”金毓黻由此而推论之:“现代档案,即为他日之史料,古人于档案外无史,古史即天府所藏之中也。”即便文字未生之前的结绳记事者,也可以在书记官的意义上追称为史官。所谓书记官,金毓黻云,“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即与后世的秘书或书记类似。朱希祖对书记官和历史官的区分,渐渐得到认可。1970年代末,王尔敏《史学方法》断言:“史官掌秘书之职,为近世学者普遍承认,毫无疑义。”
从上面的罗列能够看出,虽然“五经无双”的许慎早已遭到质疑,但因后世对“史”的基本印象,解说仍然与能书写的简册相关,也即与经典确认的属于记录系统的史脱不开干系。再说得确切些,以上诸说始终没有离开史是“记事者也”这一思路。这正是经典的力量。总体来看,虽然有追溯至尧舜甚至更早的部分,传世五经的核心,是有周一代的革命建国与理想政制。这一轴心经典的断代选择,既在思想层面给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精神支持,也把一个共同体的认知圈定在某个颇大的范围之内,提供精神性保护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上的限制。经典其实跟任何事物一样,也难以避免时间的推排消蚀,最终都会陈旧破败,被无常席卷而去,只是因为其生命周期太长,往往会被我们忽视。这个无常席卷的过程一直不曾停顿,并且会在某个时候出现临界点——比如五经之于清末,呈现雪崩式的坍塌。临界点上的群体,就不得不迎面遭遇一个天经地义的精神世界倒塌的过程,有些人会因此崩溃而颓丧沉沦,极端者甚至要以身殉之;有些人则对经典重赋意义,以期恢复其饱满的活力;更有一部分人会振衣而起,根据变化的时代状况,试着重建新的经典系统。
这个崩溃和重建的过程,传统经典系统的圈定范围桶底脱落,精心述作过的有周一代文化不再是唯一选择,原先被经典封存的能量持续涌出,此前不够雅驯的文化就此有了新的意义。对“史”字的解释,便也逐渐离开了此前的“记事者也”范围,向具体事务和神明祭祀两个方向扩展。1960年代,屈万里在审阅一篇文章时表示:“史字上半所从之□(按,‘之’后有一空格,疑有脱字,似应为‘图片’上之‘图片’),绝非简册之形。因册字习见于甲骨文及金文,绝无作图片者(甲骨文往往以‘史’为‘事’)。”1980年代初,胡淀咸的《释史》一文,考察多种甲骨和金文,确立了史与事之间的关系:“‘史’和‘事’,原就是一个字。所谓史官实是任事之官,史、御史、大史、卿史都是由它所执掌的事务而得名的。”从这个方向看,史与事的贯通,正是高层文化跟具体事务的沟通——或许在起始的时候,史官就并非一直高居庙堂,秉持着抽象的中正之德,目光如炬,执简运笔——那些经典系统中致力于精神层面的人,在更深的意义上,一直就没有脱离基础性的劳作与时日。
不止庶事,仔细推敲起来,恐怕连神明祭祀之事,也无法离开具体的劳作。劳榦大概就是发现了其间的关联,在《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中,他便认定史的起源与弓钻有关:“在史字中其所从的图片就是一个弓背向下的弓形,金文及甲骨凡从弓的字,弓都是对侧面的,这都是射箭的弓,只有这个弓形的弓背向下,对于弓钻的形状,正皆符合。”手持弓钻的史,主要是钻燧改火和攻治龟甲。钻燧不消说需要弓钻,攻治龟甲其实也在所难免:“龟甲是比较坚硬的,为求得卜兆先要在预备灼火之处,把它刮薄,因为硬难以刮薄,因此便先钻,然后在钻处再用凿扩大。”如此手上有具体之事的史,当然不会跟抽象的中正无关。王国维《释史》云,“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李宗侗《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承接此义,分析鞭辟入里:“中正是表示无形的物件;而最初的人所表示的物品多半是有形的。所以不可能以手持无形的物,这是不合于古人的思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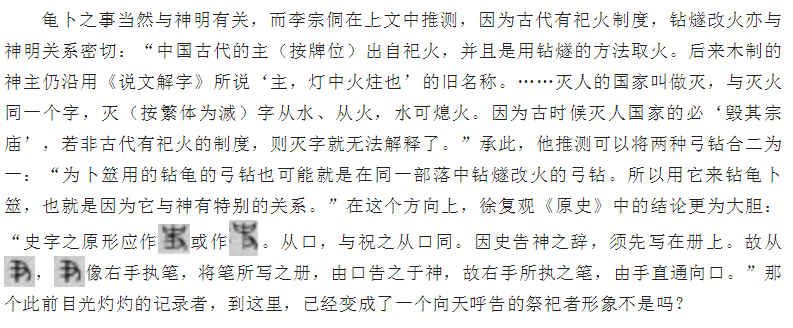
(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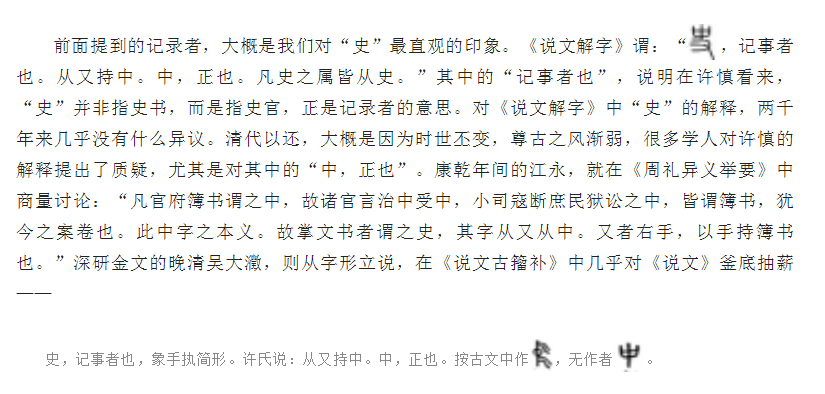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