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与《贵州文史丛刊》相遇是在2006年读贵州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在张启成老师的《诗经》课堂上。张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丛刊》是贵州省文史馆主办的具有学术性、知识性与资料性的文史类学术期刊。张老师告诉我们,为了鼓励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他会将我们的《诗经》学课程写得好的论文推荐到《丛刊》发表,并向我们展示了往届在《丛刊》上发表的学长的优秀论文。
那时候,《丛刊》成了我们心里向往的理想。张老师温和而有力量的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就那样一天天的留在我们逸夫楼201的教室里,长久的回荡在我们的心里。他给我们讲述他在1960年夏天毕业于复旦大学之时的学术理想,讲述他在毕业后离开故土成为“在黔沪客”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
在张老师的课堂上,他给我们讲授《与的比较》《明代学的新气象》《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论两汉非经学研究的萌芽》《试论的情歌》。其中,很多论文和观点他都已经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复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文史哲》《学术月刊》《贵州文史丛刊》等刊物上。
在他的课堂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国《诗经》研究、海外《诗经》研究的脉络与视域,感受到学术研究的真理与方法,感受到学术研究是通向人们内心“宁静和安定”的必然之路。秋冬时节的阳光时常透过窗子洒在他的身上,慈爱的老师,和煦的阳光,和乐的教室,成了我心里永恒的景致,成了我心里长久的思念,成了我心里永远怀藏的温暖和光明。
那时候,张老师同时还任贵州文史馆副馆长、《贵州文史丛刊》主编。他鼓励研究生进行学术论文的写作,鼓励我们向《丛刊》投稿。能在《丛刊》上发表论文成了我们最初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动力,那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还记得我们同学都努力写作反复修改论文,都希望自己的论文能够成为老师推荐的那篇稿子。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不才的我获得老师的垂爱,他宣布把我写的《试评姚际恒》推荐到《丛刊》发表。之后,张老师细致地向我讲解论文的修改内容、格式、注释以及作者单位、邮编的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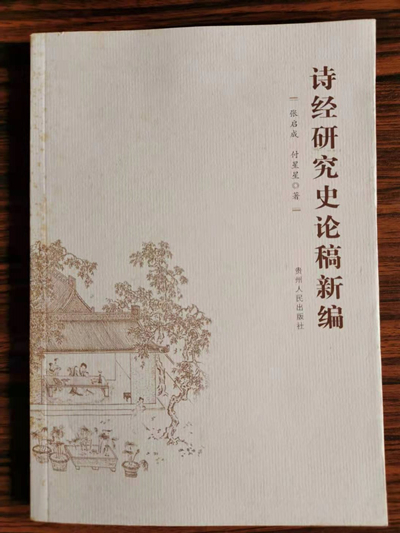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评姚际恒》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3期。看着自己的论文第一次在省级学术刊物发表,第一次印为铅字,我特别的感动。还记得张老师的话,他告诉我:“有了第一篇,就会有第二篇,第三篇了。”事后回想,在当时只是作为研究生的我,老师对我是充满了多么大的希望和信心。虽然老师现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由他帮助我开启的学术研究的理想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2009年,我考上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跟随张伯伟老师作域外《诗经》学研究。在南大的日子,我时常会收到张启成老师寄给我的关于日韩《诗经》学的文献资料,每每在宿舍阿姨那里接到写着“南京大学 南园2舍 付星星女士收”的信,看着他在眼睛几乎失明的状态下用一笔书法给我写的信封和信笺,我都会感动得泪眼模糊,我会想到在贵大校园里他在徐师母的搀扶下在校园邮局给我寄信的场景。
张老师给予了我一份长久的、浓烈的学术期待。他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在学术研究中有自己的发现,有自己的坚守。就是在读博期间,张老师仍继续鼓励我向《丛刊》投稿。随后,拙文《诗学成就简论》就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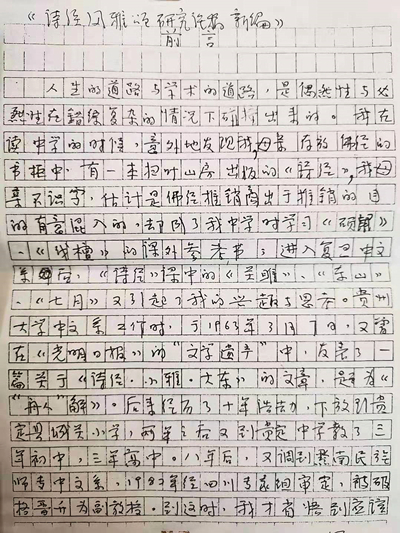
2012年,我回到母校贵州大学工作。2014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朝鲜半岛《诗经》学史研究”。在撰写国家课题期间,我在《丛刊》上发表了《海东儒者朴文镐学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4期)、《朝鲜时代儒者朴世堂学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1期)。也正是在张老师和《丛刊》的鼓励下,我2017年又在权威期刊《文学遗产》发表《汉文化圈视野下的朝鲜半岛学研究》一文。
回想从在《丛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始,我目前发表了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在《丛刊》发表论文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文章出来我特别愿意去文史馆领取刊物,因为可以看到于菲老师、王尧礼老师、何萍老师等老师们。他们浸润在文史中的气息,让我感受到《丛刊》包容阔大的学术气象。他们由文史研究所散发出来的温婉雅致,让我感受到《丛刊》刊物背后充满人文精神的温暖。
我与学术研究的结缘,是从在《丛刊》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的。我最初学术研究的动力与信心,也是《丛刊》给予的。我与《丛刊》的故事,是从跟随张老师学习并得到老师提携开始的。《丛刊》让我始终感受到张老师和文史馆老师们对后学的爱护和鼓励。《丛刊》也是张启成老师曾经主编和耕耘的园地,她见证着老辈学人对青年学者的培育、爱护和滋养。《丛刊》既是嘉惠学林的重要刊物,也是薪火相传的美好传承。
虽然“斯人已乘黄鹤去”,《丛刊》却印记着我对张启成老师永久的思念。正如《小雅·隰桑》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作者简介
付星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代表作《汉文化圈视野下的朝鲜半岛学研究》(《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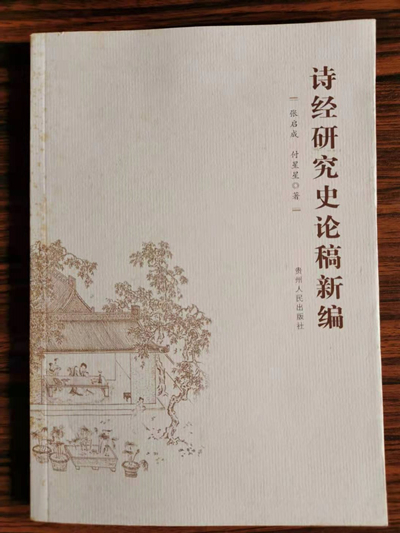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