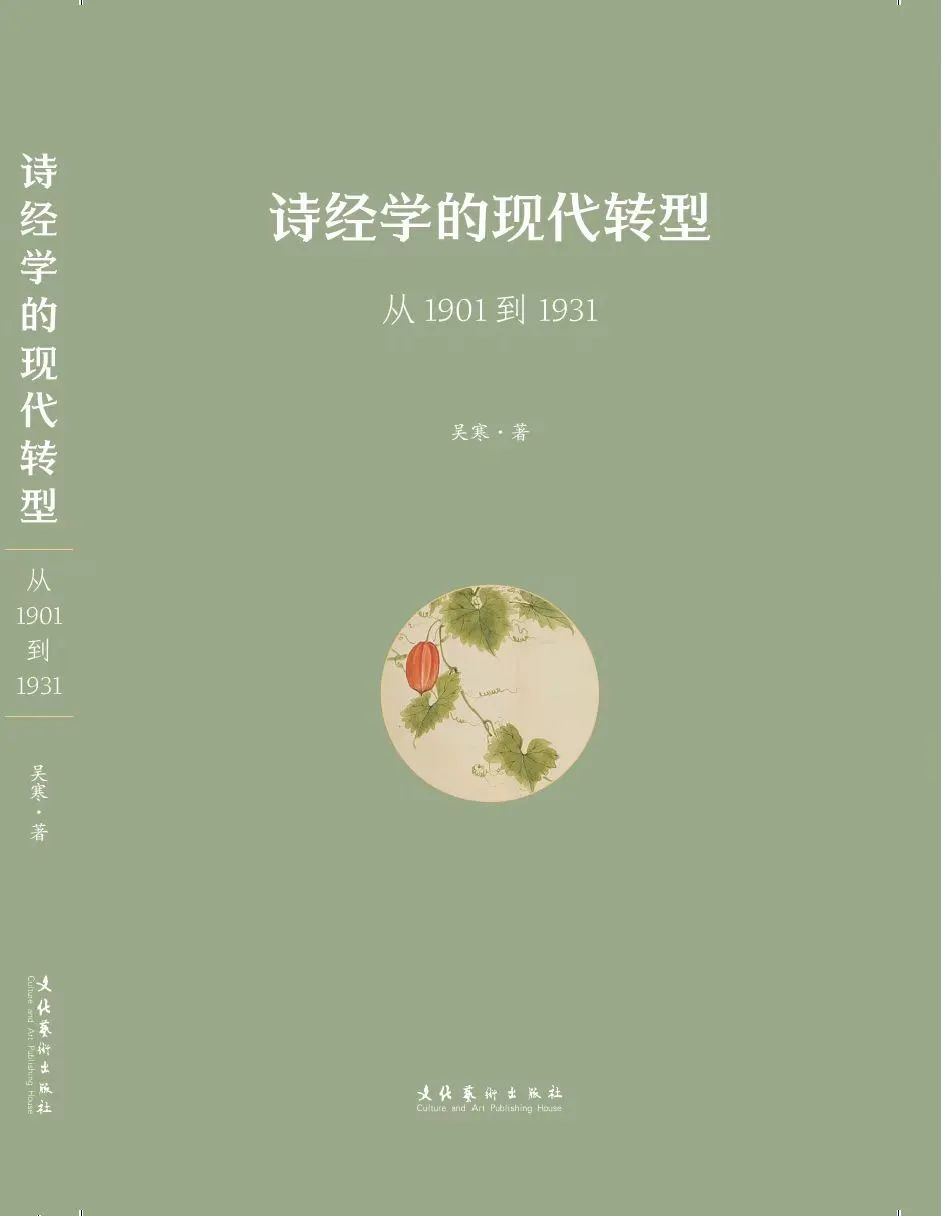
《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
吴寒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ISBN:9787503974120
内
容
简
介
”
本书以晚清民初的诗经学为对象,从“破”和“立”两个方面分析《诗经》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型如何发生、发展,如何经过教育制度变迁、文学学科建立确立出“新典范”,进而探讨这个“新典范”的性质、思路、预设、方法、规范和理论框架。
作
者
简
介
”

吴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古代文学及文献、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经典图像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美术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
目
录
”
前言
第一章 道德的重塑:从正夫妇到保国家
第一节 传统教化体系与《诗经》
第二节 晚清学制变迁中的《诗经》
第三节 经训/伦理教科书中的《诗经》
第四节 “家事”与“王事”的冲突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打下“经字招牌”:整理国故与解构《诗经》经典地位
第一节 经典史料化: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史料”
一、章学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二、章太炎:“六经都是古史
三、整理国故:“六经皆史料”
第二节 斩除藤蔓:从《诗经》回到“诗三百”
一、否认孔子删诗:斩断《诗经》与圣人的关联
二、废《毛诗序》:瓦解早期阐释体系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诗》学理论与“文学”建构:从古典诗学到现代文学观念
第一节 从“文”到“诗”:以诗学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
一、“诗言志”:“文学”的不用之用
二、雅俗互动:从民间取向到民族形式
第二节 “情”的转向:从伦理到个人
一、传统“诗言志”论
二、鲁迅对传统“言志论”的改造
三、“情”和“抒情传统”的重新阐释
第三节 民间取向:大众与精英的本位倒转
一、传统诗教观念:上达政制,下通民众
二、“五四”重释《诗经》之民间取向
三、“民间传统”的挖掘和阐释
第四节 “兴”义走向平面化
一、从“美刺比兴”到“山歌好唱起头难”
二、传统“比兴”论:政治—教化—审美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诗经》阐释与“中国”身份:从天下叙事到民族国家
第一节 以今度古:“中国文学”的系统整合
一、《诗经》与“中国”的地域边界
二、《诗经》与“中国”的时间脉络
第二节 以西律中:“中国文学”的世界定位
二、“史诗—抒情诗—剧诗”的诗体分类
三、他者的眼光:抒情与叙事之二分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 《诗经》研究与“科学方法”:历史考据中的启蒙价值
第一节 《卷耳》论争:历史考据还是审美本位?
一、“假想敌”的变化
二、文学研究会的态度:古典之为“次要”
三、创造社的立场:“青春化”与“原始化”是同一过程
四、《卷耳》论争中的内在张力
第二节 《野有死麕》讨论:“科学方法”与价值坚守
一、《野有死麕》阐释中的启蒙意识
二、俞平伯、周作人的批评:朴学家嫡派
第三节 《静女》讨论:“求真”还是“猜谜”?
一、字里行间求“原义”
二、“科学方法”之迷思
第四节 小结
后记
内
容
简
介
”
《诗经》与早期文体演进脉络
晚清民初的学者普遍相信西方文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是从“韵文”到“散文”,并努力寻求中西文学演进上的一致性。章太炎曾言及:
世言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华先发,次及樱华;桃实先成,次及柿实;故韵文完具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
他认为“征之吾党,秩序亦同”,中国的殷商誓、诰亦为有韵之史,而后又有二《雅》等借歌陈政,春秋以降,散文才逐渐发展起来,中西方的情况可以说是同波异澜,各为派别。
1905年刘师培亦有此论:
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
章、刘二人都谈到,其论出自日本学者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章太炎所言“韵文”“笔语”和刘师培之“韵文”“散文”意思相近,希腊罗马文学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其表现为韵文发达在散文之先。章、刘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相符,说明这是“事物进化之公例”,全人类的文学现象都符合这一基本规律。
章太炎和刘师培的中西对应论述已表现出某些现代因子。不过其持论还比较笼统,亦近于传统的学术观念,如以《尚书》等为早期韵文的表现,对《诗经》只言及二《雅》,也并没有就中西对应现象做更多阐发。而章、刘所引文献又是日本学者转译之西方文学史,在中国并无译介,因此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学者们一方面更大范围地翻译了西方文论和文学史著,另一方面则以新的文学性标准重新确立中国文学的领域,并将《诗经》确立为中国文学的源头,那么,中西文学的对应论述也就需要更清晰、准确的描述。
1923年第14卷第1期《小说月报》刊登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此文介绍了西方诗学、文论、文学原理、文学史著一共五十本,其中莫尔顿《文学之近代研究》和《文学进化论》由傅东华译出,于1926年和1927年分别连载于《小说月报》,这两本书是《小说月报》译介的重要理论著作。莫书从西方基本文体元素出发,试图厘清文学的演进脉络,总结文体进化的基本规律,完成世界文学的统一研究。莫尔顿以谣舞(ballad dance)为最原始的文体质素,其语词、音乐和动作(speech、music、action)三方面因素进一步演化出其他文体,包括诗(poetry)和散文(prose)两大类。具体而言,诗类包括史诗(epic)、抒情诗(lyric)、剧诗(drama)三种文体质素,散文类包括历史(history)、哲学(philosophy)、演说(oratory)三类。莫尔顿的分类与章太炎所引《希腊罗马文学史》一致,此种区分方式在西方文学史论中应该较为普遍。而莫书被译出、连载之后,很快成为中国学者竞相引据的西方理论著作。
1927年,郭绍虞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用莫尔顿文体框架解释中国文体演进。他认为从世界范围内看,风谣是最古的文学,包括音乐、语言、动作三方面因素。而古籍记载说明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一,《左传·襄公十六年》谓“歌诗必类”。第二,《吕氏春秋·古乐》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可以据此推想先民风谣的形态。第三,《诗大序》论诗之起源:“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郭绍虞认为,这三处记载共同说明了早期文学诗歌、音乐、舞蹈一体的形态,因此,风谣作为原始文学形态是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郭绍虞又提出,风谣进一步发展便成为诗。风谣与诗的区别有二,从内容而言,诗比风谣成熟;从表现工具而言,风谣以语言为工具,而诗以文字为工具。
郭绍虞参照莫尔顿理论分析中国文学的演进脉络,此论被收入《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影响很大。“五四”时期从新的文学观念出发,以情感、语体等标准勾勒了中国传统以《诗经》为起源的纯文学叙述脉络。而郭绍虞将这一脉络与西方文学框架进行了印证,这是他的理论贡献。具体包括两方面:首先,中国也以歌乐舞一体的风谣为文学的原始形态,即《诗经》早期不成熟的口头形态。其次,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是韵文早于散文。风谣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口头走向文本就成了诗,《诗经》文本所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学的“韵文时代”。所以《诗经》实际上涵盖了文学史初期从口头到文本的两个阶段。如此一来,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学传统成功地完成了和世界文学的接轨。
郭绍虞之后,许多文学研究者都以《诗经》代表中国文学的“风谣时代”和“韵文时代”。陈钟凡1922年作《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虽然采用莫尔顿框架谈中国文学,但所论完全没有提及《诗经》,到1927年作《中国韵文通论》,却俨然将《诗经》当作中国早期由讴谣到诗歌这一进程的代表:“世界各国文学演进之历程,莫不始于讴谣,进为诗歌,后有散文……古代诗歌之流传至今,足以供人考信者,其惟孔子所手订之三百五篇《诗经》欤?”陈钟凡的转变透露出学界已经接受了中西文学的对照范式。《诗经》在“讴谣—韵文—散文”演进脉络中的定位,逐渐成为文学史的主流意见。
刘麟生说:
世言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华先发,次及樱华;桃实先成,次及柿实;故韵文完具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
胡云翼谈道:
世界各民族文学的诞生,有一条共同的公例,就是韵文的发达总是较早于散文;而诗歌又为韵文中之最先发达者。中国也是如此,最初的文学是诗歌……严格说起来,我们现在可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最古的文学,只有一部《诗经》。
龚群钰也谈道:
世言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华先发,次及樱华;桃实先成,次及柿实;故韵文完具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文学的演进,由讴谣进而为诗歌;由诗歌进而为散文,此东西各国所同也。中国文学,起自歌曲。太古蒙昧之世,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阕。吴越春秋。载古孝子断竹之歌。而尧时有击壤之歌。诗三百篇,亦大抵皆闾里歌谣之什。盖人生而有感觉:有感觉,斯有好恶。或感快,或感不快;快不快感于心,发于口,为语言,为诗歌。诗歌者。中国文学之开山祖也。孔子删诗,得三百五篇,分为风,雅,颂三类。后世文学,即渊源于此。。
直到今天,“诗、乐、舞三位一体”和“原始歌谣发展成《诗经》”等表述,仍然活跃于主流文学史的先秦章节。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论著普遍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在著作中明确提到所论本于莫尔顿,而他们的论述方式及引据文献则大多不出郭绍虞文章的范围。不过我们注意到,从章太炎的“韵文—笔语”到郭绍虞的“诗歌—散文”,学者们采取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翻译。例如莫尔顿所说的歌乐舞一体的原始形式“ballad dance”,翻译就有“谣舞”“讴谣”“风谣”“歌谣”“歌曲”……而“poetry-prose”的二分也有“诗歌—散文”“韵文—散文”等翻译方式,尽管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些翻译可能产生的歧义,尝试对它们进行辨析,但是众口不一,各有指向,其间发生的语意转变值得进一步辨析。
首先是“ballad dance”。莫尔顿是这样说的:“谣舞是韵语和音乐及跳舞拼合而成的。但这里所谓跳舞,意思并不跟近代人所谓跳舞完全一样;这里所谓跳舞,乃是一种摹仿的暗示的动作,如今演说家所用的姿势庶乎近之。文学当最初自然产出的时候,其形式大都将一个题目或一段故事化为韵语,同时以音乐和之,又以动作暗示之。”他所举“ballad dance”的例子,是以色列人在红海得胜的时候,米利暗“手里拿鼓,众女子也拿鼓随从她,跳舞着出来”,又如大卫在耶路撒冷举行开幕典礼,“在主面前极力跳舞”。那么作为希腊罗马原始文学形态的“ballad dance”,不管从词根、解释,还是例证来看,最重要的因素都是跳舞。张世禄也提道:“民歌(ballad)一字,乃从古法文动词(baller)转变而来,即跳舞之意也。”因此,傅东华将其译为“谣舞”应是比较贴合原文语境的理解,表示一种载歌载舞的文艺形态。舞蹈蕴含的身体动作和韵律感,是“ballad dance”的基础性意涵,言辞维度是次之的。
不过,当郭绍虞运用“诗乐舞三位一体”理论解释中国文艺现象时,他将“ballad dance”译为了“风谣”。“风”作为一个早期概念与《诗经》十五国风关系紧密,而“风谣”暗示的是民间广泛传播的歌谣,这无形中把“诗乐舞一体”的“诗”放在了第一位。而“风谣”的定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以文学为主体而以音乐舞蹈为其附庸;以诗歌为最先发生的艺术,而其他都较为后起”。可以说,从“ballad dance”到“风谣”,语词的意义重心已经发生了偏转——言辞跃升为最关键因素,舞蹈代表的身体韵律只是附庸而已。
郭绍虞的认识基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他看来,从“发言”到“永歌”到“手舞足蹈”就代表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从《诗大序》的文本理路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郭绍虞如此强调“诗”在“舞”先。事实上,在《诗大序》讨论的“诗乐舞”中,诗代表的言辞维度占据着毫无疑问的先发位置。当人内心有了情感便会以语言表达,语言不足以表达所以嗟叹,嗟叹不足以表达所以歌咏,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手舞足蹈。“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内心之志到言辞之外发是思虑介入的表达过程,这是诗的生发机制的起点。“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诗是生命情感的运动机制,它生发于外在因素的激荡感动,触发内心的思虑,积累为强大的情感驱动力量,这种表达冲动仅以文辞不足以宣泄,而会难以抑制地走向更贴近本真状态的生命体验,由语言层层递进为咨嗟咏叹、咏歌依违甚至是手舞足蹈。所以,诗的起点就是“言志”,作为基础因素的言辞反映人的内在思虑和定向情感,而曲调和舞蹈所加持的是音律节奏带来的生命本真状态和强大感动力量。
郭绍虞的翻译明显受到《诗大序》“以诗统乐”的影响。而郭绍虞奠定这一翻译基调之后,学者们采取“讴谣”“歌谣”“歌曲”等翻译,都延续了这一思路,“谣舞”一说则并未流行。“风谣”代表的“诗乐舞”与“ballad dance”代表的“舞乐诗”,反映了中西方文艺思想的一些根本差异,这里面的张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次是“poetry”,这个名词主要有两种翻译,一为“诗歌”,一为“韵文”,都与“散文”对应。章太炎和刘师培将其译为“韵文”,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韵文发展先于散文”这一判断仍然频繁出现在文学论著中,陈钟凡著作名为《中国韵文通论》,龙沐勋著作名为《中国韵文史》,这些学者都把“poetry”译为韵文,而龚群钰等学者将“poetry”译为诗歌,郭绍虞则干脆含混言之:“诗亦可以该括一切创作的文学。本来由于各体文学发生的程序而言,韵文常先于散文,所以由风谣更进一步的文学,实在可以‘诗’作为代表。”这段话基本翻译自莫尔顿,但是郭绍虞采取了“韵文”和“诗”两种译法分别对应两句话中的“poetry”。胡云翼也采取了这种含混的方式:“韵文的发达总是较早于散文;而诗歌又为韵文中之最先发达者。”郭绍虞和胡云翼试图以此带过“韵文”和“诗”之间的矛盾,将二者都对应“poetry”。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含混?我们依然要回到英文语境。有趣的是,莫尔顿书中提到,在英文语境中也常常出现“诗”(poetry)和“韵文”(verse)含混的情况,为此他专门辨析了这两个名词。在他看来,作为文体基本元素的“poetry”不能被混用为“verse”,虽然它们都可以和“散文”(prose)相对而言,但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verse-prose”作为一组对应概念时,其区别仅仅在于表层的韵律:
这是一种节奏上的区别。盖一切文学的文字都是有节奏的,不过有个区别:韵文的节奏是“反复的节奏”(recurrent rhythms),是自己会逼着我们去注意它的;散文的节奏是“潜伏的节奏”(veiled rhythms)。韵文的节奏或由脚韵及音节的数目确定之。
而散文和诗的区别更为复杂:
已深涉文学的主要意义和实质。“诗人”(poet)一字,本是希腊语,原义作凡“造作”或“创造”的人解……上帝是宇宙的至高造作者及创造者,我们是上帝所创造所造作的东西,故诗人是一种想像的宇宙的创造者,他又把想像的人物和事情充实这个想像的宇宙……所谓散文的文学,便没有这种创造的作用;散文只以讨论已经存在的东西为限。
这样看来,“verse”译为“韵文”还是比较贴合的。但是“poetry”却难以与中文的“诗”画上等号,“poet”代表“制作者”这一意义植根于希腊文化的土壤,“poet”的活动意味着对世界的意义填充,这与中国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根本出发点就不一样。所以学者们在“poetry”对译上一直显得犹豫不决。很明显,当郭绍虞说“诗亦可以该括一切创作的文学”的时候,他只是照搬了莫尔顿的原文,而并不打算继续“诗”和“创造”的关系探讨,也并未辨析莫尔顿所说的“poetry”和“create”之间那些复杂的语意层次,所以只好在后面加上“由于各体文学发生的程序而言,韵文常先于散文”,将“诗”与“散文”含混言之。
陆侃如、冯沅君作《中国诗史》后,浦江清批评了“诗史”概念:
名为“诗史”,何以叙述到词和曲呢?原来陆、冯两先生所用的这个“诗”字,显然不是个中国字,而是西洋Poetry这一个字的对译。我们中国有“诗”、“赋”、“词”、“曲”那些不同的玩意儿,而在西洋却囫囵地只有Poetry一个字;这个字实在很难译,说它是“韵文”罢,说“拜伦的韵文”,“雪莱的韵文”,似乎不甚顺口,而且西洋诗倒有一半是无韵的,“韵”,曾经被弥尔顿骂做野蛮时期的东西。没有法子,只能用“诗”或“诗歌”去译它。无意识地,我们便扩大了“诗”的概念。所以渗透了印度欧罗巴系思想的现代学者,就是讨论中国的文学,觉得非把“诗”、“赋”、“词”、“曲”一起都打通了,不很舒服。
浦江清从“poetry”和“诗”代表的不同概念外延和层次出发,探讨转译产生的问题。但从莫尔顿的理论出发,我们能更清晰地感受到,“poetry”和“诗”都是深深植根于各自文化土壤的核心概念,尽管它们在各自的土壤中不断延伸,生发出了多种层面,在某些表象上似乎可以共通,但从各自概念的“核”上,它们是难以通约的。这个内在的深层张力本该是学者们用力挖掘的重心,遗憾的是,学者们此时的关注点并不在此,留下了尚待讨论的问题。
通过以上两个语词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认识:在西方舶来的演进脉络被简化成“讴谣—韵文/诗歌—散文”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并未对原文进行过多辨析,也并未深究西方文体质素产生的文化土壤,而是根据相应翻译在中国寻找对应内容,甚至仅仅通过二手或三手文献就开展了自己的中西对应论述。不过,不管怎样,“讴谣—韵文/诗歌—散文”还是作为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通例,被较为成功地投射在了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文学史叙述脉络之中。但在进一步细分的过程中,这种“跨语际”的概念投射就显得不那么顺利了。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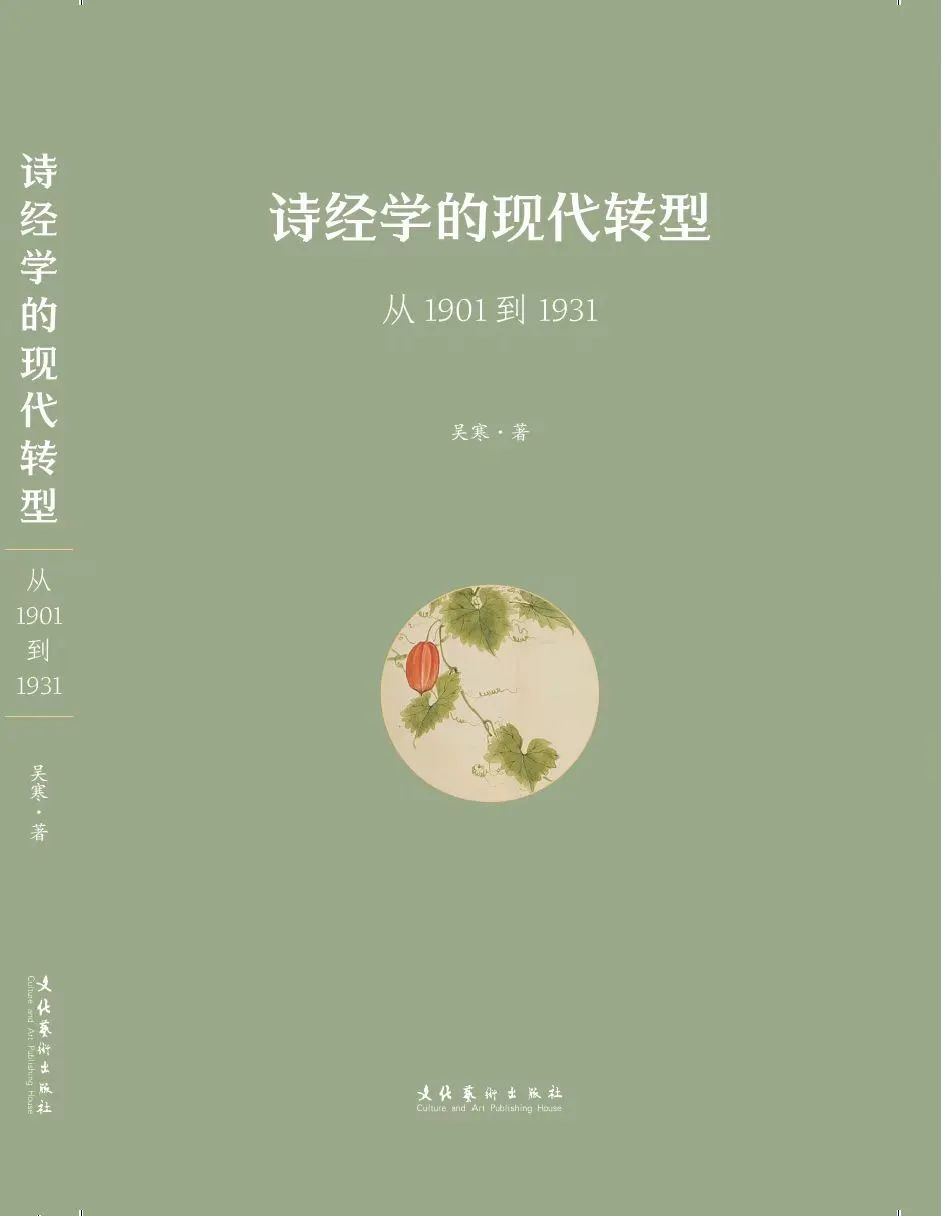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