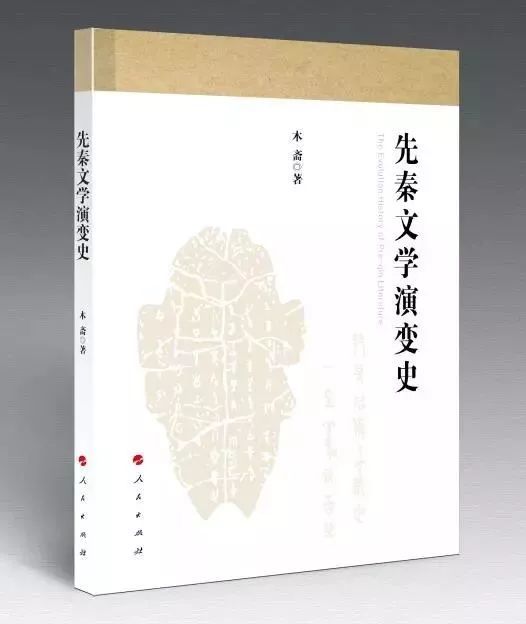
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受限于传世文献,先秦文学被称之为零落的碎片,始终是研究者的一大难题。所幸近年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更激活了先秦文学研究,进而有助于重新认识、改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相较之下,木斋教授的《先秦文学演变史》,则是抱持他一贯的“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大文学史观,在“原典第一”、“独立思考”的研究态度下,对先秦文学的源流与演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
该书观点新颖,力求突破。木斋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说:“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无不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陈陈相因、层累积淀出来的对文学历史的解读,鲜有撰写者能真正从作品出发,从原典出发,从对文学史纵横交错的深入研究出发,来做出对文学史起源和流衍的解读。”如木斋关注到“在理论上,诗歌被视为中国文学最早的体裁;而实际的文学史写作,往往是以神话为开篇”,于是省思传统文学史以中国古代神话为开篇的书写惯例,认为“当下文学史以神话作为开端,主要是采用《山海经》、《淮南子》等后来之文献,是以写作题材所显示的所谓远古内容替代了写作时间,是以想象替代了中国文学史发生的时间次序”。又对诗歌先于散文这种“不验自明”的定论,重新考察先秦诗歌的起源,提出:“诗的因素是在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萌生,以后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音乐的音律节奏引导了这种原本从散文文体中孕育出来的诗歌雏形,从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诗歌”, 并进一步指出:“不论是诗歌早于散文之说,还是神话为中国文学之起源的说法,都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推断,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误区”。另对时间跨度极大的先秦文学,进行分期:从甲骨文、金文到《尚书》的出现为第一阶段,即先秦文学的滥觞时期;西周早期“诗”的出现为第二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阶段,《周颂》—《大雅》—《小雅》—十五《国风》,正代表这一阶段的演变历程;以孔子作《春秋》为标志,其后史传文学、诸子散文、辞赋文体依次出现,展现了从诗歌向散文的回归,是先秦文学的第三阶段。书中不乏振聋发聩之见,在此仅是略举数例,相信在学界一定会激发出更多的火花。
该书文史并重,视域宽阔。作为一部新颖的文学史著作,需要具备充足的文学史料与突出的文学史识,作者自然有所考虑,强调需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前后联系的有机的整体,而非孤立的、静止的、局部的、片段的总和”,并致力于探究“文学史的起源、演变的历时性关系”。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有着比后代文学更宽广的内容范围,体现出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如中国文学最早的经典是“六经”,所以研究者不能不涉及此时期的经学、史学、哲学的研究。文史并重者,如木斋致力于梳理《诗经》中《风》、《雅》、《颂》三类作品的写作年代与演变历程,或排定先秦诸子散文儒、墨、道、法的发展次序,并主张《老子》一书应晚于《论语》、《孟子》,而早于《庄子》等,进行了相关的考释、论证,勇于提出新说。视域宽阔者,如书中论及“甲骨文”、“金文”时,关注到书写工具、载体对于散文写作的制约与影响;或第二章《周公制礼作乐与先秦文学的发轫》,从这一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文化史变革的历史背景,探讨其对先秦文学的催化,并肯定《诗经》是两周礼仪制度的产物等,都是颇具特色的视角。
该书注重原典,述评精要。如同作者在《跋语》中提及“原典第一”的学术原则,在历史文献的参酌下,极大程度地凭借文学作品的内在逻辑,进行比对、考辨,尝试将先秦文学整理成为具有基本规律而可称之为“史”的著作,确实不易,更是一项突破性的挑战。尤其,季羡林先生曾指出,研究中国文学的重点在于弘扬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其中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而木斋不论是从诗歌、散文的文体互动发展,或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技巧及其承衍,都有精要的述评与概括,使读者宏观地认识到先秦文学形式美的发展脉络。诚如书中所言:“文学的审美属性是天生存在的,没有了审美,也就没有了文学”,所以《先秦文学演变史》可说是一部相当注重“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著作,而有别于文学知识概述与代表作品选读式的讲义,充满着文学史家的观点、诠释与解说,令人耳目一新。
总而言之,该书是木斋教授经数年之功结撰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对《诗经》文学发展历程的考索,钻研甚勤,剖析独到,而被著名诗经学者刘毓庆教授称之为“学术史之第一部诗经写作史”,不愧为近来先秦文学研究中极具新意的著作,值得向学界推荐。(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柯混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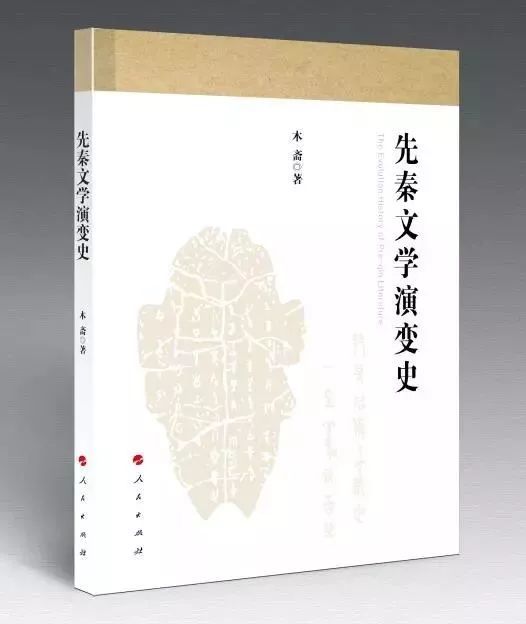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