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受日、俄侵略,满清王朝日薄西山,北洋政府自顾不暇,社会失控,胡匪蜂起。胡匪,又叫胡子,是解放前东北(包括热河、察哈尔、内蒙)对土匪的称呼。
这些胡匪是如何生存和活动的呢?
故事不妨从“东北王”张作霖讲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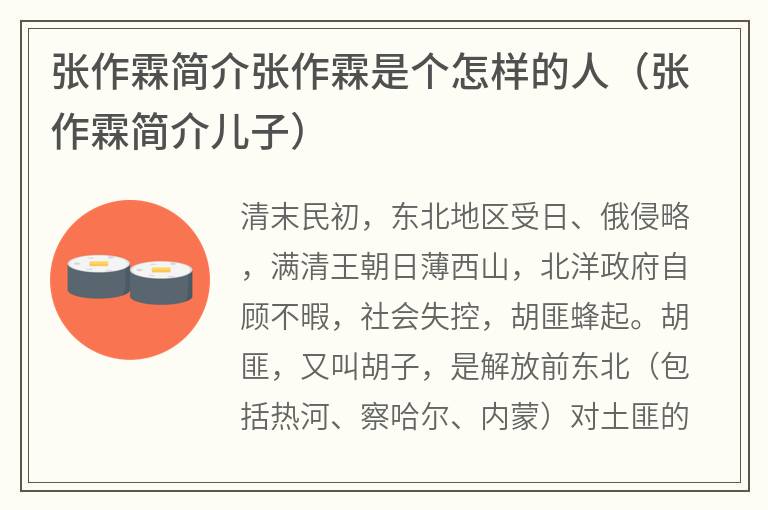
张作霖简介张作霖是个怎样的人(张作霖简介儿子)
张作霖原姓李,河北人。张学良曾说家史:“我们家本来是姓李的,是张家的女孩子嫁到李家去,生了个儿子,可是张家没有后人,就把李家的孩子抱一个回来,过继了一个,就姓张了。”当年流行“闯关东”,张作霖的祖父挑着儿子张有财来到辽宁海城小洼村落户。1875年,张有财妻子生下第三个儿子,取名张作霖,乳名“张老疙瘩”。
张作霖
张作霖十来岁时,父亲张有财给他找了一个赌场里跑腿打杂的活儿。看来张作霖混社会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张作霖14岁那年,父亲和一个姓王的产生赌债纠纷,张有财被王赌徒用镐头砸死,王赌徒逃走。张作霖与哥哥张作孚经长时间寻找,终于觅得王赌徒的下落。一天夜里,兄弟二人拿着土枪去为父报仇,翻墙声惊动了王家下房一个老太太,纠缠时土枪走火,将老太太误杀。这下报仇未成,反添人命。哥哥被捕,张作霖逃亡。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当了一段时间清兵,然后回家从事兽医。3年后,赌债高筑的张作霖走投无路,干脆投身为匪。
那时的东北,是旧中国的缩影,匪盗盛行,民不聊生。加入胡匪的,有散兵游勇,流浪成匪;有些破产农民无法生活,被迫落草;有游手好闲的混混,铤而走险。当时热河省(现分属河北、辽宁、内蒙)比较有名的匪首有好几个。其中有冯麟阁,是个老“资格”匪首,纵横于锦州、彰武一带,平时百来人,人多时啸聚千余。还有一个叫杜立山,据说有8个老婆,个个剽悍,骑马打枪,百发百中。还有一帮是日本间谍带领的,化名王小辫子,专门制造混乱,为日本侵华开路。还有张作霖。
张作霖成立了一支“保险队”,表面看是防匪的。张作霖为人豪爽,大有心计,有当“带头大哥”的天分。用他儿子张学良的话说,就是“有雄才无大略”。张作霖笼络了几个得力帮手,如张景惠、张作相等;还有阜新胡匪、外号汤二虎的汤玉麟。据说这汤二虎,曾用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眉头不皱,谈笑自若。可惜,这么一个耍浑装酷的光棍汉子,后来在1933年热河抗战中,听说日本人打来,带着搜刮的无数金银财宝逃之夭夭,让日军128骑先头部队一枪不放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张作霖落草为寇,却并不甘心,他要效仿宋江,走一条“造反——招安”的路子。1902年的某一天,他对几个兄弟说道:我们在绿林中吃这碗黑饭,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不如凭借着现在有这点实力作本钱,与朝廷讨价还价,谋得一个好出路。众人都说:只要当家的有了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从。张作霖道:据情报,奉天将军增祺的家眷,最近要从关内返回奉天府(今沈阳),现在火车不能直达,我们正好在途中如此这般……
增祺
不久,果然增祺的老婆和家人,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听得一声枪响,道路两旁冲上来一群匪徒,将人员行李截住,关进新立屯街上——这像不像《让子弹飞》的情节?——增祺夫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被张麻子捉住了。张作霖唉声叹气说:现在我国受尽外人欺凌,国内百姓困苦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说不出的痛!我们当土匪,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增夫人以为土匪一定身材魁梧、面貌凶恶,想不到眼前这个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青年,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匪首张作霖!听张作霖愿意投靠官府,增夫人当然顺坡下驴,既解了眼前的困厄,又收编头痛的土匪。回去跟增祺一说,一拍即合,增祺立即命令新民府知府,将张作霖匪帮收编为省巡防营。
从此张作霖走上了土匪—军官—军阀的道路。现在很多网文对张作霖当土匪的经历讳莫如深,甚至有的写张作霖传记,也回避他曾落草为寇。其实,当时的环境中,当土匪固然招官府剿、招百姓恨,但他们自己是不以为耻的。张作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直言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
张作霖还做了一桩狠事,就是诱杀杜立山。
当初王小辫子拉拢冯麟阁时,杜立山曾劝说冯麟阁:王小辫子是日本间谍,不怀好意,我们当土匪已经很难看了,如果再被利用当了卖国贼,岂不要留千古骂名?冯麟阁经不住利诱,不听劝阻,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杜立山对张作霖投降官府也看不起,说:张为官,我为匪,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我们是有骨头的,看他升官好了。
徐世昌
1907年,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严令张作霖解决杜立山。诡计多端的张作霖,精心谋划,设下一场“鸿门宴”。杜立山有一个同族的叔父,叫杜泮林,中过举人,足智多谋,俨然是东北匪帮的军师。张作霖曾拜杜泮林为义父。于是张作霖游说杜泮林,要拉杜立山一同来当官享福。杜泮林一听有道理,写下一封亲笔信,叫杜立山来新民府赴宴。“宴无好宴”。推杯换盏之际,张作霖掷杯为号,屋内屋外一齐动手,将杜立山和他的随从一并拿下,当场处决。
杜泮林听说侄子遭了义子的毒手,大骂张作霖无信无义,卖友求荣。张作霖辩解说:我是奉总督的命令,为民除害,这是大仁大义!事已至此,杜泮林没办法,流着泪说:我已老了,不求显达,所最痛心者,侄儿是相信我才来赴宴,他虽不是死于我手,却是为我所害!
张作霖立此大功,徐世昌奖他白银1万两,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相当于团长。张景惠为帮统,后来出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张作相、汤玉麟都当上了管带。
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时
从此,张作霖走上飞黄腾达之路。武昌起义后,张作霖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被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终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东北王”。
上文多次提到“赌”,有必要多说一句。赌博败坏社会风气,同时也是社会混乱、发展停滞的反映。
宝盒子
当时辽热、内蒙一带,汉人中最流行的赌博是“宝盒子”,不但游手好闲的混混们是赌场的常客,还招揽农民、商贩参与。许多人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输个精光。地主老财每逢刮风下雨不方便干农活时,就召集长工雇农赌宝盒。西拉木伦河乡下一个叫刘祥兆的大地主,就以赌“宝盒子”拉长工下水,使长工们成了他“不吃草料的牛马”。还有很多下乡巡演的剧团,天旱来唱“祈雨戏”,下雨来唱“谢雨戏”,无非是利用庙会聚赌。官僚军警借机抽成、收保护费。蒙古人的赌具则是一种染了红、白二色的牛骨头,也赌得很凶,不少人倾家荡产。
赌又总与毒相伴。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行销东北。民国初年,日本人又贩运来金丹和吗啡,毒性比鸦片更强烈。兵连祸结,赌毒烟毒,搞得民生凋敝,国民从精神到身体孱弱不堪,为敌国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以前的东北平原、内蒙草原,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掉进饭锅里”。关内人在家乡过不下去,向这些地方移民。原本生活在内蒙草原的蒙古族人,大家称之为“真蒙古”;从内地移民过来,与蒙古族通婚而入籍的,称为“随蒙古”。在热河朝阳县,广岭山(医巫闾山)西南,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原籍山东长清,祖先迁居到这里,入赘蒙古人家,成了“随蒙古”。李家后代,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土匪,后来当了汉奸,任伪蒙军总司令。他叫李守信。
李守信
李守信,原名李义。李家祖先迁来热河后,善于耕耘,勤俭持家。到李义父亲这一代,积攒财富日多,有三十“天”(一“天”等于十亩)土地,有牛、马、羊群,喂了十几头肥猪。家里请着三四个长工,农忙时还要请几十个短工。李义的父亲弯腰曲背,外号“李罗锅子”。
地主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有人眼红了。李家祖先刚来时,在一个叫色楞的“诺颜”(奴隶主)家当奴才。色楞每次到古力古奤收租,必来李罗锅家,大吃大喝,临走还要捉猪宰羊,拉米驮面。当时李家有土炮火枪,还有三支快枪,年轻气盛的李义恨不得拿枪崩掉色楞。李罗锅紧紧拉住李义说:“‘诺颜’杀了奴才可以不偿命,奴才杀了‘诺颜’得满门抄斩!”后来李罗锅花了1万7千串钱,交给色楞作赎身费,并买通衙门“档子房”,颁发了一张永远跟色楞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不料色楞哪管你什么执照不执照,仍然长期来李家赖吃赖喝。李家无法,一直供养色楞到死。
李义可不像他父亲李罗锅那样唯唯诺诺。他从小喜欢骑马玩枪,常与胡匪和当兵的接近,听他们讲冒险经历。这为他后来的胡匪和军队生涯积累了见识和经验。李家有枪有子弹,李义很小就拿枪到野外打野兔。到他十一、二岁时,射击准头已相当不错——李守信靠着神枪手的本领,能镇住人、能做成事,十分剽悍。“开壳”(作战)时,经常四、五个人为他装填子弹,“右肩被后坐力打肿,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这是后话。
蒙奸德王和汉奸李守信
李罗锅见儿子这么调皮捣蛋,怕长大了惹是生非,把他送进私塾读书。念了半年《百家姓》、《三字经》,李义实在提不起兴趣,经常逃学。父亲见他不是读书的料,又让他带着长工干农活,每天早起晚睡,想把他培养成持家守业的地主。李义更加不甘心,一天梦想到外面去闯荡。父亲实在没办法,干脆给李义娶了一个蒙古族老婆。那年李义14岁,老婆德力玛21岁。
各县衙门都有一支保安民团,由本县地主出钱出人。凡有地十“天”的,出步警,有地三十“天”的,出马警。这跟张作霖当初给二十来个村当“保险队”,作用相同,所不同的一个是“官办”,一个是“民营”。李义家有地三十“天”,应出马警。父亲见李义整天跟大兵混日子,根本不理田间地头的事儿,索性叫他去当马警。
由于兵荒马乱,热河蒙汉百姓养成了剽悍的民风,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会骑马打枪。老百姓把胡匪称作“耍人的”,三、五成群的小胡匪叫“地蹦子”。为对付胡匪,地主豪强修建“炮台”,中小地主合起来修建围堡,还相互联络形成“联庄”。守卫炮台和围堡的叫“炮手”。张作霖的“保险队”就是养着“炮手”,对付“地蹦子”。对于那些立起了“字号”的大胡匪,他们则尽量结交,平时互不侵犯,有利益时互相输送。
李义加入马警队后,初生牛犊不怕虎,追杀“地蹦子”毫不留情。他把杀人当儿戏、当乐趣,每逢作战,总是冲锋在前,枪枪见“肉”。渐渐地,李义在家乡大庙大奤一带打出了名声。这下李罗锅更加心惊肉跳,一怕儿子在枪战中失手,二怕结怨多有人来报复,赶紧花钱雇人顶替李义,让儿子回家呆着。
“人怕出名猪怕壮”,李义的名声打响后,不断有“朋友”来拜访,想方设法拉李义入伙。李罗锅见儿子在家里管不住,一狠心,让他出家当喇嘛。21岁的李义,剃光了头,到离家不远的平顶山庙拜罗旺喇嘛为师。罗旺师傅久闻李义大名,收下这个徒弟后,不传授经书佛卷,而是叫李义当保镖。
蒙奸德王和汉奸李守信访问日本
罗旺喇嘛的庙宇,每天迎来送往,络绎不绝。白天给“官线上的”人洗尘,晚上给“耍人的”接风。有时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就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双方都假装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黑白两道通吃的罗旺,经常与人“说票”。什么叫“说票”呢?就是土匪绑架了人质,索取赎金的多少,由罗旺这个中间人“定价”。如果哪股胡匪不买账,罗旺就调动别的胡匪和官兵联合剿除。这一特殊身份,确立了罗旺喇嘛的“江湖地位”。每次出门,李义和其他保镖骑着快马,背着长枪,腰挎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沿途商家百姓,无不拱手而立,尊称罗旺“喇嘛爷”。
李义给罗旺当了两年多“炮手”,懂得了很多为匪做官的诀窍,学会了拉帮结派、广交朋友。罗旺察觉李义野心勃勃,不放心留在身边,借口李义喜欢打野兔,杀性太重,不能当佛门弟子,婉言把他辞退了。
父亲李罗锅去世,李义这匹没有笼头的野马,开始了闯荡江湖,为害世间的罪恶人生。
1917年,27岁的李义,加入了半官半匪、亦官亦匪的热河游击马队。为了掩人耳目,掩盖行藏,李义改名李守信。他同他的狐朋狗友们扯起了“信”字旗号,招纳“耍人的”和“马鞑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李守信屡次被推举为“大当家的”,对外联络以“信字”为暗语。报出字号,才有人给你“开扇”(开门),跟你答话。
胡匪看似乌合之众,其实内部章法森严,规矩严明。一般小打小闹的“地蹦子”,和钻高粱地拦路搜腰的“穿帐子的”,算不得“入流”。胡匪纠集成帮,叫“拉杆”。各个“杆子”强弱不同,人数多寡不一,多则一百多人,少则三、四十人。要做“大买卖”,几股“杆子”合伙,叫“合杆”。杆子头儿叫“当家的”,合杆推选出一个“总司令”,叫“大当家的”。“合杆”“划起来”后,无论去“卡线”(拦路抢劫),或者去“打窑”(抢劫固定目标),一般派一组去对付对方的“炮手”,一组负责控制货物,一组担负机动警戒。“开壳”(作战)领头的叫“炮头”;有“秧儿房”当家,负责看管“秧儿”(人质和赃物);有“账房”,负责军需和记账。
“打窑”的胡匪
记账是个精细活儿,必须由“当家的”的心腹担任。每次“出摊子”,由“当家的”垫支“股本”,包括枪支、弹药、给养。“出摊子”前,大家要把自己的财物报告给账房。行动结束,“漫开”(分散)之前,还要搜一次身,以防私吞。带枪骑马来入伙的,叫“小绺子”;托亲靠友临时入伙,叫“贴杆”;有马无枪的叫“爬子”,只能做底层的苦活儿。“分项”(分赃)时,先扣除“材料费”(子弹消耗)、设“点儿”费(打交道费用)、“线头”(密探)费,再按大小来分。一般“当家的”可分得两股或三股,“秧子房”当家的和账房得一股半,其余分给各个“绺子”。“爬子”可分半股。枪、马也要参与分账,叫“枪马股子”。
当家的还要对内部进行严密控制。“开壳”(打仗)时,不听命令往后退,或危急时“溜杆”逃跑的,“炮头”可以就地正法。看守“秧子”的人,把秧子丢了,往往也会被当家的处死。“杆子”里的人,打着当家的旗号去“捐小项”(敲诈勒索),或者溜出“杆子”去“开小股”(单独抢劫),更被“当家的”深恶痛绝,一经发现,必严刑惩处。
当胡匪是高危“职业”。如果“爬子”没本事,不会混,当家的会瞅机会把“爬子”扔给官兵当礼物。比如被官兵、民团“焊上”(包围和追击不放),“杆子”会“甩头”(扔马匹);“甩头”不满足,只好把“爬子”扔给对方,让对方有所斩获好回去交差。
著名的匪首“座山雕”
不要以为“当家的”可以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如果当家的乱报花销和虚报“材料费”(子弹消耗),败了名声,以后“杆子”划不起来,甚至会挨黑枪。每到“分项”时,当家的要回避,让大家公议公决。当家的必须长期养“眼线”,打“窝子”。有时出一趟“摊子”,当家的还会蚀本倒亏!
一般“绺子”、“爬子”,都是亡命之徒,孤家寡人。“当家的”则有家有室,暴露出去会连累家人。从前的李义,现在的李守信,母亲和妻儿仍是朝阳县的地主。有一次李守信“出摊子”路过家乡,用毛巾蒙面,只露两个眼睛,但说话时被熟人听出口音。他赶紧派人回家去,叫父母兄弟到县衙递状子,告李守信忤逆不孝,脱离母子兄弟关系。
作为“当家的”,要心机深沉,处事机警,会左右逢源。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把每个人都当作敌人和叛徒看待,时时严加提防,包括“拜把兄弟”。许多表面风光的匪首,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整天沉默寡言,似睡似醒。他们看着像在打盹,其实暗地里盘算心事,琢磨行动目标和细节。长年累月下来,变得半疯半癫,连窗前落下一片树叶,也会蓦然惊醒,以为危险降临,随时准备掏枪或开溜。
李守信、王英、白凤翔被称为内蒙“三大匪首”。白凤翔当胡匪时,从来枪不离身。他后来当了汉奸高官,习惯不改,腰上仍然插着7支手枪,加上弹药一共20多斤,连睡觉都不解下来,就睡在铁家伙上!
胡匪“出摊子”“分项”完毕,迅速“漫开”,不然被官兵“焊上”,不容易脱身。其他“杆子”听到消息,也会来黑吃黑互“嗑”。“绺子”和“绺子”之间,为意气或贪财,会偷偷放“黑炮”。
胡匪正在射击
多数胡匪找“大家儿”的“炮台”、围堡,窝藏并销赃。称得上“大家儿”的,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物,如地主、商号、寺院、镖局,蒙古王公、牧主、喇嘛等等。
“大家儿”、“炮手”、“胡匪”,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胡匪缴纳“保险费”,躲进“大家儿”的“围堡”,吃喝玩乐,等待下一次“出摊子”。有的胡匪身无长物,需要向“大家儿”借马借枪,购买子弹,“大家儿”乘机放高利贷和高价卖子弹。
“炮手”明里是保安,暗中当“绺子”。他们平时为“大家儿”警卫执勤,有机会就“贴杆”做一票。“保险队”的“炮手”偷偷出去当一趟“绺子”,极其隐秘。胡匪“卡线”、“打窑”,往往会跑出“圈子”(自己和朋友的地盘)很远,到百八十里,甚至好几百里外做“买卖”,前方有“挑线的”(向导)和“引线的”(暗探)配合。
“大家儿”豢养“炮手”、窝藏胡匪,有的还吃胡匪。胡匪出了“摊子”,手中有几百上千银洋,寄放在“大家儿”的柜台上。“大家儿”要收拾某个胡匪,只需给“炮手”使个眼色,“炮手”就把这个胡匪悄悄弄死埋掉。枪、马作“炮手”的酬劳,资财落入了“大家儿”口袋。用胡匪的黑话说,这叫“寄封”。熟知内幕的李守信道:“胡匪在战场上和刑场上死得很少,被‘大家儿’弄到秘密地方‘寄封’,和自己人在回头转弯时被放‘黑炮’打死的居多。”
黑暗的旧社会,兵匪不分。热河的军队中,大约一半的人干过胡匪。当官的吃空饷、喝“兵血”,当兵的只得自找财源,一是窝匪,二是为匪。一般升到连长,可以不亲自出马,排长及以下,经常领着士兵去“卡线”,截“镖驮”或“烟驮“。“兵油子”一听说有人“划”起“杆子”要“出摊子”,换上便衣就跟去当“小绺子”。打劫回来贡献一部分给长官和同袍,互相掩盖。奉命剿匪时,与胡匪关系密切的官兵往往虚张声势,甚至让开一条出路,放胡匪突围。
骑马奔驰的胡匪
胡匪找有关系的军队藏身,叫“爬风”。中下级军官无不窝匪。胡匪来“爬风”,营、连长们可以坐地分赃,还可以高价出售子弹,必要时以匪剿匪和雇匪打仗,比指挥手下的兵还好使。军官藏着私枪、养着私马,打仗时虚报子弹消耗,然后垫支给胡匪“搭股”。
高级军官搂钱的办法更厉害。东北军骑兵旅长崔兴武驻守赤峰期间,打探到有个叫张义臣的“大家儿”,与一个姓胡的太监关系密切。这胡太监管理承德行宫和北京故宫的古玩,用赝品换出宫里的珍品,寄放在张家。崔旅长硬说张义臣窝藏和接济胡匪,要办他。张义臣只得贡献给崔兴武一对康熙时期的五彩瓷瓶,并花了几万块钱才摆平。
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热河游击马队首领张连同,在热河带了15年兵,脱离部队时,家里至少有20万大洋存款;在北京有五六处房产,大栅栏开着一家商号;在开鲁有三十方地,约合12000亩;湖南老家还有许多土地房屋。崔兴武当旅长不到7年,贪得的财产比张连同还要多。这些军官如果成为大军阀,不就是又一个张作霖、李守信吗?!
胡匪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怪胎。他们性命朝不保夕,“出摊子”回来就狂赌滥喝,钱花光了出去再抢,抢到手随性乱花,恶性循环,很难洗手不干。他们这样为非作歹,残害民间,老百姓如何水深火热,可想而知!
新旧对比,感恩当下,庆幸如今太平盛世,河清海晏,不用活得提心吊胆。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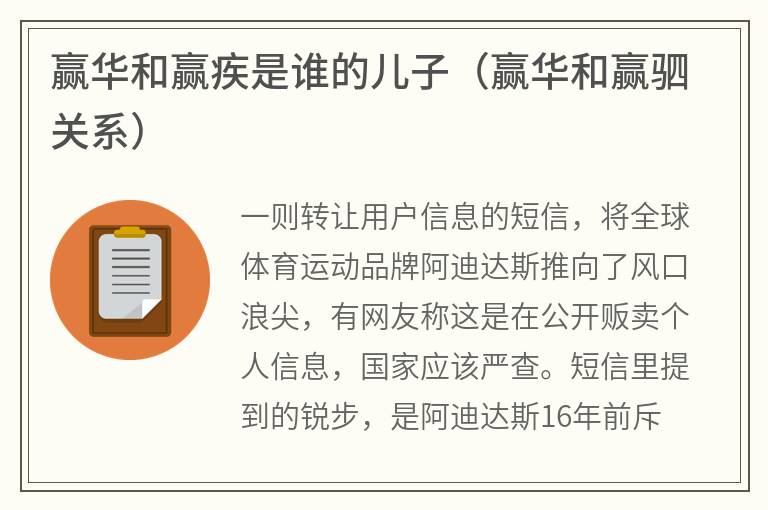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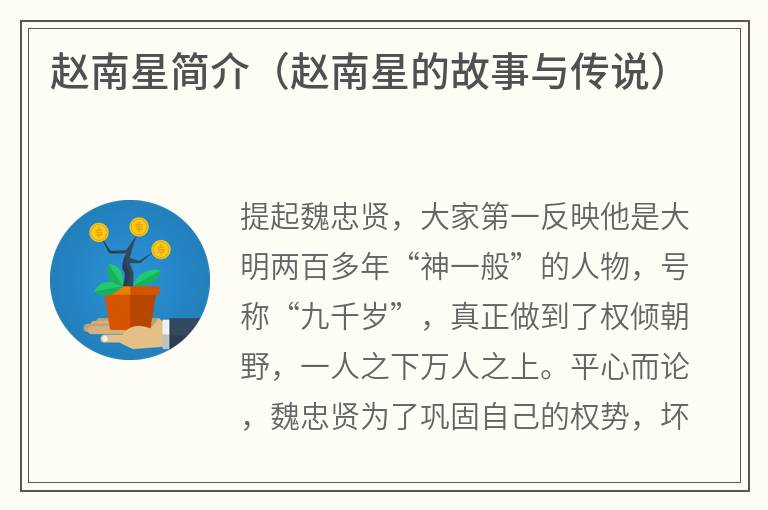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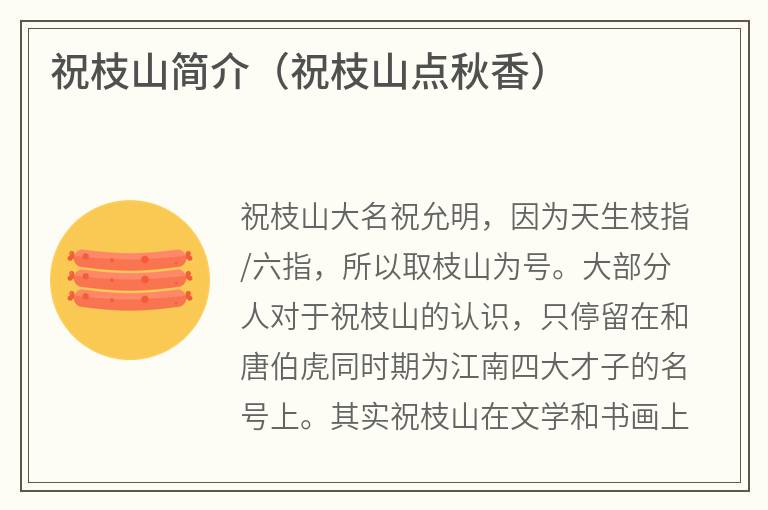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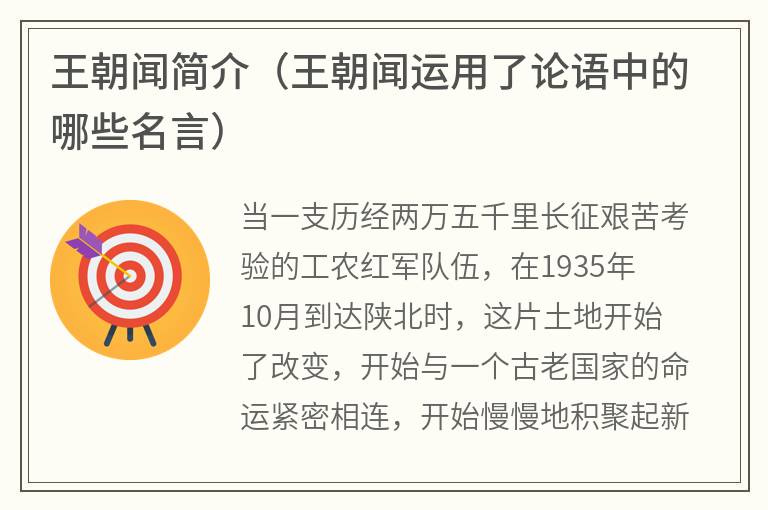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