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恩俊
清代赵之谦、程守谦合作《菊花博古图》轴。(来源于上海博物馆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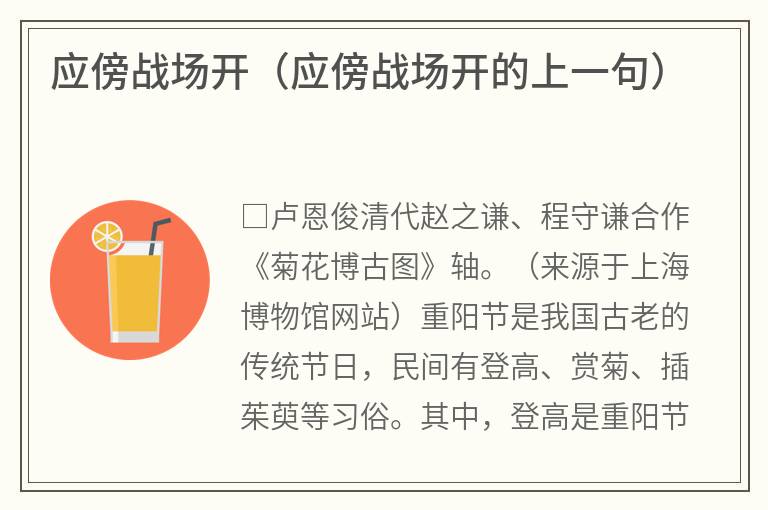
应傍战场开(应傍战场开的上一句)
重阳节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民间有登高、赏菊、插茱萸等习俗。其中,登高是重阳节的重头戏,而菊花、茱萸这一花一木,则是节日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一
“九日登高处,群山入望赊。”(明·赵时春《原州九日》)重阳登高,主要有登山、登塔、登楼、登阁、登台等形式。登高习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西汉的《西京杂记》中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可见,重阳登高习俗在西汉时就已经形成。至于重阳为何登高,南朝梁人吴均在神话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中记述了东汉方士费长房让桓景携家人于九月九日“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躲避灾祸的故事,认为当时人们“九月登高饮酒,妇女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此说虽然迷信色彩浓厚,但重阳登高祈福的习俗却流传下来。正如宋人方勺所释:“九九极阳,阳极转阴,登高为调阴转阳也。”古人将天地万物归为阴阳两类,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奇数,因此属阳,九月初九,二阳相重,遂称“重阳”。古人以登高调和阴阳,祈求健康长寿,而被誉为“长寿花”的菊花和被称为“辟邪翁”的茱萸正好繁盛于秋,成为必不可少的节日明星。于是,插茱萸、戴菊花、饮菊花茱萸酒等习俗逐渐盛行,这在古诗中多有体现。唐人留下的登高名篇最多,边塞诗人岑参在行军途中适逢重阳节,十分怀念故园的菊花:“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卢照邻重阳登山时写下“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的著名诗句(《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抒发怀乡之情。杜甫在《九日登梓州城》中写下“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的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重阳登高诗中最著名的要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该诗通过描写重阳风俗,把游子思亲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成为千百年来佳节思亲的经典之作。
与登高相关的风俗还有吃重阳菊花糕。“糕”与“高”谐音,最早是庆祝秋季丰收、喜尝新粮之意,之后民间逐渐有了“登高吃糕”的习俗,取步步登高的吉祥寓意。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论糕》中说:“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粟,当筵题句傲刘郎。”又有《竹枝词》:“土城关外去登高,载酒吟诗兴致豪。遥望蓟门烟树外,几人惆怅尚题糕。”两诗描绘了当时的重阳制作花糕、登高的盛况。据《唐六典》和《食谱》等典籍记载,唐代重阳节有菊花糕、菊花鲜栗羹、木香菊花粥等席上名点。由此可见,品尝菊花糕自古以来便是普遍的重阳习俗,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垒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识。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燕京岁时记》也记载,每逢重阳节,京城里的人纷纷“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可谓“一时之快事”。时至今日,在我国许多地区,吃重阳花糕之风尤盛。
二
“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唐·王勃《九日》)古人过重阳,最看重的是菊花。菊花在古诗词里也称“黄花”,是“长寿之花”,亦是不屈品格的象征,所以古代重阳节,赏菊、簪菊、饮菊花酒、食菊花糕等,自然就成为风行的习俗。唐代另一位诗人王维则直接称重阳节为“菊花节”:“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
古代重阳的“菊花热”,最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驱邪、保健、延寿的理念。汉代的《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的记载,“黄华”即菊花。最早以菊入诗的名人当数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他通过“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诗句,表明自己不随流俗、洁身自好的节操。早晨饮用木兰花上滴落的露水,傍晚咀嚼秋菊飘落的花瓣,诗人不仅赋予菊花高洁的品行,还提及菊之可食,奠定了菊花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魏晋时期,田园诗人陶渊明更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享誉古今,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其“独爱菊”。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序文中记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陶渊明关于菊花的诗句数不胜数,他将菊花视为洁身自好的象征,还将其作为“长寿花”来食用。他在《读山海经》(其四)中说:“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陶渊明以品行高洁闻名于世,他的菊花诗更是千古名篇,大大推动了后世重阳赏菊之风。
三
“明年会此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唐·杜甫《九月蓝田崔氏庄》)古人将茱萸视为祛邪之物,每逢重阳争相佩带。我国对茱萸的记载比较早,《礼记·内则》中有“三牲用藙”的记载,“藙”即一种茱萸。周代祭祀之制,是把牛羊猪“三牲”放在祭板上,将煎过的茱萸等放在祭盘中用于祭祀,可见那时人们就视茱萸为非凡之物了。对于茱萸的药用价值,早在《神农本草经》《吴晋本草》中已有记载。东汉桓景携家人于九月九日戴茱萸囊登高躲避灾祸的故事传开后,茱萸又被视为辟邪禳灾的“护身符”,称“辟邪翁”。南朝宋武帝刘裕曾在重阳节大宴群僚于戏马台,还把茱萸当成犒赏军队的奖品,有诗曰:“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唐·储光羲《登戏马台作》)。可见,茱萸在民俗中的地位并不比菊花逊色。既如此,茱萸在唐代之前为何没能像菊花那样在诗词歌赋中大放异彩呢?
余光中先生在《茱萸之谜》一文中说,“重九二花,菊与茱萸,菊花当然更出风头,因为它和陶渊明缘结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或许因为屈原曾在《离骚》中把樧(茱萸)斥为恶草,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了唐朝,茱萸由“恶草”陡然变成“佳木”,一首首关于茱萸的好诗令人目不暇接。重阳节插茱萸之风在唐代民间很流行,用王维诗中的“遍插茱萸”来概括恰如其分。宋代以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减,但从明代申时行的诗句“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登高胜事夸。郡人齐出唱歌曲,满头都插茱萸花”,还有清代吴伟业的诗句“秔稻将登农夫喜,茱萸遍插故人怜”来看,插茱萸的习俗在一些地区依然盛行。
对于唐代“遍插茱萸”的习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茱萸插在何处?怎么插?唐诗里对此多有描述。朱放的“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权德舆的“他日头似雪,还对插茱萸”,耿湋的“九日强游登藻井,发稀那敢插茱萸”等诗句,都表明当时过重阳是将茱萸插在头上的。进一步来看,卢纶的“茱萸一朵映华簪”,白居易的“舞鬟摆落茱萸房”,王昌龄的“茱萸插鬓花宜寿”,还有李白的“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等,都点明了茱萸在头上的具体位置。
沿着茱萸的诗韵步步深入,就嗅到了迷人的酒香。我们能够通过苏舜钦的“欲言无上策,且复醉茱萸”,体验沉醉在茱萸佳酿中的人生际遇;通过白居易的“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分享重阳小酌听曲的惬意,还能通过张谔的“归来得问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几人”,感受古代重阳的风情画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