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早年“轻侠杀人,闻于郡中”,因此被视作亡命奸臧,甚至被冠以“锦帆贼”的诨名。然而考诸史料,可以发现甘宁的出身与仕宦履历并不寻常,应被归入富室、豪强阶层。
鉴于甘宁以“粗猛好杀”闻名,且入吴之后屡为军锋,因此常被视作武夫之伦;然而其“开爽有计略”的性格特征,又不同于寻常武人,这应得益于他“颇读诸子”的教育背景。
本文想就史料线索,探讨甘宁的出身、籍贯、仕宦履历与早年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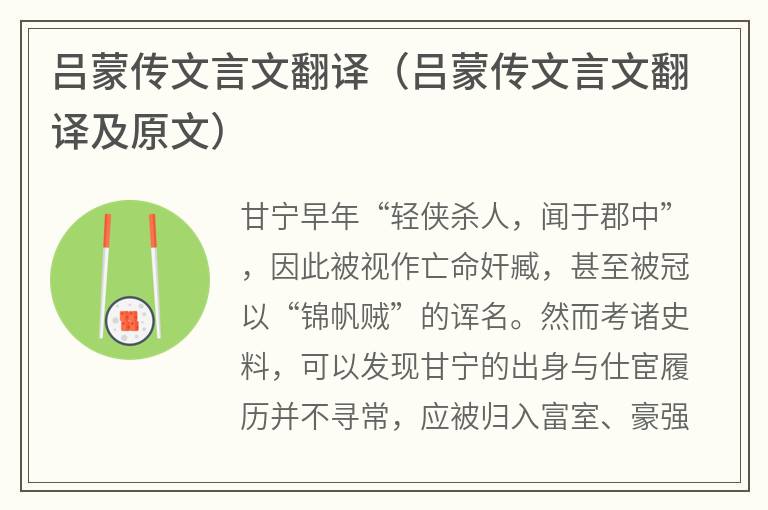
吕蒙传文言文翻译(吕蒙传文言文翻译及原文)
本文共7300字,阅读需14分钟
陈寿在《吴书》中称甘宁为“巴郡临江人”,即益州出身,却未提及其先世所在。
东吴国史作者韦曜称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即甘宁祖籍荆州,之后客居益州。相较陈寿,韦氏的论调便完善许多。
不过严格来说,韦曜的论调也不够严谨。按《晋书甘卓传》,传主是甘宁曾孙,同时也是“秦丞相(甘)茂之后”。可知甘宁先祖可追溯至甘茂。
按《史记》,甘茂出身下蔡。两汉时代,下蔡旧属沛郡,隶豫州;后划入九江,隶扬州。照此描述,甘宁先祖实际经历了自长江下游(扬州九江)迁徙至中游(荆州南阳),又由中游(荆州南阳)迁徙至上游(益州巴郡)这样一番变迁过程。
按彼时传统,流寓侨人落户新土,数代之内便会改移籍贯。便如甘宁仕吴时以侨人自居,但至其曾孙甘卓,便成为“丹阳人”(见前文注引《晋书》),籍贯从益州变为扬州。
类似案例还有张昭(籍贯徐州彭城)曾孙张闿、薛综(籍贯豫州沛郡)之孙薛兼,此二人在《晋书》中皆被称作“丹阳人”。可知士人后裔一旦扎根新土,便会改易籍贯。
张闿,丹阳人,张昭之曾孙也
从时代背景上看,改易籍贯基本可以视作侨人出仕的必由之路。因为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官人法,均由长官(牧、守、公平、中正、州都)在辖区内进行考察推荐,“乡论”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流寓士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出仕机会,因此改易籍贯势在必行。
《华阳国志》记载,巴郡临江县中有五大宗族:严、甘、文、杨、杜。常璩还特意标注“甘宁亦县人”,可知魏晋之际,临江甘氏已成巴郡“大姓”。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后,甘氏宗族已经扎根益州,且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这也是甘宁可以通过正常宦途出仕益州的历史背景。
《甘宁传》中有一处带有歧义性质的描写,即传主“贼害”郡中,“至二十余年”,之后才“止不攻劫”,出仕州郡。
此处的“二十余年”涉及到翻译问题。若将之理解为甘宁在巴郡地方作恶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则与甘宁的年龄及履历不符。
兴平元年(194)是甘宁人生的分水岭,是年他反叛刘璋,战败后亡入荆州。因此他“贼害”郡中,必然在此之前。
按甘宁“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的行径来看,彼时其年龄下限不会低于十五岁,若如此,“二十余年”后的甘宁,年龄便会逼近四旬。此时他“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出仕后再历经“计掾”、“郡丞”的升迁考核,那么兴平元年(194)的甘宁,年龄至少在四旬以上。
这里存在一处矛盾记载,即建安十九年(214)甘宁从攻皖县,“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是年(214)与兴平元年(194)相距二十年,若甘宁真的在巴郡之中“贼害”二十余年,那么他“手持练,身缘城”时的年龄便不会低于六十岁,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甘宁从攻皖,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
学者卢弼对陈寿的记载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甘宁在郡中贼害至多“十余年”,怀疑“二”字为衍文,否则“史文为误”。
其实卢弼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史文为误”。在笔者看来,或者“二”字为衍文,或者“年”字为衍文。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甘宁在郡中“贼害”,前后“至二十余”。即甘宁的游侠生涯,在他二十余岁时便已结束,之后读书仕宦,出仕州郡。
若此设想成立,便可完美契合甘宁的年龄与履历。换言之,他在皖城之战、合肥之战时不过四十余岁,正值盛年,“为吏士先”、“出斫敌营”的行为也便合乎情理。
甘宁在益州的仕宦之路,是先“举计掾”,后“补蜀郡丞”。应该说,这是地方豪强才拥有的特别待遇。
“计掾”即州郡的“上计使者”,亦作计佐、计吏。按甘宁为“巴郡临江人”,他充当的应是巴郡的计吏。
所谓计吏,即负责将所在辖区钱粮、赋税、户口等考绩指标上报于上级单位的属员,该职责称作“上计”,类似现代之“述职”。县邑上计于郡国,郡国上计于中央,州刺史亦上计于中央。
上计使者的人选,因时而变。西汉初一般由郡国长官躬行,东汉时则委之于掾属中地位较高者,官长不再事必躬亲。
“上计”在人口流动性较差农业社会下,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比如“少孤”、“家贫”的邓艾,本为“稻田守”、“丛草吏”,微末至极,他在担任“典农纲纪”时,因为得到了“上计”的机会,拜谒了太尉司马懿,便被延揽为(太尉)掾,遂仕宦洛阳,最终发迹。
注:典农,即典农中郎将,位同郡守,见《常道乡公纪》;纲纪,即功曹,属于郡、县中的高级掾属。州一级功曹称“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
从历史发展看,虽然邓艾担任“纲纪”时的境遇已比之前改善不少,但真正令他飞黄腾达的,还是“上计”赋予的宝贵机会。侧面亦反映出,出仕即担任计掾的甘宁,宦途比“孤贫”的邓艾要顺畅得多。
邓艾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懿
东汉时代,“郡国计吏多留拜(洛阳)为郎”,可知这一职务亦可视作中央的储备干部。
汉末三国时,出仕为计吏、计掾者,多为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郑玄被孔融延揽“为计掾”、许靖“举计吏,察孝廉”、蒋济“仕郡计吏、州别驾”、姜维“仕郡上计掾”。
注:郑玄事见《邴原别传》、蒋济事见《魏书》、许靖、姜维事见《蜀书》,文多不引。
郑玄“隐修经业”,属于汉末儒宗;蒋济“才兼文武,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许靖“清谈不倦”,与从弟许邵(月旦评创始人)知名当世;姜维“凉州上士”,被钟会誉作夏侯玄之伦。
不难看出,上述诸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具备出色的学术素养,这与计掾、计吏的工作职责密切相关。换言之,甘宁能够出任巴郡计掾,便证明其必然具备寻常水准之上的文化底蕴,这也符《宁传》记载的传主“颇读诸子”、“开爽有计略”。
通过“计掾”的身份,不难推测甘宁能够“补蜀郡丞”必然与此有直接关联。
按前引《英雄记》,甘宁出仕益州,当在刘焉统治时期。刘焉初治绵竹,后徙治成都,刘璋遂因袭之。甘宁既为巴郡计掾,那其“上计”时应赴成都汇报,成都县又属蜀郡,那么他得到上官的提携延揽,担任蜀郡丞也便合乎情理。
郡丞的地位又较计掾为高,属于郡中的高级佐官。按《续汉书百官志》,内地之郡置长史、郡丞各一;边地之郡“丞为长史”。东汉时“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代其)行事”,可知郡丞之于郡守,便近似于常务副职,有权在长官无法履行义务时“代行郡守事”。
以同时代人物为例,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在宗族流徙之前(尚未失势时)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泰山郡丞,而甘宁早在初平年间(190-193)便成为蜀郡郡丞,比诸葛珪的仕宦起点要高得多。
注:按《英雄记》,甘宁反叛刘璋在兴平元年(194),可知其担任蜀郡丞必在此前。
亮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
东汉时有“三互法”(见《蔡邕传》),即“任官避籍”制度(官避吏不避),由非本籍士人担任地方官长(官),地方官长再举用本地豪强充任官府属员(吏)。
甘宁为吏则为巴郡计掾,为官则至蜀郡郡丞,结合甘氏在临江为“五大姓”之一(见前引《华阳国志》),充分证明他必定是益州地方的头面人物,绝非寻常的草寇蟊贼。
如前所述,落籍巴郡,宦途坦荡的甘宁,无疑出自益州地界的豪强之家,因此看待甘宁的“游侠”行为,便需要结合其出身背景,不宜单纯以强盗视之。
甘宁的装扮十分具有迷惑性。他行劫时“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审美可谓怪异。
所谓“负毦”,即背插鸟羽兽毛织物。韦曜注释《国语》时,便将“鸟羽系于背”比作“负毦”。可知甘宁行劫之时,前呼后拥,背插鸟羽,腰悬铃铛,因此“民闻铃声,即知是宁”。
鉴于甘宁的审美观念怪异,因此易被误解为出身层次有限,文化水准不高;其实这种怪异装束,在彼时的巴郡(甘宁老家)并不算特立独行,与门第高低亦无关联。
《华阳国志》记载,魏晋时期,益州巴郡“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又有“女服贼千有余人,布散千里”,已成地方盛景。相较于“女服贼”,“负毦带铃”的甘宁,顶多算是审美奇特,任侠之时喜好夸耀于众。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游侠之风盛行。其中既有臧霸、孙观这种出身较低,被视作“强盗”的游侠;也有袁绍、袁术、张邈、曹操这种兼备“名士”身份的游侠。
从甘宁的宗族出身(临江五姓之一)与仕宦起点(巴郡计掾)来看,他明显属于后者。即豪强之家的不肖子,以游侠之事为乐。
按甘宁“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的记载看,他的行径与刘縯、刘秀兄弟具备相似之处。
两汉之交,刘縯兄弟在南阳“臧(藏)亡匿死”,而“吏不敢至门”,可见这一级别的豪强明显凌驾于治安体系之上。而甘宁“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甚至还可以接待“属城长吏”,乃至“隆厚者乃与交欢”,与当年的刘縯兄弟毫无二致。
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
甘宁在巴郡作恶多端,“属城长吏”却拿他无可奈何,侧面反映出其家族在当地必是雄霸一方的豪强。相较而论,关羽、臧霸等人轻侠杀人之后便被迫“亡命”外州(臧霸由兖州入徐州,关羽由司隶入幽州),明显不具备甘宁般的权势。
关羽早年记载不详,或出自单家。臧霸劫狱时能够“将客数十人”,应出自低等豪强,即使如此,他还是被迫“亡命东海”,可见其家世背景无法庇荫其人身安全。
两相对比,与“属城长吏”交好,“贼害”郡中“至二十余年”的甘宁,其家世能量究竟如何,也便不言自明。
同时代中,类似甘宁般豪强出身的游侠,案例甚多。曹操“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张邈“以财救人”,皆属此类。
再比如袁氏兄弟,出身门阀之家(比甘宁的门第高得多),却均具备游侠色彩。袁绍“坐作声价,好养死士”,早年还曾参与抢婚一类的无赖行迹(见《世说新语》);袁术“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也是一丘之貉。
相较而论,袁术“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的行为,与甘宁“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的炫耀之举,并无本质区别。袁术有“路中捍鬼”的诨号,甘宁亦有“锦帆贼”的恶名,均属豪强之家的不肖子。
甘宁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
甘宁出游,“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其同僚贺齐,“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便被时人称作“奢绮”;那么甘宁“以缯锦维舟”的豪奢程度也便一目了然,可知其家族不止是豪强,同时也是富室。
《华阳国志》记载,临江县盛产井盐,以至“一郡所仰”,而“豪门亦家有盐井”。按甘氏为临江五姓之一,可知其家族很可能亦拥有私人盐井。两汉魏晋时盐铁专营,掌握了食盐,便掌握了财富命脉。甘宁也因此具备了交结“属城长吏”的底气,以及“以缯锦维舟”的资本。
从历史角度看,甘宁“以缯锦维舟”的铺张行径,与后世的石崇、王恺颇具相似之处。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一时轰动洛阳。
石崇是大司马石苞之子,家世殷富,然而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乃至官军扮盗,“任侠无行检”。可见游侠行径不分阶层,孤寒者可为之,富室、强族亦可为之。
甘宁出身豪门,却流徙辗转,飘荡半生,直至入吴后以胆烈闻名,遂为江表虎臣。
作为益州豪右之子,甘宁先后出任巴郡计掾与蜀郡郡丞,宦途一片光明。然而他不安现状,先叛刘璋、再叛刘表、又叛黄祖;仕吴之后依旧故我,不加收敛,“既常失(吕)蒙意,又时违(孙)权令”,乃至被时人视作“斗将”,完全不见昔日的干吏色彩。
显而易见,甘宁虽然“颇读诸子”,但他骨子里依旧是“挟持弓弩,负毦带铃”的放浪游侠。
他从诸子百家中汲纳的养分,全部用于军旅生涯,因此“开爽有计略”;而殷富出身养成的奢靡之风,又塑造了他“轻财敬士,厚养健儿”的侠士本色。
甘宁壮志所向,既不在案牍之上、亦不在仕宦之旅;而在关羽濑中、在皖县城下、在濡须渡口。在一次次的奋强突固中,甘宁亦无数次梦回少时岁月。
甘宁阻羽渡河,遂名此为关羽濑
合肥城下,“张辽步骑奄至”,在吴军“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的绝境中,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处险不变,豪气凌人。
《建康实录》称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冬,即合肥之战同年,或死于战创、或死于疠疫。设使如此,则甘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依旧维持了开爽奔放的游侠之风,在摧锋摇刃的绝境下,踏着累累白骨走完了最后的征程。
不必怀疑,若梦回昔日,甘宁依旧是那个“缯锦维舟”、“负眊带铃”的豪门游侠儿。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