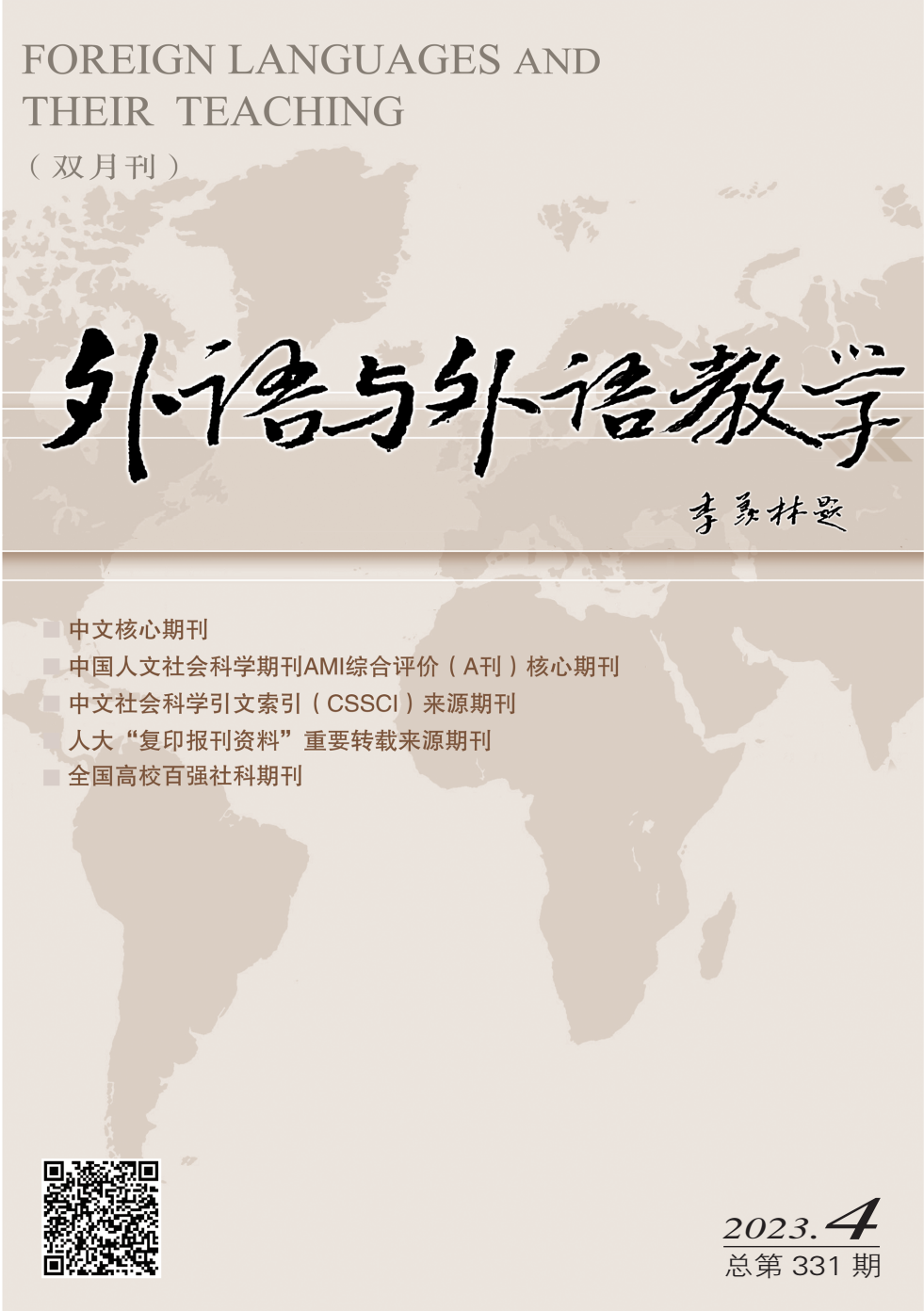
摘 要:1972年翻译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后,作为子学科的翻译史研究也逐渐登上舞台并吸引了诸多中外研究者的目光。在该学科发展历经半个世纪之时,回顾其发展历程,并指明未来走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从融通比较视角回眸了中西翻译史研究发展历程,将其分为起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并剖析各自特点,在此基础上从研究材料、研究主题和研究路径三个方面钩沉学科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系化史料、强化主题和深化路径等启示,以期推动翻译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史研究;学科史;历程、趋势与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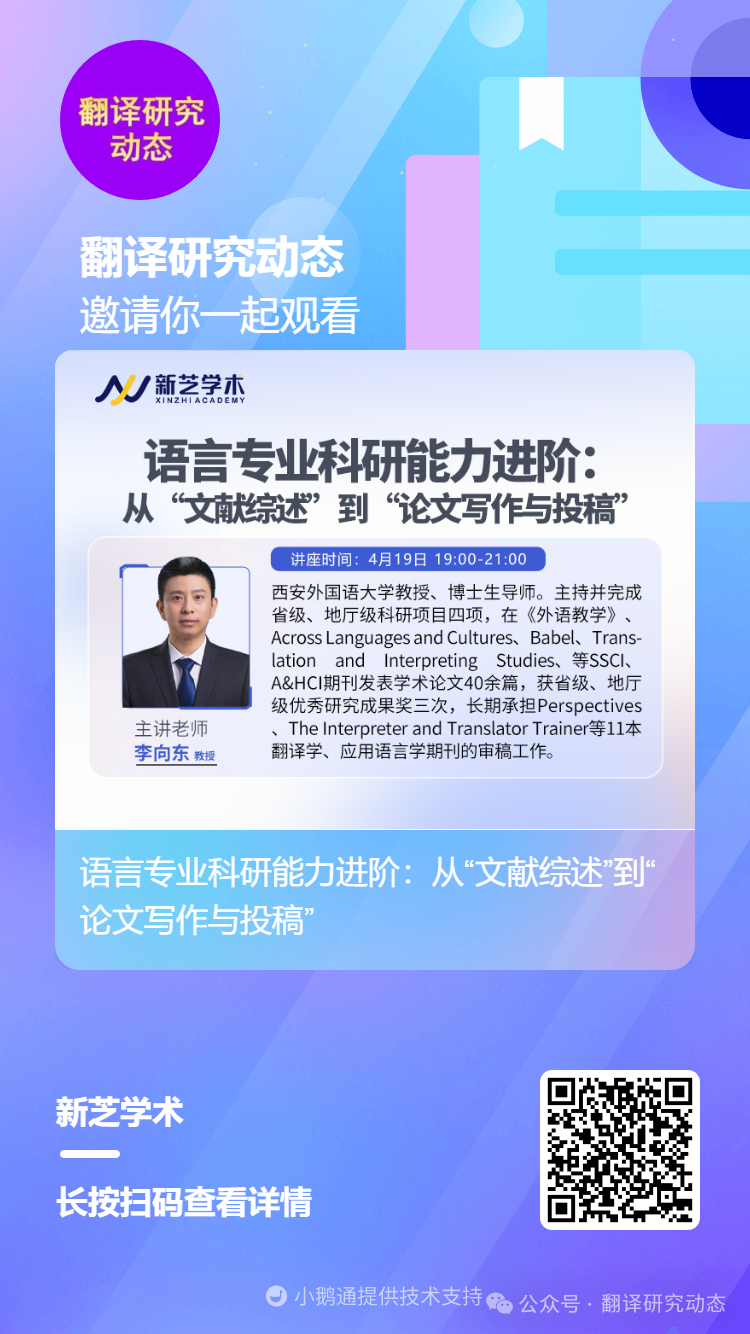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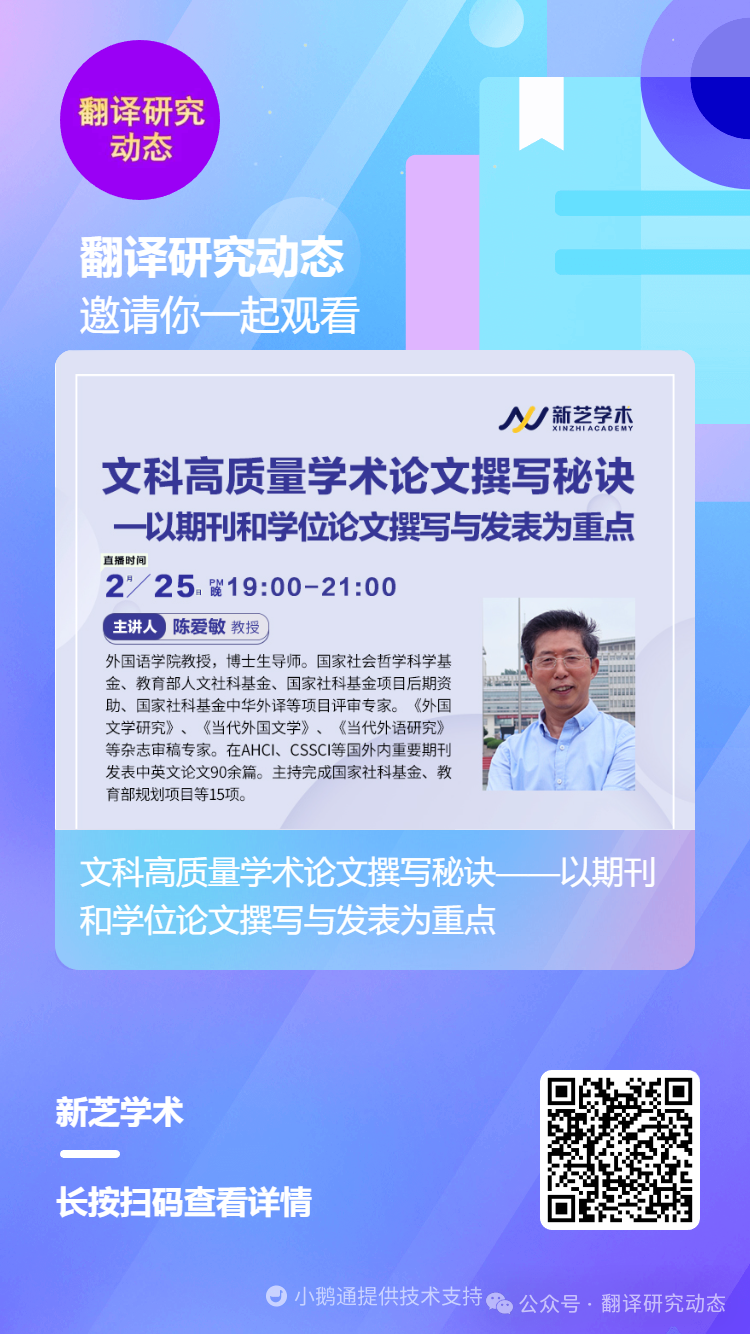

引 言
Holmes于1972年宣读的《翻译学的名与实》被誉为翻译学学科的“独立宣言”,此后学科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迄今为止翻译学已经走过半个世纪。在过去五十年中,作为翻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史研究,其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在此背景下回顾翻译史研究历程,并反思学科未来发展具有学科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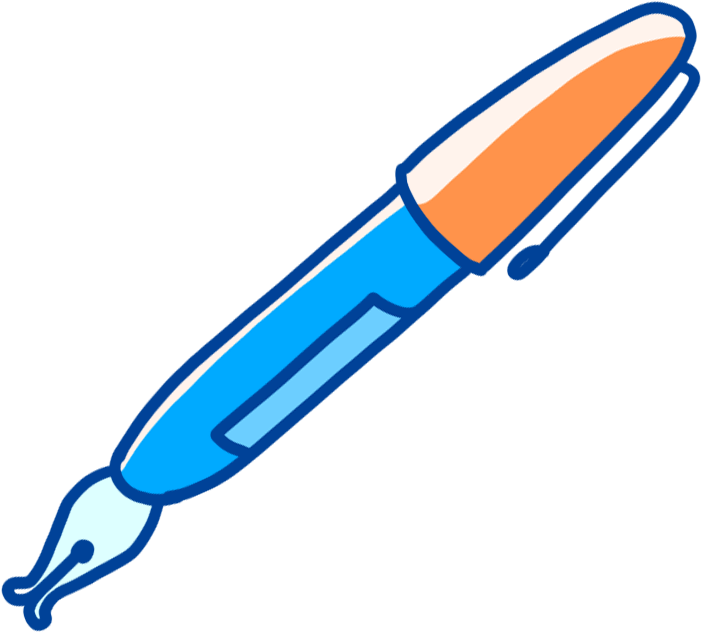
通常而言,历史学涉及三个层面,即历史、历史编撰和元历史(D’hulst 2010),其中第一个层次指涉历史的双重意义,包括“以合适顺序发生的事实、事件、思想、话语”以及“呈现这些现象的口头或者书面形式”(D’hulst 2010: 397),换言之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以及历史叙述者选择呈现出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记录者通常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第二个层次是“结合史学概念和方法以及研究对象所属的专门特长来开展的学术活动”(D’hulst 2010:397),也就是通过一定理论、方法或者视角来描述或编撰历史事件而开展的历史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书写历史的概念与方法的具体反思以及与上述概念和方法使用相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D’hulst 2010:398),即对史学研究的发展开展元层面反思,包括理论、对象、方法以及视角等。翻译史研究是介于历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学科,借鉴历史学三分法,包括翻译史事件、翻译史编撰以及元翻译史三个层次。其中,第三层次研究“回答‘怎样认识翻译史’的问题,是翻译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思考,它既是翻译史研究的最高形态,又是考察翻译史的总体指导思想和最根本的方法论”(黄焰结202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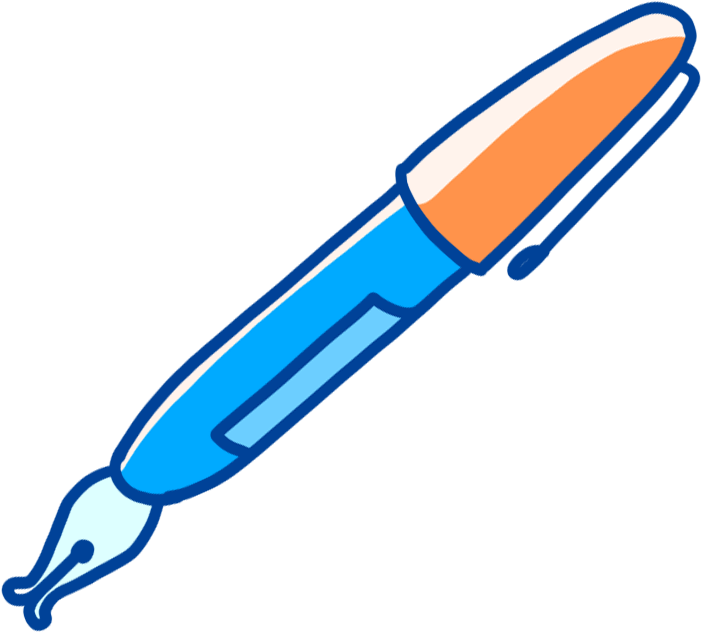
当前学界部分论文探讨了某一特定时期我国或者西方翻译史研究的状况,如文军和胡庆洪(2007)从发文统计、引用抽样、研究对象等方面回顾了中国百年翻译史研究(1880-2005),并指出“研究队伍仍需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翻译史研究仍需强化以及口译史研究需要拓展”;袁丽梅和李帆(2018)以2000至2018年间国内期刊论文为样本,统计分析了翻译史研究现状,发现研究在史实案例讨论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在翻译史理论建构以及新方法使用上依旧存在很大空间;王峰和陈文(2020)从课题、理论与方法三个层面分析了2005至2017年间SSCI以及A&HCI检索期刊的149篇翻译史研究论文,并对翻译史研究的走向提出了建议;孙艳和张旭(2022)基于9本国外翻译学核心期刊,考察了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译学界的发声情况,从数量、主题和视角三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措施。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通过著作或论文集聚焦翻译史研究,如《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邹振环2017)、《现代翻译知识史:溯源、概念与影响》(D’hulst & Gambier 2018)、《西方翻译史学研究》(谭载喜2021)以及《中国翻译史新发展研究》(段峰、罗金2021)等,研究分别从不同时期对中国或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翻译史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勾勒,并提出了拓展领域。

上述梳理体现了翻译史研究在近年来受到了较大关注,但也存在一定的扩展空间。史学研究在近年来提出要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进行综合对比,进而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夏伯嘉2020)。这对我们考察翻译史研究发展状况也大有裨益,因为当前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各国家或区域的翻译史研究现状,鲜有研究从融通比较视角审视中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随着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壮大,我国与外界交流日益加强并且译学成果国际化不断丰富(张汨2019),同一主题的研究并不是在某一区域的单向线性发展,而是彼此交汇、相互影响,因此除了单独关注中国或者西方的研究之外,还可以将中西翻译史研究置于同一背景下综合考察,从而“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新的研究问题,累积新的学术成果”(夏伯嘉2020:31)。综上,本文从融通比较视角钩沉中西方过去半个世纪翻译史研究的进展,在此基础上为翻译史研究更好地发展提出建议。
中西翻译史研究历程
本文主要考察过去五十年中西翻译史研究的发展,选取的时间节点为1972年至2022年,主要原因有二:就西方翻译学研究而言,1972年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确立后,学科系统化建设得以展开,因此该年份具有学科史意义;对中国翻译学研究来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就逐渐参与到翻译学学科建设中,时间段大致与翻译学在西方成为独立学科相近。由此,以1972年作为本研究的起点,符合翻译学在中西方发展的轨迹。纵观五十年的学科演变,我们可以将中西翻译史研究分为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现分别论述如下。
2.1 起步阶段(1972—1990)
Holmes在翻译学研究图谱中将学科分为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类,翻译史研究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在学科框架内部,但他充分意识到了从历史角度从事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其是研究的两大未来走向之一(Holmes 1972/1994),这可以看作过去五十年间翻译史研究发展的起步。随后,Steiner、Bassnett以及Newmark等西方翻译理论家在其出版的著作当中都或多或少提及了翻译史的相关论述(谭载喜2021),但大多是通过回顾式文献梳理记录翻译学学科发展历史。此阶段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基本和西方的研究路径相同,邹振环(2017)认为1984年是我国的“翻译史年”,主要标志是《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论集》以及《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的出版。从上述论文集或论著名称及其具体内容也能看出,其主要目的也是爬梳中国翻译史史料,进而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

由此可知,在翻译史研究起步阶段,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研究特点主要是以史料梳理为主,而理论化研究尚未真正开展。主要原因是学科建立初期,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如何进一步巩固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且在Holmes勾勒的翻译研究图谱中,翻译史研究还处于相对边缘地位,子学科地位尚未得到确立,研究共同体暂未形成。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的发生,研究视角逐渐被扩大至历史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及二者的彼此互动,中西方翻译史研究均出现了从传统翻译史学到现代翻译史学的转变(黄焰结2022),由此吹响了翻译史研究理论化号角。
2.2 发展阶段(1991—2000)
现代翻译史研究号角吹响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史书写问题。此间,西方翻译史研究出现了两本影响颇大的翻译史著作,即《译者的隐身》(Venuti 1995)以及《翻译史研究方法》(Pym 1998)。前者提出了翻译学研究中著名的归化和异化策略,而后者则是翻译史研究系统化思考,包括研究材料清单、作为研究中心的译者以及文化间性理念等。同时,中国翻译史研究也开始探索研究的理论化路径,其中王克非(1997)的《翻译文化史论》是这一阶段的扛鼎之作,作者虽未构建出翻译文化史研究框架,但提出的翻译文化史观对于思考翻译行为的历史文化意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标志着我国翻译史研究理论化的开端。当然,史料整理依旧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翻译史研究有Lefevere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1992)以及Robinson的《西方翻译理论史:从希罗多德到尼采》(1997)等,而中国翻译史研究则有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以及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1993)等。

通过梳理可知,研究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史料爬梳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中西方均开始有了理论自觉,相对而言西方在翻译史研究系统化方面走在了前列,开始探索翻译史书写的理论、方法和路径。在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至2000年,堪称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一个‘学术复兴’期,代表性著作的出版蔚为大观”(邹振环2017:237),由此新世纪初也可以看成是中西翻译史研究繁荣的起点。
2.3 繁荣阶段(2001—2022)
21世纪以来,跨学科成为了翻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而与之最为相近的历史学自然而然成为了翻译史研究理论源泉的重要汲取地,拉开了系统化和理论化探讨翻译史书写的序幕。具体来看,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探索,前者是对研究深化的综合性把控,如孔慧怡(2005)呼吁重写翻译史,尤其是要重视一手史料挖掘,并突破以文学翻译为中心的桎梏;Bastin和Bandia (2006)从多角度、多层面勾画了翻译史研究的未来走向;Rundle (2022)既勾勒了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又从理论、路径和主题等板块点明了研究进路;黄焰结(2022)从史料、方法和视角等方面论述了重写翻译史的方法论问题,回应了王克非(1997)和孔慧怡(2005)对翻译史书写的思考。微观层面研究表现在如何借鉴各种史学理念开展研究的方法论文章,如微观史(Munday 2014;张汨2021)、口述史(McDonough-Dolmaya 2015; 张汨2022)、全球史(袁丽梅2019)等。此外,这一阶段研究繁荣还体现在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对此议题的集中反思,如Meta于2004和2005年分别推出的“翻译的历史和历史的翻译”和“历史视角”主题专刊、Translation Studies2012年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专刊以及The Translator2014年的“翻译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等,上述研究大大丰富了理论视角,突出了跨学科特点。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西翻译史研究展现出理论化特点。一方面得益于中西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另一方面也说明翻译史子学科地位于21世纪初确立(Rundle 2020)之后,学科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提升。
中西翻译史研究趋势
从上述三个阶段各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中西翻译史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西方领先、中国追随到中西互鉴、齐头并进的历程。史学研究拓展有赖于材料和议题,并且不同研究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或路径(邓小南2009),故本部分从材料、主题和路径方面呈现出中西翻译史研究发展趋势。
3.1 研究材料日益丰富
材料或史料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纵观过去五十年研究的发展,研究材料呈现出价值彰显和类型多样两大特色。

起步阶段的翻译史研究大多聚焦文献编撰和汇集,为研究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很多研究发现译者所言和所译存在矛盾之处,这是由于“引用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孔慧怡2005:12)的倾向所致。正是因为意识到此桎梏的存在,一手史料对翻译史研究的价值逐渐彰显,如Pym提及翻译史研究要注重“补充性文献、出版商目录和个人文档等”(Pym 1998:55)一手资料,而Munday (2014)也强调一手文本材料对描写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手史料对研究的价值逐渐得以彰显,这一研究理念的转变也促使各种材料先后进入研究视野。

以往研究常基于来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对比来归纳翻译策略,但近年来翻译手稿、出版商合同等一手史料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就翻译手稿研究而言,Toury (1995)可谓先锋,但之后对此类史料的关注在国内外均处于万籁俱寂的状态,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重回研究视野,如Munday (2013)指出了翻译手稿对译者决策研究的价值并以几位译者的手稿做了个案分析。无独有偶,许钧和宋学智(2013)在同一年也发表了傅雷翻译手稿研究的论文,这体现出我国学者在史料敏感度方面不亚于西方,且随后翻译手稿研究在国内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冯全功2022)。除了翻译手稿类的前文本(张汨2021)之外,由于副文本概念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出版合同(Paloposki 2017)、译者通信(许诗焱、许多2018)、翻译笔记(鲍德旺、梁佳薇2019)等史料也先后进入了研究者视野,丰富的材料也带来了多元的研究主题。
3.2 研究主题逐渐多元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虽然中西方翻译史研究主题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但是双方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逐渐开始关注非文学翻译史,而西方则将目光投向了口译史。

中国翻译史研究长期以来关注文学翻译,翻译史重写的向度之一是摆脱以文学翻译活动为中心的书写模式(孔慧怡2005),在翻译史研究系统化开展之后,研究重点转向了非文学或科学翻译史。事实上,随着明清两朝逐渐与西方频繁交流,诸多西洋科学技术先后通过翻译传入我国,而18世纪初始,我国的科技典籍也开始通过英译向西方传播,这一过程中很多传教士、汉学家和中国翻译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成为了21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对象。如《上海翻译》2016年以来一直关注非文学翻译家的研究,大大促进了科学翻译史研究的发展。此外,方梦之和傅敬民(2018)还专门论述了科学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与中国翻译史研究关注个体译者不同的是,西方翻译史研究的走向更关注翻译事件及其影响,尤其是在21世纪以来口译史成为研究焦点并在口译研究中引发了“历史转向”(Pöchhacker 2016),在主题上与战争史和军事史紧密结合,而这也和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历史状况相关。近年来,以纳粹集中营口译史(Wolf 2016)、西班牙内战口译史(Baigorri-Jalón 2021)、亚太战争口译员审判史(Takeda 2021)为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研究不仅关注口译过程的语言转换决策,更将着眼点拓宽至军事战争背景下译员角色和职业伦理等内容,尤其是对当前口译行业的启示,大大拓展了研究主题。
3.3 研究路径趋向综合
基于史学研究内部和外部路径的区别,翻译史研究也可分为内史和外史,“具体表现为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和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前者“以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为主线,惯于使用演绎逻辑”(屈文生2018:833),而后者“讲究史料、史论和史观,研究者对史实和史料高度敏感,惯于使用归纳逻辑,惯于从细节出发,研究常受某种史观指导,力求使作品能够再现史实并形成合适的史论”(屈文生2018:834)。换言之,内部研究主要是从翻译史本体出发来探寻问题,外部研究则是借鉴史学研究理论或方法来开展翻译史研究。

虽然翻译史是翻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但研究关注点仍是翻译行为,所以人物、策略、思想或标准等内部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这一方面在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体现尤为突出,对鲁迅(骆贤凤2021)、傅雷(宋学智、赵斌斌2022)、许渊冲(张智中2022)等翻译家思想挖掘持续深入,但研究逐渐摆脱了主观评点模式,更关注翻译思想生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意义。

从外部路径看,微观史、全球史等史学研究路径逐渐被借鉴来丰富翻译史书写,从而促进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如近年来微观史吸引了中西研究者目光,除了方法论层面探讨(Munday 2014;张汨2021)外,还出现了针对朝鲜停战谈判(Wang & Xu 2016)、波多黎各殖民时期翻译政策(Mellinger 2019)以及翻译家理雅各(丁大刚2021)的扎实个案研究。可见以微观史为代表的外部途径,成为了翻译史研究拓展的方向。
中西翻译史研究启示
上述总结不仅反映了五十年内中西翻译史研究的趋势,同时还可以籍此反思未来研究的走向,以促进学科良性发展。
4.1 系化史料
上文提到,一手史料价值的彰显使手稿、合同、通信等先后进入翻译史研究视野,但今后在史料方面应该持续系化,具体包括史料深挖与系统整理。

一手史料可包括翻译手稿、合同材料、日记回忆、口述访谈(Munday 2014)等。当前翻译手稿研究日臻成熟,而其他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尚需加强。日记或回忆录(Wolf 2023)在近年来颇受研究者青睐,因为在政治史、精英史为主的传统治史模式下,翻译活动由于地位不高而历史记录相对较少,故译者日记或回忆录能够更完整地还原历史场景。另外,很多历史事件不一定会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因此研究还可借助口述史料来丰富历史细节。当前“口述成史”已经得到了史学研究界的普遍认可,口述史料在翻译史研究中的潜力还有待发掘。

除了深挖史料外,如何有效利用各类材料也是研究需要深化的方面。史学界“孤证不立”和“多重证据”理念体现了史料互证的重要性。因此,未来中西翻译史研究在史料方面还应该系统化和档案化。近年来“翻译档案”在国内外逐渐受到关注,通常包含个人、机构和官方收藏的一手史料(Atefmehr & Farahzad 2022),其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来源,也是研究的对象”(Cordingley & Hersant 2021: 9),即除了借助已有档案馆或图书馆开展研究外,还可思考如何将涉及具体翻译家或翻译事件的文献进行全盘梳理,包括前文本、文本、副文本和元文本等并建成翻译档案,形成系统的史料链,从而奠定更扎实的史料基础。
4.2 强化主题
近年来,中西翻译学研究的交流互鉴也为翻译史研究主题深化提供了参考。研究主题的强化一方面要摆脱文学翻译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需要将目光聚焦更“隐身”的参与者。

口译史和非文学翻译史将继续成为研究主题强化的方向,尤其是中国口译活动源远流长,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严重滞后,学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有相关呼吁(任文2018)。但迄今为止似乎仍是呼者众而践者少,这可能是因为口译研究在国内相对小众,而在国外则有Interpreting和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等口译研究期刊,国内则可由相关研究者引领推出专栏。另外,中西交流历史上诸多非文学翻译事件,往往也会对国家命运或国际关系产生重要作用,如不平等条约的不对等翻译及其对于中英和中美关系之间的影响(屈文生、万立2021),而西方教育学(刘洋、文军2022)和社会学知识(马士奎、徐丽莎2017)传入我国也离不开翻译助力,因此可以关注非文学翻译史事件来拓展主题。

在聚焦参与者方面,翻译档案在国内外呈渐兴之势。目前研究通过手稿考察译者自我修订,但新近研究开始基于译者与出版商通信探究(Paloposki 2021)翻译过程中译者建议译文以及校对编辑的决策,从而拓展了研究主题。以此为鉴,今后研究主题除了关注译者外,还可将目光投向编辑干预、出版商审查等过程中不同参与者,他们相对译者而言身份地位更为隐蔽,其心态及与译者互动关系可以作为考察内容,进一步突显翻译史研究以人为本理念。
4.3 深化路径
跨学科是翻译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研究深化的最佳路径,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或视角能够进一步推动翻译史书写,具体可以从相邻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取益。

首先,历史学是翻译史研究关系最紧密的学科,因此可以继续借鉴史学理论或视角开展研究。近年来,文化史、社会史、概念史、知识史等话题在史学研究中蔚为大观,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其对翻译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例如,文化史的复兴出现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口号与探索,其包含的书籍史进路在近几年颇为成熟,将其引入翻译史研究的呼吁已经出现(Pickford 2022; Hermans 2022),但具体方法论层面的系统论述尚未出现,因此可以思考其在翻译史研究中的理论价值。此外,翻译史研究的“比较性决定了翻译史研究自然要借助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文化媒介学、文化变异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邹振环2017: 309),因此研究还应该与相关的其他学科进一步融合,如法律翻译史研究不仅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法律术语及内涵,还需要结合跨语际转换、权力斗争和历史文化影响等内容进行拓展,研究涉及法律学、翻译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只有做好学科交叉,才能更好地实现翻译史书写的目标。

其次,近年来数字史学的发展蔚为大观(陈志武2016),这也符合当前文理交叉与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要求,故翻译史研究者还需要将视野投向自然学科,尤其是当下流行的数字人文领域。数字人文对翻译史研究影响最显著的当属语料库的使用,但当前大多为涉及两种语对的平行或可比语料库,如能根据不同研究主题建立多语种多类型语料库甚至历时语料库,则能够有效提炼翻译规范的演变,从而为翻译史研究的结论带来更扎实的数据证据,甚至激发新的研究问题。此外,基于数据库的网络分析和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虚拟现实,在史学界也已有较多讨论,但其在翻译史研究中的运用还未有触及,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过多展开,但学界今后可以深化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翻译史研究。
结 语
翻译史研究业已成为翻译学的一门子学科,并在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史料范围不断扩大、主题关注逐渐多元,且书写路径日益丰富,中西翻译史研究也从“西领中随”到“中西互鉴”。鉴于翻译史研究依旧是翻译学的一门年轻子学科,研究的后续发展有赖于史料系化、主题强化以及路径深化,以便更好地促进翻译史研究的整体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张汨,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史。
文献来源: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23年第4期,第98-106 + 149-150,参考文献部分从略,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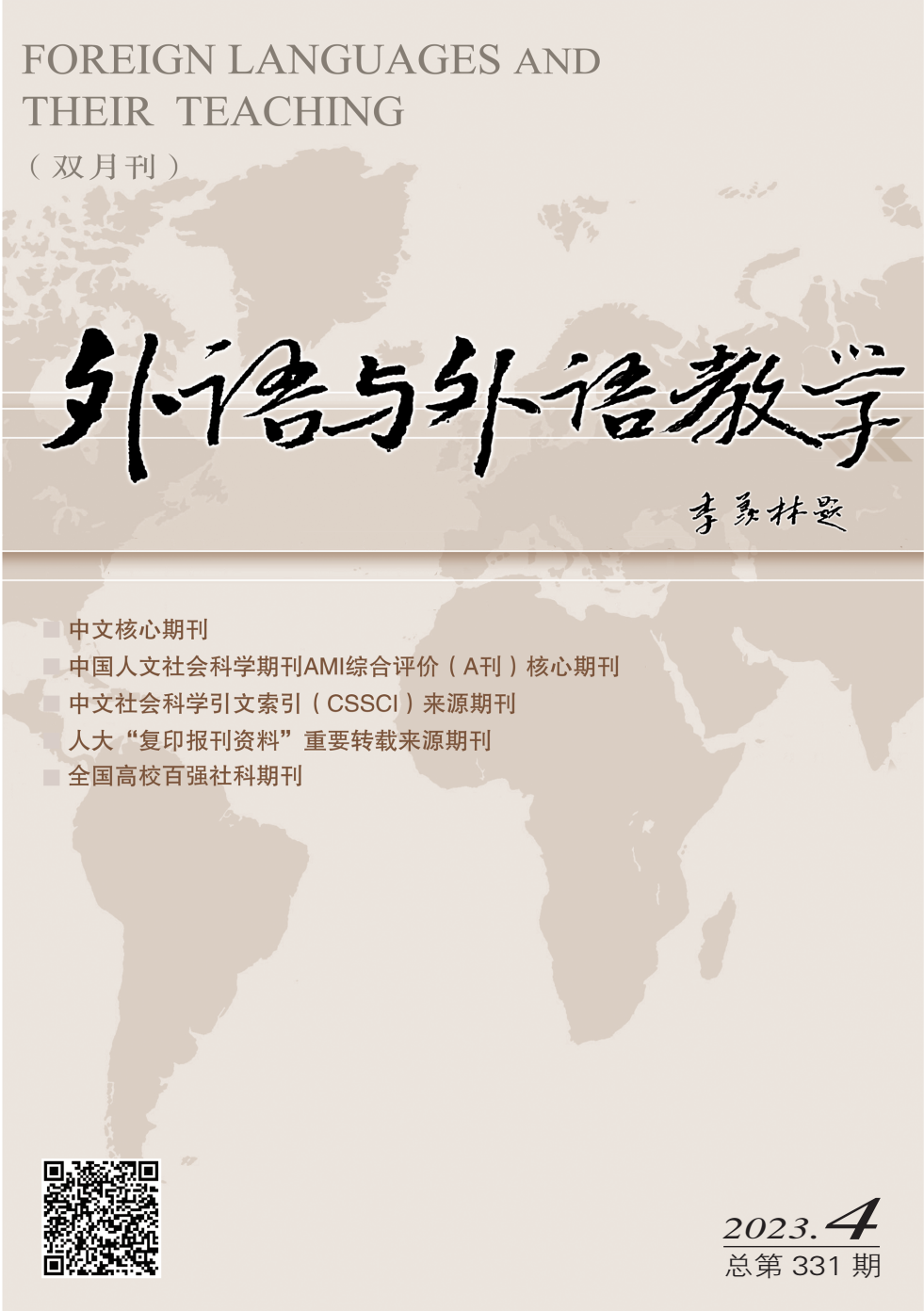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