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自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步入正轨。三年来,有关历史政治学的理论范畴、经典范式、研究议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都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晰和明确的界定。本期小惑为大家介绍历史政治学研究路径下,史料的定位与用途。
内容提要
本期siri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政治学下“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意味着什么。第二部分讨论历史政治学应当如何处理史料。第三部分为大家介绍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学者们关于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与总结。
一、“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
杨光斌提出,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仅仅是观念,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就是本体论性质的历史政治学。那么,“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历史本体论”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毫无疑问,“历史”的存在给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清楚地表达,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失去历史,人就是“牲口”,“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但是,过度的“历史感”是有害的,“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追踪了新权力技术的诞生,历史化了曾自然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监狱统治机制。在此书中,除了权力谱系学的方法得到展示,福柯还谈到 “当下的历史”的概念:“如果人们想要用当下的术语写过去的历史,那就是时代错乱;如果人们想要写‘当下的历史’,那就不是了。”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福柯建立了“启蒙”与“我们自身”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了一种针对我们自身的当下现实及其历史谱系的新批判哲学。福柯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概括为“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他对历史分析方法的创新——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在后期被吸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的本体论”这一新的批判哲学当中。考古的方法成为福柯批判哲学的核心方法。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充满了诱惑,时间与空间框定了人类存在的限度,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将精神寄托于自然本体、神学本体、道德本体、历史本体乃至情感本体,然而时至今日,有限理性下,这些本体论都已呈现出论证的不可能。从尼采到福柯,无不启发我们去思考“我们当下是什么?”,使我们对各种当下主体经验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反思,同时又强调历史的限度。尼采强调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福柯则根本将“我们自身的历史的本体论”作为现代性的批判态度。经验的历史不再自然而然成为先验形式,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意味着一种存在,一种需要经过因果论证与现在进行关联的存在。
二、如何运用史料
在考虑如何运用史料之前,非常有必要回顾政治与历史的纠缠。在19世纪以前,政治现象始终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中心,19世纪英国史学家弗里曼的名言“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形象地概括了政治史在西方传统史学中的核心位置。兰克学派重视政治史和对档案材料的研究,主张探寻一种“客观的历史”,集中关注“国家与政治”。20c20s末,兰克学派陷入了危机。年鉴学派的学者们掀起了批判将历史与政治挂钩的浪潮。他们反对事件史,倡导“新史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年鉴学派还提倡“总体历史”观念,相信“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不仅关注浮现于表面的历史事件,更关注整个社会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从而发掘历史深处的深层逻辑。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年鉴学派发生了多次革新,新史学阵营内部也无法政治现象和政治史研究自身的重要性,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美、英、法等国逐渐兴起了新政治史的研究潮流。
(一)认识史料
时间、人物、事件和史料是历史学的四个基本要素,其中史料又是最值得重视的要素。注重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也是19世纪以来职业史学家普遍强调的职业素养。以德国历史学家、著名的现代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即兰克学派)十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兰克对历史编纂和历史学的首要贡献, 在于开创现代史学研究的首要科学方法——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史料),连同史学方法的一项重大创新——对史料的批判性考证。或者说, 他创立了以同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史料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准则, 并且创立了史料之科学考证的基本方法。受其影响,傅斯年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中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他极力号召人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兰克首创的史料现当代搜集方法的首要原则, 是要尽可能搜集存于公私档案储存场所或储存机构的原始档案史料, 即人们一般所称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对于未经刊印的史料, 即上述档案史料, 首先要了解它们是否已经解密, 亦即是否已经可以查阅(在许多情况下是指了解其中哪些已经可供研究者使用, 哪些并非如此) ; 就那些已经可以查阅的档案史料而言, 需要注意和详细得知它们的保存、集中和分类情况与查阅手续等问题。
如果在所要研究的课题领域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课题领域已经有了有关的目录学编纂, 则往往需要熟悉有关的目录学。史学家唐德刚曾受命为张学良做口述传记,其第一件事便是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
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史料加以考证。史料的考证, 意味着鉴定史料的性质和它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考证可分为外形鉴定与内容鉴定两方面: 前者即校勘和辨伪, 或曰“文本批评”, 后者则是考订史料所述史实是否可信和是否精确, 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信和精确。
史料的形式大致可以可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三大类。文字史料是最基本的史料载体,大体又可分为口述史、回忆录、日记书信、年谱和档案几种,对这些史料的阅读、使用、比较和分析,是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仅大致地按照其原始程度(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其重要程度) 的递减顺序排列, 历史政治学研究可使用的史料可分为以下六大类:(1)未刊档案史料;(2)已刊档案史料;(3)官方史;(4)公开文件;(5)回忆录、书信集、已刊日记、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等;(6)第二手资料(书籍和文章)。在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之下,官方文献资料是政治史的重要研究对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民间文献研究一度大规模进入史学工作者视野。总之, 除尽可能多地收集和使用档案史料这一基本原则外, 其他大都必须依据具体的研究任务所处其中的具体的史料情势。
另一个可喜的变化,甚或说“史料学革命”的内容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与数字化技术的革新,各类文献、档案、图像乃至于文物、遗迹、遗址,以不同方式加以数字化处理,如光盘、电子版图书、史料数据库等,数字化的史料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这也开启了量化历史分析这一重要分析路径。数字化的史料为历史分析拓展了长时间维度分析的可能,同时也更便于跨国别、跨地域的资料搜集。根据当下数字化史料的特点,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最好能够利用历史数据库拓展材料的广度。史料类数据库相当丰富,除去如明代史料汇编全文数据库系统等文献资料的数字版,还有诸多例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华政的“中国治国理政历史案例库与数据库”等新建数据库项目。
尽管史料的重要性如此之高,但毫无疑问,史料并不等于史实。首先,相对于任何一段历史而言,史料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并且史料的选择、运用与阐释都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其次,“揭示历史规律”这样一种颇具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目标不曾消弥,诸多已经定评的“史实”不起查证,存在着大量的推导、演绎,甚至出现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
(二)“先归纳,后溯因,不演绎”的方法
政治学如何运用史料呢?有学者言,“历史学家还原历史,不过是试图在史料与史实之间拼接出合理的社会图景;政治学家解释历史,不过是试图在史料与史实之间建构起逻辑的理论关联。”
黄晨老师在一次线上会议中总结了理想的历史政治学的核心方法论:先归纳,后溯因,不演绎。归纳历史经验以确立因变量,在此之后溯因以寻找自变量。理想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应该既满足历史学的标准,又满足政治学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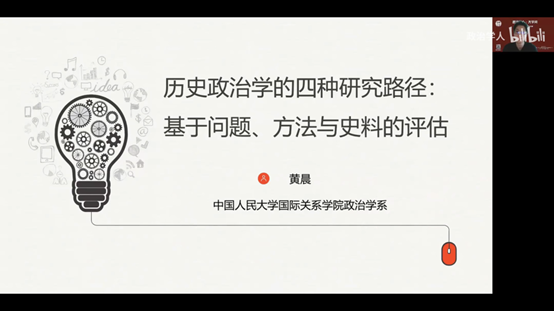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