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张仲民的专访。更多系列文章也会在文化频道陆续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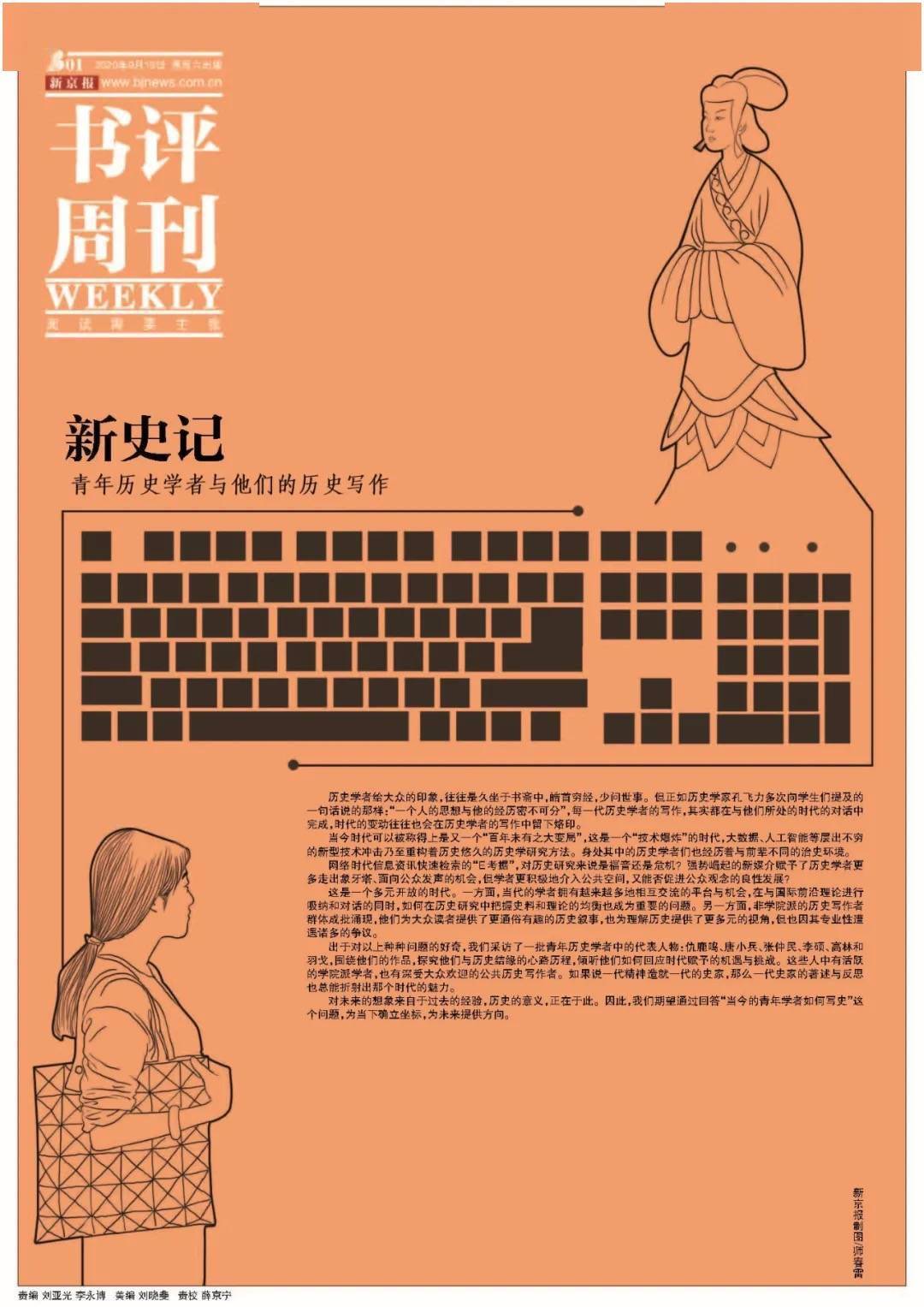
2020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
采写 | 刘亚光
“蜜蜂”的方法与阅读史研究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对于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来说,扎实的史料和适当的理论分析都不可或缺。但历史学界也不乏一些作品为了迎合理论框架而去“裁剪”史料,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也受到了许多的批评。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看来,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可能比不用理论大得多。
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经批评历史学者与社会理论学者看待彼此的刻板印象:“时至今日,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社会学家仍然是用粗鲁而抽象的行业黑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时空感;而在社会学家这边,传统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属于业余而短视的事实辑录者,缺乏体系、方法或理论。”
不过,伯克也承认,没有一个时期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的。尤其是自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一些新的转移,社会史、新文化史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断涌现,这些历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历史学应与其他学科展开充分的对话,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历史学者们借鉴,通过理论的烛照,他们辛勤搜集的史料似乎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对于不同的学者类型,弗朗西斯·培根曾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比喻:蚂蚁、蜘蛛和蜜蜂。蚂蚁重在搜集、搬运经验材料,而蜘蛛则永不停歇地编织着自己的“理念之网”。而对历史研究来说,一个学者仅仅具有“蚂蚁”式的史料功夫或是“蜘蛛”式的理论储备,似乎都难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按照培根的比喻,最理想的历史学者应该是“蜜蜂”:搜集“原料”的功夫了得,也懂如何加工,能实现理论和历史的完美结合。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现实往往不尽完美。理论如果运用得当,自然能点石成金,对解读史料大有裨益。但倘若使用不当,也可能“喧宾夺主”,出现对史料的过度解读问题。
这种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也十分显著地出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关注的“阅读史”领域中。从博士时期研究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开始,张仲民就开始运用“阅读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对读者阅读实践的考察,侧重于发现思想观念真实的传播与接收过程,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需要借助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帮助,张仲民本人也曾在论文中强调过理论对历史学者的重要性。然而,他也始终坚持“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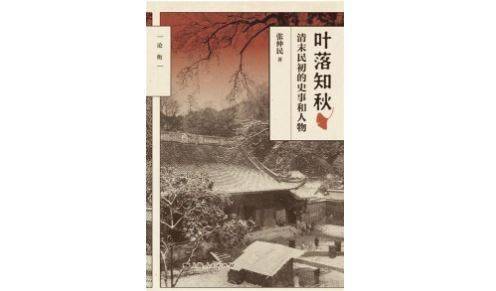
《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与人物》,作者:张仲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对话张仲民
新京报:你前几本著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和《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也都聚焦于近代中国的出版、传播与阅读体验。为什么会对阅读史研究感兴趣?
张仲民:我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阅读史尚没有太多人注意。当时大家都比较关注西学东渐史,背后的近代化关怀比较浓厚,关注的对象也以精英为多。我自己最初的兴趣也在此,后来在大量阅读报刊资料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一个比较少有人关注的选题,就是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征得导师同意后,就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尝试着跟国外的阅读史作品进行了一些对话,这个尝试现在看来是比较幼稚的。
这些年学习下来,个人觉得或可以这样看待阅读史研究。把阅读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就是关注书籍、报刊、图像等文类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广义来说,阅读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关注文本发生、传播的历史、被受众如何接受使用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常关注的是思想、文化、制度、事件等自身的情况是怎么样,却不太考察它们如何被大众接受、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又是如何被人们接受和表述的。
而阅读史把“受众”放在更关键的位置,这种视角颇让我心有戚戚,后来自己的一些研究虽然没有用阅读史的名义呈现,但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用传播的视角、接受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即关注所谓的“接受政治”问题,这让我对近代史的很多问题有一些新的理解。
新京报:围绕阅读史研究你发表了一些文章,在文章中你有提到,从事阅读史研究其实有许多的困难,是否可以再展开谈谈做阅读史的难点主要在哪些方面?现在相对于你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些困难有得到比较好的克服吗?
张仲民:较之于十几年前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阅读史研究现在已经慢慢热起来,不只是历史系,很多新闻传播系、图书馆学系的人都在做。但之前我曾遇到的那些问题和困难现在依旧存在。
首先是,阅读史是欧美学者引领的一股学术潮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更好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或随意牵强附会,依然比较困难。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或难点在我看来,是阅读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阅读史研究都存在一些障碍,就是受众通过阅读所引发的变化必须是有迹可循、有材料记载的,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又全部是建立在后设的立场和后天可以得到的材料基础上。
然而事实上,从我们个人现实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认知发生转变或剧变的时候,并非源于阅读外部世界的影响,却经常是发端于一些很偶然的突发异想或自省、顿悟、断裂。通常这样的瞬时变化是缺乏史料记载的,有时甚至当事者本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这个转变过程。这就给阅读史研究带来了挑战,如果只根据常规的史料呈现与后设叙述,我们的确可以建立一套比较具有连续性的受众阅读、接受与使用的系谱,但这样一种再现显然忽略了史料不存在或无法呈现的那些情况。这个瓶颈或许可以运用一些理论介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而很多阅读史的研究者也的确喜欢使用理论来弥补史料不足的问题,但根本上讲我觉得这个障碍还是没法克服。
青年历史学人“我在读”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 编,彭刚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此书是九位欧美一流历史学者的访谈录,编者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定,让九位学者现身说法,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与参考意义。”(张仲民)
新京报:这里其实涉及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理论似乎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历史学讲求“论从史出”,理论的过度引用也有可能导致论述并不很贴合史料反映的事实。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张仲民: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现)代化、传统、民族主义、社会转型、本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大叙述结合起来,而不去探讨这些概念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同自己具体研究的个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这就导致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选题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或研究旨趣大同小异,是在为理论或某些研究做注脚,难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同质化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如不用理论,不如将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表述方面。
简言之,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们才有更好与理论对话的基础。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比不用理论大得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概念被一些汉学家运用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国内研究者也跟风而上。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初曾红极一时的此类研究现在几乎不再有人看,被认为大有问题了。当我们占有了大量史料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时髦理论化选题本身其实大有问题,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新京报:相对于老一辈学者,青年学者拥有更多的海外交流机会,和西方理论的对话也更频繁一些,你说的这些问题在青年学者中是不是更突出?
张仲民:这个不太好下判断。现在固然有一些青年人包括青年学生喜欢援用理论进行研究,但一些早已成名的学者,甚至是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他们对理论的偏好程度和捕捉当前流行时尚或流行学风的敏感程度也非常高。这种情况部分原因的确可归因于海外学者,特别是海外汉学家的影响。他们经常回国交流,在国内演讲,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因为具有一定的身份优势与话语霸权,所以较易受到媒体关注和学术机构的领导重视,也更容易引起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历史研究者的追捧与效法。另外一些原因似也可归结于部分大众媒体、学术杂志缺乏自信,无原则追捧的结果。
作者 | 刘亚光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