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副教务长。张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客座研究员。本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刊发。

欧立德
张梅:尊敬的欧立德教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重要研究成果。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开始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的?又是如何投身清史这一研究领域的?
欧立德:我大学读的是欧洲史,硕、博阶段改学中国史。1979年邓小平访美,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那一年中美恢复邦交,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在美国较之前增多。坦率地说,在此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肤浅,可是因为我对语言感兴趣,先后学习过俄语和法语,不过觉得不够用,就想要学一门难度高点的语言,因为邓小平访美让我对中国产生兴趣,所以在1979年的秋季我开始学习中文。耶鲁大学历史系那时候有非常有名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他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我选修了他的课程,这是我学习的第一门中国历史课程。后来回耶鲁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我做了史教授的助教。那一年他的课有700多名学生选修,是当时全校选修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学习中文两年后,我先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去台湾读书进修,当时能够获准去中国大陆读书的机会很少,我当时去的是台湾大学史丹福中心,那里有专门给外国学生开设的中文学习班。后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教育部共同成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启动了中美双方的交流项目,我幸运地被选中,于1982年去辽宁大学学习一年。
我之所以对满洲或者说东北产生兴趣是因为之前俄国在东北一带非常活跃,我既懂俄语,又懂中文,认为一边用俄文的资料,一边用中文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辽宁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我完成了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如何看待和理解中俄关系的论文。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已决定将来要走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事实上,我选择研究清史也和我在沈阳的求学经历有关。那个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沈阳市内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和设施,而沈阳有自己的故宫、北陵(皇太极之陵墓)、东陵(努尔哈赤之陵墓),留学生去外面放松时就常去附近的北陵公园玩,我自然而然地对清史和满文有了一定的实地接触和了解。

沈阳故宫大清门
张梅:当您投身中国历史研究的时候,想您一定遭遇到了某些困难。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在开展清史研究的过程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有哪些?
欧立德:遇到困难肯定是有的,我当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我要研究的那个课题——八旗制度和它旗下的满洲、蒙古、汉军那些人,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研究。我的老师们对清初八旗是非常感兴趣的,但真正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包括史景迁、魏斐德两位老师在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是我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他那时候正忙于写作出版《洪业:清朝开国史》,所以清初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课题。他对八旗制度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是他知道八旗制度很重要,所以鼓励我进一步去了解。因为当时日本学者在八旗制度史研究方面是最强的,所以我当时考虑去日本。
另外,因为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必须要使用满文的资料,所以我在耶鲁大学读硕士的时候还选修了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的课,她给我的影响非常大。从1971年至1981年她一直在台北和北京的档案馆里搜寻资料,在此过程中她发现满文资料和中文资料其实并不重复,而在那之前,清史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满文资料和中文资料是重复的,满文是汉文的译本。她指导我去历史档案馆查找资料,并说一定要认真阅读满文资料,这是开展清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后来听从她的建议,在伯克利学习了两年的满文。到了东京后,我一方面继续学习满文和利用满文资料,另一方面开始研究八旗制度的历史。到了90年代,我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访问交流,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搜寻资料,这些资料是我后来写作《满洲之道》一书的基础。
张梅:对于清史研究,历史学界有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强调汉化的重要性;另一种则是以满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强调满族并未被完全同化。当前的中国历史学界普遍采用第一种研究范式,而在您的著作《满洲之道》和《乾隆帝》中,我注意到您将两种范式结合起来,那么,请问您如何理解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关系?
欧立德:你问如何理解满族史和清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从很早之前就注意到历史学界有这么一个分歧,不仅是中国学术界有这种分歧,在日本也是。日本有一个“清朝史”学派,还有一个“清代史”学派。研究“清朝史”的人注重研究清初,他们使用的很多都是满文的资料,他们的研究路径与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清史”的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近之处,关于这一问题我之前在我的论文里曾谈到过。而“清代史”的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史,特别是19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在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清朝史和研究清代史的学者们来往极少,彼此不参加对方的研讨会,在思想上也很少有什么关联,这跟中国国内的情况有些相似,尽管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当时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还没有流传到中国大陆,中国国内主要是研究清代史,以清代的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史为主。关于清代史的研究时段,学者们一般认为是从清朝开始到鸦片战争时期结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就是近代史的范畴,而近代史的研究则属于另一个方向,有另外的研究基金、另外一拨人在做这些研究,事实上,这种分歧对整个清代历史的研究非常不利。
在我看来,中国清代史的研究历来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因为汉族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在美国有很多人喜欢研究美国史,而对欧洲史、中国史不感兴趣一样——人们普遍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而非他国的历史,这是很普遍的。当时研究满族史的学者和研究清代史的学者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来往,这么说并不夸张!因为满族史属于民族史的一支,民族史和清代史是两码事。民族史的研究通常不会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进行而是在民族大学开展。我在中国大陆读书的时候,有两位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韦庆远教授。他是我当时的指导老师,也是明清史方面的研究专家;第二位是中央民族大学(当时是民族学院)的王钟翰教授。王教授也曾在哈佛读书,英文说得很好。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够迈进清史学界就是因为韦庆远和王钟翰两位教授,同时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华立、成崇德、郭成康等学者们的帮助,他们对我们这些来自美国研究清史的学生们当时都非常欢迎并鼓励支持。
在当时,我一方面参加他们指导的清代史的研究讨论,同时也和研究满族史的人,主要是王钟翰教授的高徒们尤其是定宜庄、刘小萌等学者经常探讨满族史的研究进展。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满族史和清代史在中国区分得这么开,现在想来,当时能让这两组人坐在一起研讨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不过我想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不应该把清代史和满族史分得那么开,要两者结合才有道理。事实上,我一直努力将这两者结合到一起,那时候刚好所谓“新清史”的英文著作开始出版,然后美国、日本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要想研究好清代史,不能不重视满洲人在其中的作用。之后,日本国内清代史和近代史两个学派的距离变小了,中国国内清代史和民族史两个学派的距离也变小了,而在美国研究清朝初期历史和研究清朝中期历史的距离也变小了。应该说,这一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产生了一些成效。
张梅:清朝政府给予满洲八旗以特殊的民族政策,用以维系这一族群的战斗力,却仍然不能阻挡满洲衰落和清朝灭亡的命运,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欧立德: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尽管清史研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感兴趣。研究清代史的学者们好像都有责任要去解释和弄明白“为什么清朝会灭亡”这一问题,当时不仅清朝灭亡了,而且整个帝制都消亡了。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过我相信,即使再过一百年也还是会有人继续问同样的问题。我能给的回答:我们都要努力适应当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来看清朝的领导阶层,他们在17、18世纪都能比较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环境上的各种变化,到了19世纪他们的适应能力好像已不如18世纪那样强,虽然他们也尝试过改革,但最终并没有完成,甚至到后来制度都已经不起作用了,政府也失去了有识之士的信任。在我看来,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人民的信心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尤其是在信息发达的时代。那么,为什么清朝会灭亡呢?主要是因为在一个正在转变的历史环境里它没有能够说服大多数的人来支持其统治。当时大家都能看到周围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可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对于清朝灭亡可从微观方面去解释,也可从宏观地角度去理解。从宏观上来说,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寿命,一旦它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八旗军旗式样
张梅:您关于清朝历史的观点与20世纪以来中国清史研究的主流论述并不一致,您试图从满族、从“他者”的角度来寻求问题的答案,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民族主义重新看待历史的路径,因为从满洲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清代历史,学术界称之为“新清史”。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新清史”?
欧立德:20世纪90年代末“新清史”出现于北美学术界,这派认为:满洲人的统治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汉化,而且因为他们保持了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因此,要理解满洲统治的重要意义,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满洲人是谁,他们的政治、军事、法律机构是如何运转,他们又是如何在这些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清帝国的复合帝制体系的。当然这里的帝制不能简单地视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传统的帝制,而是清朝政府专有的独特体制。在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满洲人的实践时,新清史不可避免会面临传统观念的挑战,那就是认为满洲人单方面被彻底汉化了。可根据我们的研究,尽管满洲人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尽管他们一直在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却不能说他们被完全同化了。也就是说,一直到清代末期,人们(至少住在大城市的人)都还很清楚,谁是满洲人,谁是汉人。
新清史的出现引起了许多新问题,作为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学者,如果要真正开展研究的话,必须在研究中使用满文文献,这种满文文献应该是原文,而不是译文,同样对蒙古语、藏语、察哈台语文献的使用也是如此。
如果清代历史研究学者们真的这样做了,就可以发现这种满洲特征或者说对满族特征的意识不只是在17世纪发挥作用,甚至到了18、19世纪,乃至到了辛亥革命都还在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把清朝皇帝不仅看作是一个汉人的皇帝,而且把他视为满洲人的大汗,乃至蒙古汗的继承人,对清代宫廷政治、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的分析将会有所不同。通过深入研究满洲统治下的清朝历史,“新清史”寻求的打破有关清朝历史的线性历史叙事,承认并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把学术探讨延伸到族群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与世界历史相关的领域,把满洲统治纳入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把清代历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张梅:这一研究理路促使您怎样看待现代中国的形成?
欧立德: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应该说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地思考现代中国形成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大家都这样说——满洲人经历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政治考验,在此期间他们受到汉人的影响都被汉化了,而这正是他们能够经受住考验,统治中国这么长时间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当时的想法是想了解这个汉化的过程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我很奇怪的是在清末的时候,有很多的革命家在他们的著作或是演讲里对于清代的宣传充满了浓烈的排满情绪,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提到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说满族人都被汉化了的话,怎么还会存在“满洲人”这个群体的概念呢?这是很让人不理解的,甚至有点悖论。我就是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才开始对“满洲人”的民族意识或者说族群意识进行研究的。可是想要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汉文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阅读他们自己语言写成的史料。研究到了后来,我又在想,如果我们把清代看作是一个帝国,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如果我们把这个帝国看成是满洲人的帝国而不是彻头彻尾被汉化了的满洲人的帝国,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是我在《满洲之道》一书写作基本完成之后才意识到的,不是我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也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
要知道,任何一个学者他在做个人研究的时候,都希望他所做的研究能让其他研究方向的学者感兴趣。比如,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到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做研究不应该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研究兴趣。我在研究八旗制度的时候有些方面的研究做得很具体,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八旗制度感兴趣。我更不可能期待所有人像我一样对八旗制度感兴趣,那我的研究为什么别人要关注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如果我们把清朝不仅看作是汉人的帝国,而且是满洲人的帝国,是包括传统十八省和周边其他领地在内的这么一个帝国的话,这好像和现代中国的形成有了关系。不用说,我不是第一个这样思考也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何炳棣教授就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和我的立场并不一致。现在多数中国学者也都已经承认清代的统一和现代中国的形成密切相关。
张梅:两者是因果关系吗?
欧立德:有没有因果关系,主要看你怎么看待“中国”这个概念。葛兆光教授在《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里曾谈到“中国”这个概念一直在变,宋代、近代、现在的解释都不一样。事实上,是否有因果关系,我觉得我们要研究清代人对“中国”这个词怎么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语境下使用,什么情况下不用?弄清楚了这些,我们才可以明确清代中国是什么样子;认清了清代中国,我们才可以说它跟20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关系。中国当前历史学界那种认为“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她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观点。在我看来,我们的责任是要在正确的语境中理解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对于那些看上去很熟悉、意思也很相近的术语我们要谨慎使用。我们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去作出判断,批判性地去思考这个满洲人统治的天下是怎样的天下,他们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在我看来,“中国”这两个字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符号。当然,在进行这一陈述的时候,我必须强调,我绝不是要否认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一中国领土上现存政体的历史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从学术思辨的角度来说,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与前人所说的“中国”不完全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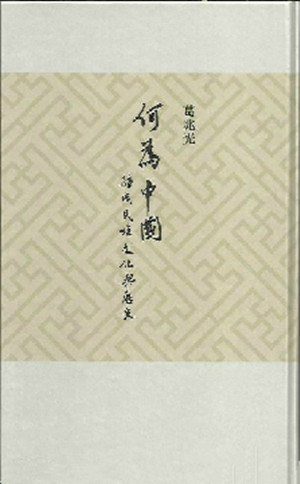
《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
张梅:如您所言,通过深入研究满洲统治下的清朝历史,“新清史”寻求的是把有关清朝的线性历史研究回溯到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的学术话语中,把满洲统治纳入到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域中,可是让我存疑的是,您的这种想法到底有多少可能性实现?您认为您现在所做的工作将会给世界历史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
欧立德:在美国大学的历史系,你可以看到学习美国史或欧洲史的学生很多,而学习其他国家历史的学生相对较少。在美国,历史主要是指美国史或者是欧洲史。事实上,传统的美欧知识分子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就像法国、德国和英国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不只是个简单的“过去”。可以说,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源自于黑格尔,马克思也接受了同样的立场。不过,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出现了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而不是从欧洲的历史经验建构出来的叙事标准看待中国的新趋向。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益明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学术趋势占据优势,已经在北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稳步确立,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历史经验在人类历史中重要性的普遍认知。
当然,这一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容易,因为在美国,一般学生还是很不熟悉朱元璋或者乾隆皇帝这样的名字。我想我们所做的这部分工作就是要使我们所讲述的清代历史能被其他历史学家(不管他们的研究区域或时段如何)理解,并和他们的研究关联起来,清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将清史与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的历史加以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称之为清代的这个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如何促成清朝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变,而且还可以重塑北美乃至全球学界对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认知。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