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这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就以一本《西方的兴起》赢得大名。2003年,他与其子著名环境史研究者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2011年引进此书,2018年推出的中文修订版,则更名为《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值此新书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小麦克尼尔,请他谈谈撰述此书的初衷与经过,以及他们父子对全球史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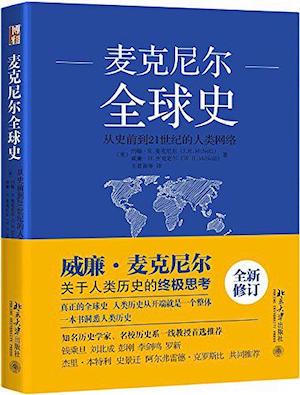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
您的祖父是一名历史老师,您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又是一名蜚声全球的历史学家,是世界史研究的先驱性人物。您选择从事历史研究是否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在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您觉得这种家学渊源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威廉·麦克尼尔,摄于2004年
麦克尼尔:没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历史学家。我祖父研究的主要是基督教会史,他是加拿大人;我父亲研究世界史(全球史),他们都很成功,写了很多书,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成为历史学家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家学渊源是一种优势,我比大部分其他孩子能耳濡目染更多。但也有一些劣势,因为我父亲很成功很有名,我常常被拿来跟他比较,可以说我还没有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但这也没关系。
我曾经努力学习其他学科,我在本科一开始学的是数学和物理,我也尝试过工程方向,但学得不太好,所以我直到本科最后一年才转向历史方向,因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你一开始不需要选定本科专业方向,你可以在中途选择,你可以改变主意。我就改变了主意,因此我较晚才决定要成为历史学家,但我很庆幸自己做出的选择。
如果说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他们的专注投入和勤奋。他们工作都十分努力,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职业道德方面的榜样。这大概是我从他们那里受益最多的,但肯定不止如此,因为我父亲是世界史学家,这影响了我的观念,有时使我也想成为世界史学家。
我们知道,写作全球史对历史学家的知识面的要求非常高。《麦克尼尔全球史》不仅涉及西方世界,还涉及诸多非西方世界。这让我们很好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您和您的父亲是如何进行知识上的准备的?
麦克尼尔:我们所做唯一的准备就是多年来的历史阅读和教学。我们合写这本书时,我父亲的阅读积累和教学经历已逾五十年,我也有二十年的经验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准备。我也努力学习了我父亲不太熟悉的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洲史,他不太了解非洲史,我的优势在于我曾在大学教过几年非洲史,这增进了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这就是准备工作了。
我们能够读到的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历史著作,有不少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您和您父亲写作的这部世界史来说,你们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来写人类历史的呢?现在回看这部已经完成的著作,您觉得你们对这一点完成得怎么样?
麦克尼尔:我不确定,我尽力规避了,但是很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偏见,因此尽管我尽力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但也许在某些方面并未做到,肯定有一些非洲、亚洲的历史学家会反对我或我父亲所写的内容,觉得这本书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也是事实,但同时我要说,我和父亲都做出了努力。如果你将这本书中涉及欧美历史的页数与涉及非洲、南亚和东亚历史的页数相比,就会发现此书并未过分强调西方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自己数过每一页,但我认为情况大致如此。我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努力在于尽力公平分配读者的注意力,使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所占篇幅大致平衡。
您父亲在其回忆录《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中说:“40年后,我的儿子和我编制了一部修订的、校正的和浓缩版本的人类历史。不论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一生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可见,您的父亲对《麦克尼尔全球史》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也是他世界史著述的封笔之作。他曾说起,这本书的写作缘自您的提议,那么,您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呢?您觉得这本书与其他世界史著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您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
麦克尼尔: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这一想法,我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即将迎来第三个,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我需要更多的钱,所以我就想,如何赚更多钱呢?我可以写本畅销书。我之前写过几本书,但它们是学术专著,《人类之网》不是学术专著,更像普及读物,这是我写书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与我的家庭环境也有关,那时候家里有小孩,我无法继续写之前那类作品。之前我写作时会在海外待一年到一年半,泡在档案馆里。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在四个国家的档案馆里工作过,耗时约一年。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去了六个国家,离家一年半。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得写另一种可以在家完成的书,我不能去档案馆,只能参考二手来源、出版资料。写这本书时,我的研究是在图书馆完成的,没有离开家乡。这就是我制定这一计划的两个原因,都与我的家庭情况有关。
我可以跟你聊聊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我父亲住的地方离我有五百公里远,我们每周通过邮件联系,不是电邮,是传统纸邮,因为我父亲更喜欢写信,虽然他后来学会了发电子邮件,但他还是更喜欢写信,我保留了所有往来信件。我们的通信持续到2000年,那时我们基本完成了全书。他先写完了他的部分,因为我还要照顾家庭和上课,没法写得像他那么快。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全天都有空写作,所以他比我早完成,然后我们交换所写部分,对对方的部分进行修订,有时我们会争论最后的呈现方式。我一年至少去看望父母三次,每次去就会和父亲长时间讨论写作计划,也会具体到某一句话的遣词造句,这就是我们的写作过程。最后一部分是与出版商交涉,这一块基本是我在负责,因为谈这些事情用电邮更方便,但我父亲不喜欢用电邮。
关于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的篇幅几乎短于任何一本世界史书籍。其次,它有一个主题,即标题中的“人类之网”,对人类社群不断增强的联系的探讨贯穿了每一章节,所以这本书并非想要详细阐释某地的历史,而是试图表现地区之间的联系史,所以我认为它有多数世界史没有的主题。
我对这本书整体来说挺满意的,其中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些妥协。我们写作时争论过,并且各有胜负,有时互相让步,有一些部分我并非全然满意。我现在在写另一本世界通史作品,已经快完成了,我是唯一的作者,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不用妥协。但我对这本书的满意程度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了。
您和您的父亲选择以“网络”(web)作为贯穿整部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能否请您谈谈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您的父亲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种比旧有方法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我们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麦克尼尔:因为我觉得“网络”一词展现了地区和社群间的交互联系,我选择该词后,我父亲也立即同意了这一选择,因为我们写作时,电子互联网还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新事物。互联网象征着人群和社群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所以该词在当时十分恰当,现在我仍然认为它展现了这种联系关系。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变革来自这种联系,所以当个人和群体接触到新的思考方式、新技术,可能还有新的疾病时,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思维和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联系常常是人类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因此这本书和我写的所有史学文本都强调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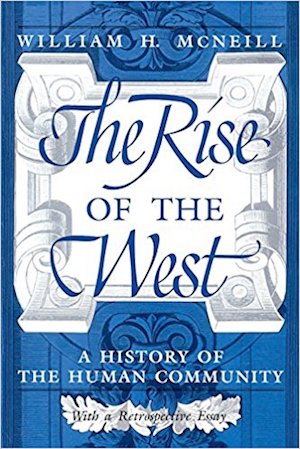
The Rise of the West(《西方的兴起》)
我父亲的那句话是指他自己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书,即《西方的兴起》,这是他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同意,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西方的兴起》很少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尤其是前哥伦布时代的拉丁美洲,即西班牙人到达那里之前,我们合写的这本书对这些地区的阐释要好得多,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更好的原因之一。第二,这本书对网络和联系的探讨更明确、更清晰、更有力,《西方的兴起》就略逊一筹,尽管我父亲在《西方的兴起》中就思考过社群联系,但比起这本书还是有不足。
具体到“网络”这个概念本身,您觉得推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有哪些?
麦克尼尔:有好几种,有些是无意识的人类行为,带有偶然性,一些社群间的联系是偶然形成的,并非人为,一个例子是生物交流,比如天花怎么就传到了日本,没有人有意这么做或想要如此,但天花就传到了日本,这是偶然事件,是网络构建的途径之一。此外,人类也有许多有意建立起来的社群联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商业联系,为了经济利益寻找贸易伙伴,所以历史上很多网络是由商人建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丝绸之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此外还有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例子,有海上的、陆上的,它们共同组成了社群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在扩展联系网的背后也有政治动因,比如帝国的建立,随时间流逝建立更牢固的统治,但也有僧侣和传教士建立的独立的文化联结,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五百年前访问印度的僧侣。佛教的引入改变了中国,这与政治扩张无关,与商贸也只有微弱的联系。这些是网络构建的其他方式:经济、政治和文化。
更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个文明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麦克尼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被提及很多次的汤因比,他写《历史研究》时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几类不同的文明,我记得他一开始列出了二十一种,后来这个数字又有增长。我认为这不是了解人类历史最好的方法,如你所知,我强调联结性,否认文明之间是独立分离的,至少一般来说是这样,因此“独立的单个文明”这一概念在这本书中出现得很少。如果完全按我的想法来写,它的比重还会更少,实际上我完全不会使用这一概念。我自己并不将历史看作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等的集合,我认为它是一系列人类社群的联结,所以我也不太接受“文明”这样的概念,它们常常限于精英文化,很少提及普通的村民、牧人等等,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印度或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只是进行无意义的分类。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觉得这种分类很有用,但它们主要用于理解精英文化,社会最上层百分之一的人,他们能识文断字,了解宗教传统等等,这一分类对理解大众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倾向于弱化单个文明的重要性,很少使用这一术语。
如果不使用这一概念,那您在书中如何区分不同的文明?
麦克尼尔:我会用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等表达,避免“文明”这一概念,但我父亲对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就比我高得多,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不是在说日本文化就跟印度文化一样,远非如此,两者差异很大。在本书中,我们首先会从地理和生态方面描述某一地区,然后很快涉及更多方面,如经济、宗教。有人可能会说你综合了这些方面,就是在描述某一文明,但我不会这么想,这本书的网络联结视角没有忽视不同社群和文化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史学专门化和碎片化的时代,您怎么评价《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种史学上的宏大叙事对历史学、历史学家乃至历史读者的意义?
麦克尼尔:我倾向于这么想:所有历史学家应该从事不同规模的研究,这包括了细节化的地方研究,有历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其他历史学家从事更宏观的研究或是全球研究也很重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应该覆盖所有地理规模。我常说这跟地图制图很相似,描绘北京中心城区的地图很有用,能展现很多有效信息,比如每条街道;但它无法展现北京与其他亚洲地区的关系。这时就需要另一幅地图,有时甚至需要地球仪来展现大洲之间的关系、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巨大的地图,因此我眼里历史跟地图类似。我们需要小范围的地图,也需要大范围的地图,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宏观历史学家,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微观历史学家,但作为整体,我们要研究所有规模的历史。
您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够读懂这本书吗?对世界史而言,您是否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
麦克尼尔:是的,更多的普通人读懂这本书,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说这对我,比对我父亲要重要得多,部分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她不是学者,喜欢阅读流行小说,她总是对学者式的自负不屑一顾,包括我父亲的,她更像个普通人。我在写了两本学术专著后,希望其他作品都通俗易懂,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懂里面的用语、概念和论点,我觉得这样更“民主”。我觉得每个人都懂一点世界史很好,如果懂很多就更好了。但事实上,我也知道这不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历史,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所以这不会很快实现,但若实现,世界会变得更好。
您现在将更多精力放在环境史的相关研究上,世界史研究对您的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麦克尼尔:我研究环境史差不多三十年了,环境史和全球史是我的两个专业领域,这两个领域有许多交叉共通的部分。我有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全球环境史的,试图全面地梳理地球上的环境变化问题。其中一本书针对二十一世纪,另一本研究的时间段则是1945-2015年,我很快就会再出版一本全球环境史的专著,范围是十九世纪。这两个学科有很多交互的机会,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气候变迁的进程常常发生在全球性的范围内,几乎不会仅限于单个国家,因此环境史在性质上往往是跨国的,甚至全球的。例如,你想充分了解大气层的历史变迁,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含量的上升,你只能将它视为全球性的现象,否则无法理解。
那么,目前仍有很多学者研究世界史吗?世界史的前景如何?您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吗?
麦克尼尔:我只能从美国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太了解。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且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映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史研究越来越热的主要原因。尽管没法下定论,但我认为这一趋势仍将继续,我也认为在某些方面全球史研究会越来越简单,因为现在通过电子媒体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二十年前,你要撰写全球史专著的话,必须接触到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现在这一点就没那么重要了,因此现在研究全球史的门槛降低了,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
在《人类之网》中译本修订版中,书名翻译为“全球史”,您如何区别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概念?
麦克尼尔: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我用这两个术语表达同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有一些人坚持两者的差异,认为全球史针对的只是现代时期,学术界意识到“全球”的概念之后。比如说,两千年之前中国没人知道南美洲的存在,南美洲也没人知道中国的存在,有些人就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有“全球史”。因为人们需要意识到“全球”的存在,“全球史”才得以成立。但我不同意,我认为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术语可以相互代替。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您父亲说这是一部全球范围的“极其简短的历史”,您为什么希望它尽可能地简短呢?
麦克尼尔:一开始我想将此书命名为《全球简史》,但出版商说,这个题目不好,你得换个题目。我希望它尽量简短主要是因为我希望更多人来读这本书,我想效仿刚去世的英国学者史蒂芬·霍金。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时间简史》,那是一本宇宙史。我想如果霍金能用两百页写了一部跨度达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史,那我也能用两百页写一部世界史、人类史。它的跨度最多也就二十五万年,但我没能成功,这本书超过了两百页,部分原因是我“聘用”了我父亲跟我合写,他写的一些章节比我们预想的长,所以这不是一本“极其简短的全球史”,但它是一本“全球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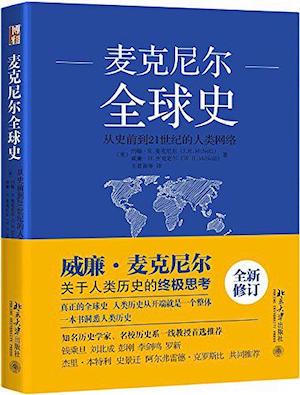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