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鹏

汤姆·霍兰(章静绘)
汤姆·霍兰(Tom Holland)是谁?
估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在漫威电影宇宙中饰演蜘蛛侠的那位英国帅小伙。而另一位汤姆·霍兰则是英国作家、通俗历史学家和翻译家,贵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他的作品《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和《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在中国的世界史读者当中的声望,恐怕不亚于蜘蛛侠在漫威粉丝当中的知名度。他的《千禧年:世界末日与基督教世界的铸造》全景式描绘了公元1000年前后一两百年时间里欧洲的全貌,《剑的阴影下:争夺全球帝国的战争和古代世界的终结》讲述了伊斯兰教发源、阿拉伯帝国兴起的故事。《埃塞尔斯坦》则是一部传记,传主埃塞尔斯坦是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孙子,第一位统治整个英格兰的国王。另外,他还翻译了一部古典名著,希罗多德的《历史》,由企鹅出版社推出。喜欢看BBC等英国电视台制作的历史纪录片的朋友,肯定会熟悉这个灰白头发、清瘦而风度翩翩的老帅哥,以及他那“咬牙切齿”、每个辅音都极其清晰、每个元音都特别饱满悦耳的英语RP口音。
霍兰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在英文和拉丁文两门专业获得优等成绩(即所谓double First)。他的历史著作都面向大众,取材并不稀奇,也谈不上有学术创见。但同一个故事让不同人来讲述的话,效果很可能大相径庭。通俗历史作品非常考验作者的材料选取剪裁能力以及文学功底。霍兰擅长凝聚戏剧性,很会营造扣人心弦的气氛(也许与他经常给历史纪录片写稿有关),辞藻华丽,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2018年9月,霍兰在伦敦接受了本次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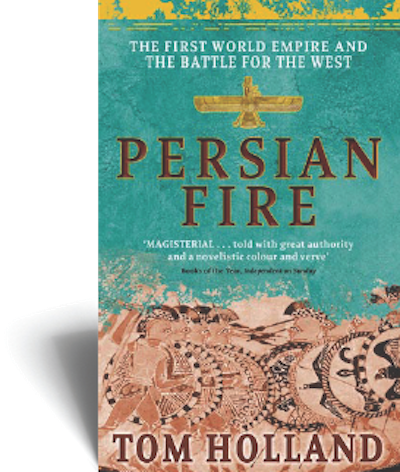
《波斯战火》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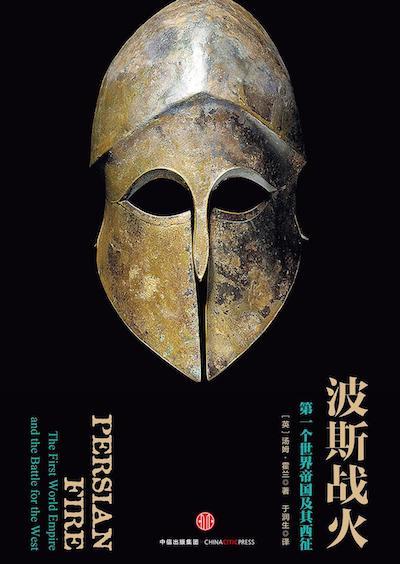
《波斯战火》中文版

《卢比孔河》英文版

《卢比孔河》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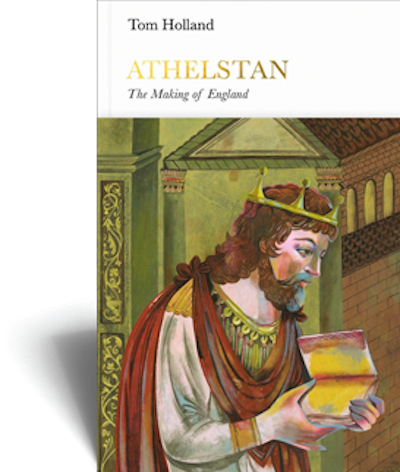
《埃塞尔斯坦》英文版
您在剑桥学英文和拉丁文,后来如何走上历史写作的道路?
霍兰:我在中学就开始学拉丁文。在那时,学习古典语言已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你有时间学习翻译维吉尔,说明你不需要为了生计发愁。我觉得学拉丁文和学任何外语一样,最美妙的事情就是阅读文学原著,走到那些伟大作者的脑子里去。
我原想写小说。我写过几部小说,后来意识到自己永远不能成为优秀的小说家。我还认识到,在写作方面,最让我激动的是面对往昔。我觉得历史比小说更有趣。往昔的方方面面都令人着迷,尤其是古代世界,简直就像科幻小说。因为就像科幻小说的世界一样,历史也有让我们觉得熟悉的地方,但大多数地方都是陌生和新奇的。
在您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哪些学者或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您的文学偶像是谁?
霍兰:我最喜爱的两位作家是狄更斯和普鲁斯特。我曾野心勃勃地效仿他们,现在看来是不自量力了。
在历史作者当中,我非常喜欢芭芭拉·塔奇曼。她写了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书《八月炮火》,我读了可能有十遍。她的另一部作品《远方之镜》,关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其中有一章写黑死病通过热那亚商船从克里米亚抵达欧洲,所有船员都倒在桨座旁,腋下生出可怕的黑色肿块。这种描写极具震撼力。《远方之镜》我读了五遍。
我大约十岁、十一岁的时候读了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我,克劳狄》,从此对奥古斯都和他的家族的故事十分神往。格雷夫斯笔下的那些聪明而邪恶的女性角色特别令人难忘。格雷夫斯把克劳狄皇帝描写得很正面,而我在为写《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根据史料,克劳狄其实远远没有格雷夫斯写的那样善良。他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而且他可能是刺杀卡利古拉皇帝的幕后指使。
您最有名的两部作品《波斯战火》和《卢比孔河》都与古典世界有关。您还翻译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作为科班出身的古典语言学者,您做这样的翻译工作是怎样的体验?
霍兰:我们可以说希罗多德发明了非虚构写作。当然他写的很多不可思议的奇闻怪事,我们今天知道是虚构的,但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认为那是虚构的。他明确表示自己在转述自己的亲耳所闻。有意思的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存在。他对印度很感兴趣,但说印度之外就是沙漠,再往外就是一片虚空了。他也不知道不列颠的存在。他说:“有人告诉我大洋上有岛屿,但我不知道,我没有遇到过那里的人。”你看,你们中国和我们英国都受到了希罗多德的蔑视。
希罗多德的《历史》卷帙浩繁,是古希腊最长的散文作品。希罗多德也是我的文学偶像,他是我读过的第一位古典作者。我对他爱得如痴如醉。《历史》我读了很多遍,在我的一生中,它一直是我的慰藉。他对万事万物都抱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所有人、所有事都让他兴致盎然,包括山川河流、岩石、蛇和大象等等。翻译一个人的作品,就好比和这个人结婚。与希罗多德结婚和生活,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译完《历史》之后有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相比之下,我就不是很喜欢修昔底德,他的文字比较枯燥。他没有幽默感,不懂得女人、美酒和生活的美妙。修昔底德当然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希罗多德更有趣。
您的《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一书详细描写了从奥古斯都开始的罗马帝国最初几位皇帝,即尤利乌斯-克劳狄家族的统治。提比略、卡利古拉和尼禄三位皇帝对贵族元老千方百计的羞辱和压制,是个人的暴虐和具体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始终如一地逐渐摧毁共和国机构,实现从元首政权到东方式专制转变的“大棋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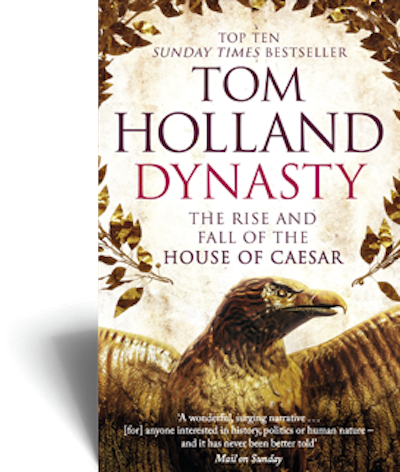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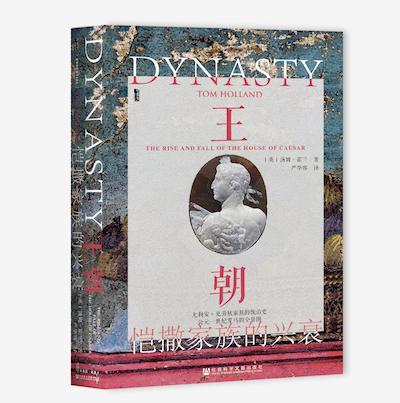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中文版
霍兰: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斗争与意识形态无关,不是左右之争,不是政党之争。争斗的焦点其实是政客展现自己,或者说争夺和行使权力的风格。贵人派(Optimates)和平民派(Populares)都是权贵,但贵人派追随古老的政治传统,遵守传统的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的作风是精英主义的,自命为传统的捍卫者。平民派政客则直接呼吁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熟悉他们的生活与喜好。
恺撒属于平民派。他出身豪门世家,却能用劳动人民熟悉的方式讲话,懂得他们的心声。
奥古斯都是个天才,把上述两种政治传统融合起来。他向广大民众赠送面包,穿着朴素,喜欢戴一顶破的旧帽子,经常去竞技场观看群众喜欢的比赛。所以群众爱戴他。但他掌权之后,在元老院也游刃有余,(假装)尊重共和国的传统,尊重那些出身贵人派的元老。他的厉害之处就是混合了贵人派和平民派的政治传统。
但他的继承者必须在两种传统当中选择。提比略在思想上是贵人派,他蔑视平民,拒绝为了向平民邀宠而举办角斗士比赛。所以他不受群众欢迎。但他得到元老院的尊重。他有点像约翰·麦凯恩,是个战争英雄。精英阶层会尊重这样的人。
卡利古拉就像特朗普。他懂得,可以通过羞辱精英阶层来获得群众的欢迎。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小心地避免得罪元老院,维持着“元老院的地位与皇帝平等”的假象。卡利古拉则想方设法地羞辱和压制传统精英。人民看到精英受辱,都很高兴,都喜爱卡利古拉。就像今天很多美国人喜欢看到特朗普羞辱有权有势的美国自由派精英一样。
克劳狄的做法是对卡利古拉的反拨。克劳狄是学者,对古老的传统感兴趣;并且他的形象不佳,瘸腿且口吃,没有吸引群众的魅力。所以他的政治作风更像贵人派。
尼禄则是彻头彻尾的平民派。他不仅从平民那里获得支持,还亲身去做平民喜欢做的事情。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参演一部戏剧,扮演弑母者。他参加赛车,弹奏里拉琴。如果放在今天,就相当于参演一部好莱坞电影,参加F1方程式赛车,以及举办歌星演唱会。这太让人震惊了。如果美国总统做这些事情,我们会怎么想?里根曾经是演员,大家一直拿这个取笑他,觉得这是令人尴尬的事情,觉得他不靠谱。尼禄后来被推翻并自杀,他的历史声誉就是经典的昏君。《新约·启示录》里带有数字666的野兽很可能指的就是尼禄。但尼禄受民众爱戴。他死后很多年里都有人给他的墓地献花,还有人弹奏里拉琴,COSPLAY尼禄,仿佛他是猫王。
我读《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的时候觉得其中一段特别有意思:“图斯库斯街是伊特鲁里亚人曾经聚居的地方,还有亚非拉加街。在很多罗马人眼里,罗马城的多元化代表了全世界对罗马之伟大的顶礼膜拜,多元化也是新生力量的源泉。但也有一些罗马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只要这些移民最终能变成罗马人,接纳他们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野蛮习俗,用他们的迷信去污染正派的公民呢?”帝国初期的罗马城让我想到今天的一些全球化城市,比如纽约和伦敦,以及这些全球化城市正在面临的与移民和宗教相关的问题。您写这一段的时候在考虑当下的问题吗?
霍兰:可能有吧。我把古罗马和今天的纽约、伦敦或巴黎相比。古罗马距离我们今天非常遥远,但从某些角度看,又不遥远。因为我们西方人经常把奥古斯都当作榜样和蓝图,就好像秦始皇始终在中国人意识的背景里。中国的版图经历过扩张和收缩,统一和分裂,但始终存在一种延续性。如果欧洲的历史走向和中国一致,那么今天的欧洲就是一个单一国家,大家都说某种形式的拉丁语。但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在它废墟之上崛起的新格局和以往大不相同,所以我说罗马帝国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
罗马在国际化程度方面很像今天的纽约或伦敦。罗马帝国包罗万象,接纳和包容各种民族、宗教与文化,吸收形形色色的移民。就连罗马的始祖埃涅阿斯也是个移民。你知道他是从特洛伊来的。罗马城建立的时候,罗慕路斯欢迎任何人加入。最早的罗马城居民包括很多罪犯、土匪,然后他们强暴和掳掠萨宾女人。
美国是以罗马帝国为蓝本的,举个例子,美国的国会山(Capitol)就得名自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美国也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共和国。
您对奥古斯都的态度似乎很负面,比如说他是“恐怖分子”,说他的政权(至少在早期)是“收保护费的黑帮”“黑手党国家”。这些意象都非常生动,令人难忘。而颇有一些奥古斯都的传记家,比如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对奥古斯都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
霍兰: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遵照当时的标准。用二十一世纪的标准来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是荒唐的,所以我说早期的奥古斯都是“恐怖分子”,遵照的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标准。
罗马共和国的价值观是,任何人能不能长期垄断权力。所以按照当时的标准,奥古斯都的夺权是针对国家的犯罪。但你知道,历史上这样的强权人物通常就是这么做的。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按照共和国的标准都是罪犯。当时的罗马人评价他们所用的措辞,就像今天的美国自由派评价特朗普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对照。恺撒、奥古斯都和特朗普做的是一回事:绕过传统的精英机构,摈弃传统的办事方法。而恺撒和奥古斯都做的事情非常受民众欢迎。所以他们受到精英群体的憎恨。
西方长期以来有一种美化和歌颂奥古斯都的倾向。他给饱受战火摧残的世界带来了和平。他为罗马帝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无疑是西方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但在个人层面,他无疑是个混账。按照当时罗马的标准,他也是个混账。他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不是善良的人。也许要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就必须是坏人吧。而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成功之处有一方面就是他成功地隐藏和掩饰了自己恶的一面,而把自己打扮为祖国之父。
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新书《主宰:西方思想的诞生》?
霍兰:《主宰:西方思想的诞生》涉及的时间跨度有两千五百年。其中也讲到中国,比如天文学家和基督徒徐光启。有整整一章讲的是耶稣会士在北京的活动。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之前的作品。
你知道,我写过古典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古希腊、古罗马,还有波斯。我得出的结论是,古代波斯很可能是把东西方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文明源泉。后来我写了一本关于伊斯兰教起源的书《剑的阴影下:争夺全球帝国的战争和古代世界的终结》(In the Shadow of the Sword: The Battle for Global Empire and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我感到古希腊罗马和穆斯林世界的思维,与我所在世界(现代西方)的思维差别很大,我不禁开始思考:我的思维,换句话说就是西方的很多思维,比如伦理、道德、社会的组织方式等等,是如何产生的。我相信,现代西方的这些思维都来自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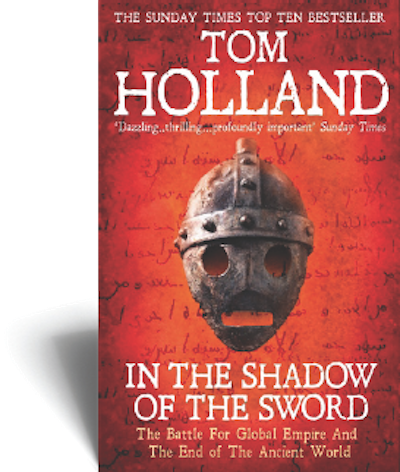
《剑的阴影下》英文版
我认为,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基督教是一种革命性思想。人类相信耶稣,这就是基督教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但基督教革命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对后世的影响。本书的论点是,西方的科学革命依赖于基督教思想。耶稣会士在中国取得成功,吸引到注意的原因是他们懂得宇宙运行的原理,他们能比当时的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日食之类的天文现象。中国人当然也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对天文现象的解释不如耶稣会士。
启蒙运动,也就是后来的自由主义的看待世界方式,将自己展示为对于基督教的一种反拨。但实际上启蒙运动是基督教思想的演化和新发展。另外,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在深层次上也是基督教的延续。世俗社会、政教分离这些西方思想,也都是从基督教发展出来的。今天的中国和日本都是世俗国家。世俗化社会、政教分离这些思想,是西方鼎盛时期,由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但西方帝国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架构,已经部分被拆解了。大英帝国已经解体,法国的殖民霸业已经消失。美国的力量正在衰减。但即便房子被拆了,作为建材的石棉仍然弥漫在空中。
今天的欧美知识精英都不是基督徒,他们蔑视基督教,觉得宗教是一种落伍、反动的东西,认为宗教是迷信,是一种浓雾,蒙蔽了人类,直到理性的阳光穿透了浓雾,也就是启蒙运动。这是西方目前的主流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启蒙运动是伟大的基督教思想演化的一个阶段,是基督教思想的延伸。这个演化从《福音书》和圣保罗开始。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改变了罗马帝国,改变了中东,影响远至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一直走到蒙古和中国。但基督教在西欧的影响最大,因为中世纪的西欧没有一个大一统的世俗君主,而拜占庭有皇帝,伊斯兰世界有哈里发。所以基督教思想在西欧被政治化。“洗礼”成为一种政治思想。
《千禧年:世界末日与基督教世界的铸造》讲的是十一世纪的欧洲,讲的是基督教如何成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它启发了很多后来欧洲人熟悉的东西,比如政教分离思想、天赋人权的思想、人类应当有专门机构来研究宇宙运转(也就是后来的大学),以及“如果别人不喜欢你的思想,你应当杀掉他”的思想。于是出现了烧死异端分子、十字军东征这些事情。对中世纪欧洲人来说,穆斯林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与基督教的世界观不容,于是欧洲人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占领了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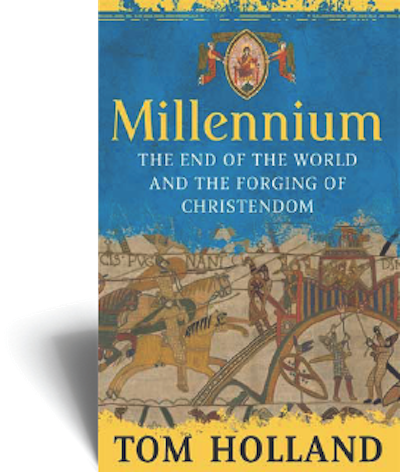
《千禧年》英文版
但后来,天主教会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机构,内部出现了病症,它变得具有压迫性。于是出现了基督教的第二次革命,即宗教改革。但是这样的话,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开始竞争和争斗,在《圣经》、真理的性质、上帝的性质等问题上互相争执。在这些争执的基础上,基督教发生了第三次革命,即针对基督教会本身的革命,也就是启蒙运动。从启蒙运动发展出了《权利法案》和血腥的法国大革命。
推崇宗教改革的新教徒有一种自负的观念,认为天主教是蒙昧的、腐败的、邪恶的;而盲目崇拜理性的法国革命者有一种自负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是腐败的、邪恶的。但实际上,新教徒和他们反对的天主教有很多共同点,因为新教是从天主教发展来的。而法国革命者和他们反对的基督教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从基督教发展来的。
今天的西方思想是上述三种革命——天主教革命(天主教的兴起)、新教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混合体。但这三种革命都源自基督教思想。这就是《主宰:西方思想的诞生》的主要观点。本书的目的是在历史长河中追踪思想的演化,就像追踪鸟类如何从恐龙演化而来一样。
除了写作之外,您还制作电视纪录片并担当主讲人。您的这两方面工作之间有什么联系?
霍兰:我喜欢写作,它给我一种自主权。但我也喜欢拍纪录片,那是团队合作的工作。我经常与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凯文·西姆(Kevin Sim)合作,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拍过很多获奖作品。他拍的一部著名纪录片《美莱村四小时》(Four Hours in My Lai)是关于越战期间的美莱村屠杀。他去采访了参与屠杀的美军士兵,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我和他合作了好几部纪录片,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努力寻找黑暗的根源。比如我和他合作的纪录片《伊斯兰国:暴力的根源》(Isis: The Origins of Violence),探索了伊斯兰国为什么如此凶残。为了拍这部片子,我们去了伊拉克的辛贾尔,去了雅兹迪人生活的地方。伊斯兰国曾占领辛贾尔,屠杀了雅兹迪男人,把女人要么杀死,要么掳为性奴。我们去的时候,伊斯兰国武装刚刚被库尔德人的民兵武装佩什梅格(Peshmerga)打退,我们去了屠杀现场的万人坑,就在伊斯兰国和佩什梅格激战的战场附近。我们在佩什梅格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来到现场,他们告诉我们,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就在几英里之外,所以我们必须在二十分钟之内完成拍摄,因为那里太危险了。我们没有充分时间去查看万人坑。我原以为那是墓地,死者已经被掩埋,然而土堆里伸出人骨和骷髅头、满是泥土的鞋子、用来蒙眼的布条。干枯的河床上散布着女人的衣服、更多的鞋和牙齿。那景象太可怕了。我们就是这样直击事件最黑暗的一面。
您参与拍摄和讲解了BBC纪录片《恐龙、神话与怪物》(Dinosaurs, Myths and Monsters)。在您看来,人类的神话传说是否都应当有理性的解释?动物化石对人类的想象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霍兰:其实拍那部片子时我特别想去中国,因为在恐龙研究这个领域,中国绝对是超级大国。中国出土了大量重要的化石。可惜因为经费限制,我没能去得了中国,只去了希腊和美国。
我觉得人类的神话传说并非总是能找得到理性的解释。很多传说中的怪物可能更多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某种当时人类还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比如古生物。不过,古生物化石的确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让古希腊人、古代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等民族创造出了精彩的神话。比如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发现了史前大象的骨骸。古希腊人认识到这是大象的骨骼,为了解释大象为什么到了萨摩斯岛,就编织出一个故事:酒神狄俄尼索斯带领大象从印度来到了希腊。
您的另一部纪录片《伊斯兰:未讲述的故事》(Islam: The Untold Story)引起了很大风波。这部片子的观点是什么,为什么引起争议?
霍兰:这部纪录片以我的《剑的阴影下:争夺全球帝国的战争和古代世界的终结》一书为基础。那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穆斯林对伊斯兰如何兴起的传统说法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神话,今天我们掌握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和阿拉伯帝国早期的很多史料其实出现得很晚。比如现存的最早的先知传记是在他去世将近两百年后写下的。《古兰经》作为一个文本,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记录、修改和编辑。我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激起了很多愤怒。我和电视台都收到了很多恐吓信。纪录片第一次公映的时候,还没有播完,我接到了伦敦警方的电话,他们说要来检查一下我的住宅,保障我的安全。
这有点像萨尔曼·鲁西迪的经历。
霍兰:鲁西迪写的是小说,我写的是历史。我不是穆斯林,我当然不会相信《古兰经》是天使直接启示给穆罕默德的。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自己安全。唯一有点担心的一次,是2012年美国籍科普特人纳库拉·贝斯利·纳库拉(Nakoula Basseley Nakoula)制作的电影短片引起了大规模的反美暴动,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身亡。伊朗的电视台Press TV把我们的纪录片和纳库拉的片子相提并论,说我们的片子是以色列或者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反伊斯兰阴谋。不过后来没出事。
现在写伊斯兰话题的书,真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倒不(主要)是因为有些穆斯林会生气,而是目前西方人很焦虑,害怕别人说自己敌视伊斯兰,害怕别人说自己不够自由主义。所以我们如履薄冰。
您的下一本书会写什么?
霍兰:我已经写过关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初期的书,我下面打算写一本关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书,大致从苇斯巴芗和提图斯皇帝的时代开始,涉及尼禄之后内战的“四帝之年”、庞贝城的毁灭等等。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