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成为官方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红船”自然不必多说,“巨轮”却也不单单是作为前者的简单对仗而存在:从“衰落的清王朝如破败的沉船”到“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再到“伟大的舵手”,自近代以来,“航船”已然被中国社会赋予了一种国家的象征意义。事实上,这种象征意义正体现了航船,或者说航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特殊地位:列强自海上乘船而来,并沿海沿江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中西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学习与抗争也由此而起,在此过程中航运既是列强“在华势力扩张的模式之一”,也是“中国主权与外国主导之间长期斗争的领域”,更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域”(002)。易言之,航运问题或可作为一面“镜子”,供当代学者检视“近代中西两个世界相遇的宏大进程”及其影响。

其实去掉腰封之后颜值会高很多
而美国学者罗安妮(Anne Reinhardt)的专著《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构建(1860—1937)》(以下简称《大船航向》),正是对这面“镜子”的一次积极运用。作者以近代中国的轮船航运体系(包括航运权、航运网络、航运公司以及作为社会空间的轮船)为切入点,通过梳理1860年到1937年间中国领土内航运事业的诞生、发展与转型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尝试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社会思想及国家地位的动态变化,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印度航运的比较,在全球史视角下重新检讨了“半殖民主义”这一略带“古早味”的历史概念。
作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修订后的作品,《大船航向》遵循了相当严格的学术规范,并利用了大量的未刊档案——中、英、印三国档案的比较研究姑且不论,仅就国内档案而言,从地理上来说,本书关注的领域横贯整个长江水道,加之在论文撰写的21世纪初,历史档案的数字化进程恐怕也才刚刚起步,故而作者在中国大陆的查档之旅也不可避免地要重走一遍从上海到重庆的万里长江路了,其辛苦可想而知(只是不知道作者从重庆到上海有没有突发奇想坐一下船2333)。就全书的章节安排而言,由于各章标题中存在时间与主题相互交织重叠的情况,难免让人有混乱之感,所幸其行文实则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前四章聚焦于晚清中国的航运发展状况,分章讨论主权(第一章)、产业(第二、三章)、轮船空间(第四章,时间下线顺延至1925年)三大主题;后三章则关注民国前25年的航运事业变化,并具体分为北京政府的无秩序时期(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的秩序重建时期(第六章)和轮船空间在1925年后的新变化三个具体部分。
政权、主权与航运权
与同一时期略稍后发展起来的铁路、航空运输相似,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船舶航运(本书主要指内河航运)这一近代交通运输方式也具有“舶来品”的性质,是1840年以来域外输入的产物;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相对于铁路、航空技术导向的“舶来”性质(即对于中国而言从无到有),近代航运在中国生根发芽则颇类似于银行、纺织等商业或轻工业领域,经历了一个驱逐和消灭本土原生行业,并取而代之的历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美船只利用《南京条约》及其补充规定赋予的特权(悬挂外国国旗的“洋船”在某一通商口岸缴纳进出口关税后,得享有在中国内水其他港口的纳税豁免权),非正式地成为中国沿海(乃至沿江)贸易的承运者(称其为“洋倒爷”恐怕也不过分)。这一对条约特权的“灰色运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及其附则《长江各口同上暂行章程》(1861)实现正式化,并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由于天国政权与清廷的相互封锁,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成为了这一时期长江航道上唯一能够享受“航运自由”的势力)的考验得以完全击败中国原生的沙船航运业,成为“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航运网络”的直接“起源”(023)。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
7.8
程麟荪 / 2021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与近代航运业在中国“开疆拓土”的经历类似,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驱逐中国传统钱庄、票号的“殖民历程”,这与航空、铁路、电报等跨越性技术在扎根的过程不同。
由上述可见,在1842到1864年的近代航运网络“草创”过程中,主导因素并非西方轮船的技术优势,而更多的是条约特权赋予“洋船”的经济和安全优势。然而随着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航运网络向中国内地的进一步扩张并遭遇清廷基于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厘金收入造成的打击、华洋民间冲突的风险以及对清王朝主权的破坏,具体可参见041-044页)而对这一扩张所进行的阻击,轮船的技术优势却又被西方用来为自身的扩张提供辩护,并借此将清政府的反对标识为一种“保守主义者抵制技术进步”的态度。考虑到这一“19世纪60年代的扩张主义话语”(045)很有可能构成了至今仍相当流行的现代化史观的源头,不得不说真是颇为讽刺。而从实际情况的发展来看,这种话语背后的扩张主义也确实取得了相应的优势地位:
1860—1911年,清政府力图扼制外国航运的增长,而列强却迫使清朝让予越来越多的航运特权。(023)
然而,这种逐步性的航运权扩张却因清政府的垮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遏——1910到1020年代的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呈现出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尤其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急剧下降,导致西方失去了维护航运特权以及推动航运扩张的单一谈判对象。换言之,“1911年后,条约体系依然稳固,但消失的——尤其是1916年以后——是一个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条约条款的中央政府”(057)。因此,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尽管因战乱与割据的影响,条约体系赋予外国势力的航运特权在效力方面得以进一步扩大(即“更有用了”),但受到同时期有效谈判对象缺失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崛起,这一特权的进一步扩张已然失去先前的条件。而1927年后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重新统一,但其秉持的民族主义信条使中外谈判的主题转变为了航运特权的“收回”问题,从而使外国在华航运特权迎来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虽然特权的真正废除还要等到全面抗战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收回航运权”问题上,主权与政权(控制力)之间的张力导致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国民政府尝试通过外交谈判收回航运权的过程中,名义服从中央,实则自行其是的川军军阀刘湘以向华资轮船公司(即下文提及的民生公司)提供政治和资金保护,并以政治手段向外资轮船公司施压的方式,在长江上游实现了实质性的航运自主。然而其更具对抗性与“非规则性”的策略在取得实际成果的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给南京的外交解决路径造成困扰,甚至更进一步地对其权威性造成了伤害。
纵观全书,政权、主权与航运权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实际上构成了《大船航向》考察近代中国航运发展史的一条主线:中外对于航运权(尤其是内地航运权)的争夺构成了这段历史的明线;而其中蕴含的则是近代中国国家主权(及主权与由此衍生的民族意识)由逐步丧失向逐步收回的U型变化进程;在此过程中,近代中国三个政权(清、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的稳定性及对全国的控制力的变化与差异则构成对上述两种过程变化的最大影响因素(当然,影响的正面与反面意义兼而有之)——航运问题当然只是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进程的一个面向,但通过罗安妮的叙述,其所折射出的多因素动态变化已足够令读者体悟其过程的复杂性。
民族主义潮流下的商战与合作
虽然航运网络的扩张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于国家间条约的签订、官方照会的往来乃至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博弈(例如因1875年英国领事馆职员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杀而导致的“滇案”谈判最终迫使清廷开放了长江中上游的通商口岸,从而为外国轮船航线向中国内地的拓展创造了条件),但其具体执行仍仰赖于轮船航运公司这一商业体。
通过对19世纪60年代后在华轮船航运公司发展状况的梳理和考察,罗安妮注意到,虽然在内河航运开放后的最初10年间,航行于长江上的轮船往往呈现“万旗飘扬”的态势(轮船公司往往采取股份制,将大量股份卖给通商口岸的洋商乃至华商,导致这些公司往往具有了“国际性”,其直观表现便是各公司下属的轮场所悬挂旗帜显得比较“偶然或随意”),“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航运业已呈现条约体系下的两极化:悬挂英国旗帜和清朝旗帜的轮船公司在业内两家独大,相互争夺更大的贸易份额”(063),具体而言,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以及清廷支持下的轮船招商局成为了1872年以降清廷统治最后40年间长江航道上的“霸主”。
而之所以形成这种“航运中资本与旗帜的统一”,在作者看来“出自两个互有关联的历史进程:英国航运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以及清政府对中国水域航运业的干预”(064)。前者作为一种世界史领域的“常识”或可不必多提,后者则代表了一种清廷在航运权问题上的策略转变:对于轮船招商局的传统叙事通常侧重于其作为洋务运动代表性成果的“自强、求富”动因,然而从航运权的角度考量,则这一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更有可能是清廷在无法通过政治渠道阻遏外国扩张航运网络的情况下,通过“鼓励在内核航线组建悬挂清朝旗帜的航运公司……以阻止外国航运公司‘抢占优势’”(054)的早期尝试,亦即一种“商战”策略。
然而历史往往朝着其设定目标的相反方向发展:在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支持下(给予资金借贷、提供航运订单并予以税费缴纳方面的特权)实现一系列扩张并购(包括美国的昌旗轮船公司),以至于“三分长江有其一”后,为同西方商战而创立的轮船招商局,却于1882年同太古、怡和两家英国航运公司建立起了班轮公会这一长江航道上的“卡特尔联盟”。轮船招商局这种符合经济规律,却有损“民族尊严”的经营策略转变,往往被视为买办阶级软弱性的表征,以及洋务企业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动因。然而罗安妮在本书中同样指出,尽管“招商局确实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并因此日渐同另外两个公会成员拉开差距,但这种“合作”同样“保全了轮船招商局,让它得以在内部纷争和与政府关系的动荡时期度过时艰”(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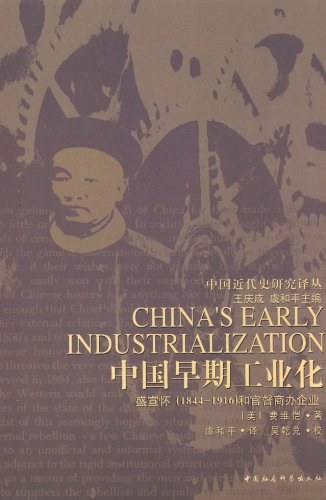
中国早期工业化
8.0
(美)费维恺 / 1990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对于招商局早期发展历史有进一步了解兴趣的话可以参阅本书(《大船航向》第二、三章引用率极高的一本著作),虽然比较老,但至今仍是研究洋务运动或中国近代化早期历史的必读书目。
当然,“三公司”对长江航运的垄断不可能长久持续:甲午战争后日本轮船公司对公会的挑战与“一战”时期两家英国公司的“无暇东顾”已然削弱了班轮公会的影响力与实力,而清末民初迅速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则对该公会的垄断造成了最具实质性的冲击——作者提出,清廷统治在20世纪初的崩溃及民初的军阀割据,不仅导致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护条约体系的中央政府的缺失,同样进一步使得曾受到清政府拘束的“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抵制在中国全社会蔓延开来”,“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动员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业精英,有时甚至还包括军阀政权。”(177)这一运动在政治层面体现为如前所述的收回航运权的主张与行动(包括对于外国企业的抵制运动),在经济层面则表现为悬挂中国旗帜的小型华资轮船公司在1910到1920年代的大量出现(其中当然有企业家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感召,但全民性抵制洋货运动使民族企业有利可图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这些企业加入对航运网络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垄断组织的瓦解——“1917—1935年,更全面的公会体系被短期费率协议所取代,而这些短期协议经常被违反,又重新被商定”(196)。简言之,公会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要求其成员遵守其设定的条款和管制。
更进一步的,在这些华资轮船公司中,还涌现出了数个具备同“三公司”直接竞争实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张謇的大达轮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轮船公司以及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在本书第五章,作者结合上述企业,辟专节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及“民族资本家”这对颇具传统意义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辨析,反驳部分学者对“民族资本主义”概念“言过其实”的质疑,并强调了这类企业资金来源具有多元性的现实特点。同时,通过比较归纳三家航运公司的发展共性,作者又进一步指出,三家企业皆设立于中国通商口岸的腹地(创始人的家乡),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优先对其规模进行扩张——刨去经济方面的动因,这种共同的经营策略或许也体现了其创始人在企业船板工程中所具有的一种民族主义(或者乡土情结)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进入1930年代,民族资本家的爱国情操或官方有限的支持(如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或刘湘对民生公司那样)已不能满足社会舆论对于航运事业的要求,强有力的国家介入航运事业的全过程,扮演整个民族航运领域的赞助人和保护者,成为这一时期的舆论共识。对此,国民政府于1933年以轮船招商局国有化的尝试予以回应,然而其在经济领域统制政策一贯的失败同样蔓延至航运产业:“国民政府缺乏资源,可能也缺乏意愿充当《航业月刊》中设想的国家赞助人角色”(243),加之其收回航运权的修约外交在1930年代的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前,航运自治各项议程几乎全成泡影”(244)。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尝试仅仅证明了国家干预对实现航运自治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性与社会共识,而真正以此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则要到1956年之后由另一个政权完成了。
形塑“新民族”:作为社会空间的轮船
相对于上述航运权与航运事业自主化的步履维艰和扑朔迷离,对于轮船空间本身的改造则较为直观地体现了一种中国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近代化的线性发展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外航运企业的态度分野。
同其他舶来行业类似,航运业在中国建立和扩张初期,必然带有中外等级差异乃至种族歧视的因素。而其特殊之处则在于,作为一个在一定时间内(航行期间)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轮船船舱往往形成一种独立的“微缩世界”乃至“漂浮城市”,从而最为具象化地实现对外部世界的复制或反映,并具体体现在运营和旅行两个层面。
就前者而言,在外国航运公司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种族被当成一种能力,带有技术和文化的含义”(131)——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中国运营的轮船公司(包括招商局等华资公司在内)多以欧洲人和日本人担任船长、高级职员和轮机员等职,占大多数的中国船员则从事较低技能的工作,且两个职业层级之间流动的可能性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明显将技术能力与种族混为一谈的等级制度却有着“非明文”的特点:其成因包含高级海员选任的熟人渠道、低级海员招募的季节性和临时性,乃至保险公司对船舶所有者的压力(投保需要船长等高级海员获得相关资质认真,而由于官方制度的缺失,中国海员往往并无此种证明,导致保险公司仅允许由欧美人担任船长的船舶投保),却唯独没有明文制度的规定。
这种非明文的种族歧视同样针对于轮船的乘客:“在乘客食宿的设计和管理方面,具有明确的中外之别。外国乘客在船舱空间分配、票价以及中外客舱的管理方面都享有明显特权。”(145)最高级的“外国头等舱”(foreign first class,中文为“大餐间舱”)由船长直接负责,其他几个等级的中国舱则外包给买办进行管理(服务质量及生活条件自然难以保证);同时,没有任何一家航运公司承认有明文禁止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舱区,在实践中,却通过购票渠道(外国舱往往要亲自到轮船公司购买或向船长申请)或登船后的排查加以限制。概言之,“排拒并不是硬性规定,比如‘禁止中国人入内’,而是轮船公司的欧洲雇员在个人层面审查和裁定中国申请者”(154)。
而这种船舶空间内非明文、习惯性的种族歧视在1920年代以后的改变,同样受到中国国家近代化和民族意识萌发的推动。作为收回航运权计划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了海员资格认证条例,向中国海员提供资格认证,同时要求在华外籍海员向中国政府进行注册,这一制度安排“开始侵蚀外国技术人员和中国船员之间原本严格的界限”(255)。加之成本方面的考虑(中国技术人员的薪资要求远低于同一岗位上的欧洲人),由中国公司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包括外国在华航运公司在内整个航运行业普遍开始雇佣华籍高级海员。
如果说高级海员种族界限的打破仰赖于船舶运营成本的考虑,则客舱管理模式及空间的变化则凸显了民族意识的感召力。1933—1934年,为解决“茶房危机”(茶房即由买办雇佣或招徕,在中国舱从事服务工作的“编外服务员”,往往数量超额、举止粗鲁,甚至敲诈和威胁乘客),卢作孚主导下的民生公司大刀阔斧地改革了中国舱管理制度,取消买办的外包经营权,对茶房进行裁撤和培训,将其转变为由航运公司直接发薪、垂直管理的正式雇员。同时对茶房制度的改革还伴随着对于船舱空间的改造(中外等级差异色彩的舱名被更为中性的名称取代、各级别船舱之间的差距缩小、低级船舱的环境与服务有所提高),从而推动了“新轮船”的诞生。与之相对,太古等外国在华航运公司基于成本优先的考虑,在茶房制度改革与船舱空间革新方面往往态度犹疑,更凸显了前者在改善中国舱运用环境、消除轮船空间中外等级差异方面的坚定态度。

打造消费天堂
8.3
连玲玲 / 2018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了船舱空间的特殊性,然而在商业经营中对于外来空间的本土运用还有其他诸多案例,如上海的华资百货公司的建立发展即具有相同的性质——打破中外的人种等级差异,做“本民族的洋生意”,并借此取得竞争优势。
而民生公司所主导的着一系列改革,其目的绝不仅止于通过改善空间环境和服务吸引中国乘客,而更兼具有明确的政治使命:如果说过去中国舱恶劣的环境与茶房糟糕的服务态度印证了西方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则通过“新轮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反击了这种成见,并进一步将轮船打造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塑造乘客的举止和期望”(277)。也正基于此种“塑造新民”的理念,“新轮船”改革方案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通过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推而广之,成为其他中国公司效法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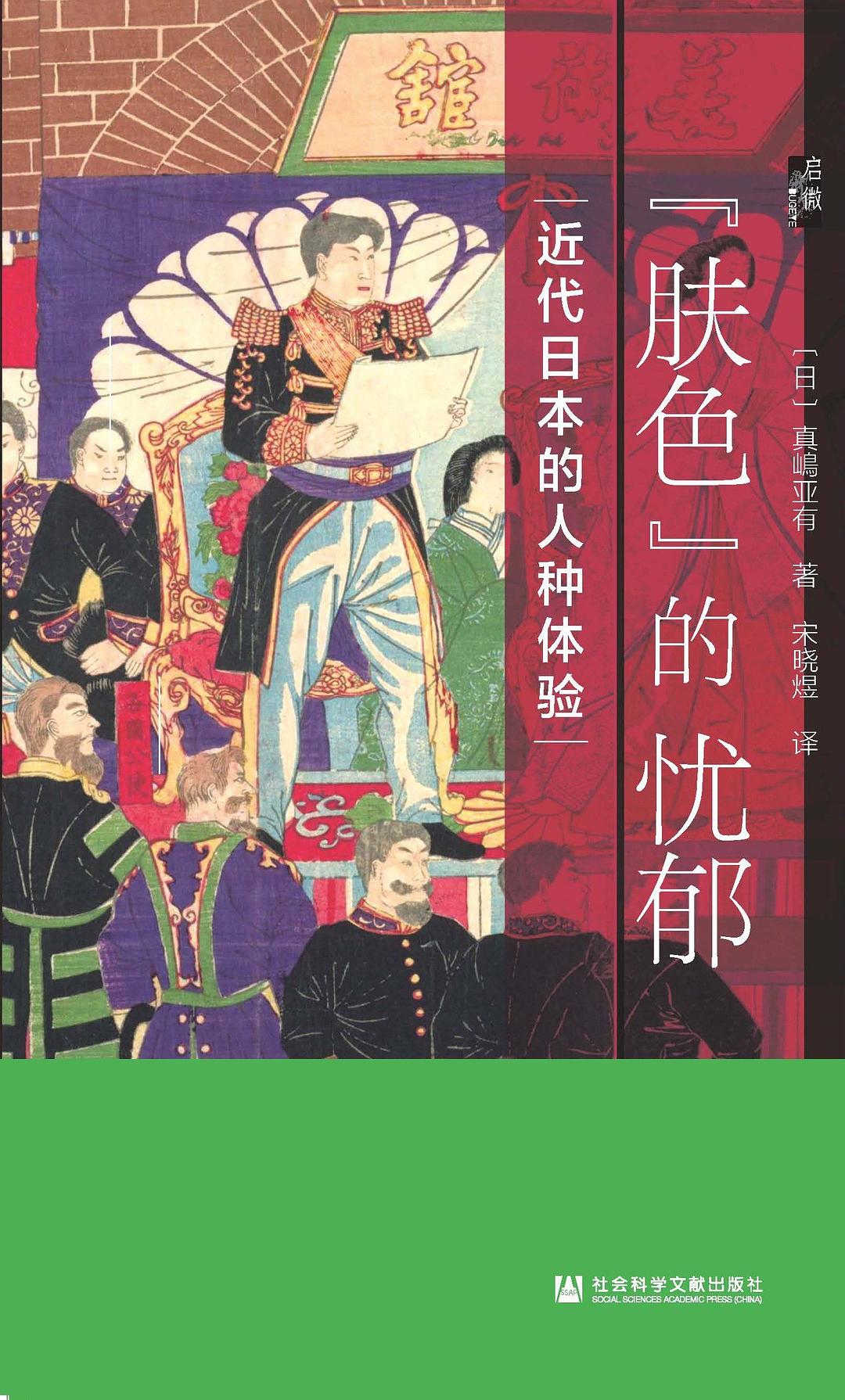
“肤色”的忧郁
8.5
真嶋亚有 / 2021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劣等民族”的歧视往往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性质——受歧视者往往因歧视而处于社会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带来的(身体或素质的)糟糕状态有进一步形成了歧视者的刻板印象。《“肤色”的忧郁》第一章内村鉴三与赴美中国劳工同乘轮船的经历,及其随后对自身肤色态度的改变,即可视为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的例证。
“旧瓶新酒”:重审“半殖民主义”
如果说上述提及的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重新探讨给人以旧题新探的观感,那么就整本书的关照而言同样具有“旧瓶装新酒”的意义:《大船航向》对于近代中国航运史跨时段、跨范围的整体性叙述,实则是为了重新考察“半殖民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不同于已逐渐淡出学界论域的教条式的对“半殖民地”概念的论述(尤其往往还要与“半封建”形成固定搭配),罗安妮认为,这一概念“既涵盖中国经历的特殊性,又兼容于其余殖民环境的可比性,还能代入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帝国的全球崛起过程”(004),易言之,她将该概念置于全球史的视角下进行了重新考察——在各章结论部分,作者引入了同一时期作为标准殖民地的英属印度民族航运产业与航运权的发展状况,并将之与中国航运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以探讨其中的共性、特性及联系。
“合作”这一概念是作者在书中对于中国“半殖民主义”特点的最重要概括,如其在分析清末条约关系时所指出的:
签订条约的西方国家和清政府官员都希望维持清王朝的主权,西方国家想借此避免直接征服和统治的代价,而清政府想保全自存。条约国想借仍有主权的清廷,以保证条约条款的执行。因此,尽管条约体系削弱了清政府的部分主权,但同时也给清政府留有余地,这对于条约体系的运转时必不可少的。(012)
正因为未被完全殖民因而具有“半”的属性,中国在同西方的交涉过程中虽屡遭削弱,却仍保有一定的主动权与生存的最基本底线(轮船招商局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相对于英国队英属印度沿海航运的几乎完全控制,招商局的长期存在本身便彰显了不同于“殖民主义”的独特地位)。而进入民国时期(尤其北京政府时期,并在南京时期依然有所留存),中西交涉双方皆陷入一种“多头政治”的状态——列强之间互相顾及,而中国各政治势力乃至朝野之前互相牵制,造成了“更多的斡旋空间,更多的制度安排和更曲折的历史实践。这都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增添了(相对印度等殖民地而言)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丰富性”(译序004)。
当然,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并非孤立存在,通过同印度航运事业发展的比较,作者认为,英国在华势力的形成过程中,英属印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不仅在于其作为印度对华扩张期间“物资大本营”与“信息中转站”的地理意义,还应当注意到,在建立中国航运网络与航运秩序的尝试过程中,“印度经验”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英国外交官与航运公司负责人所设想的“模板”与“路径”,在涉及对华航运扩张的辩论中,“英属印度是他们不断提及的例子”——半殖民和殖民统治“两者共存于同一时空,并相互影响”(062)。而这种共存并相互影响的状态甚至不仅限于东亚一隅,将中印航运发展置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全球扩张加剧的更大背景下,则可以更进一步注意到,二者既是这一扩张进程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其参与者。世界的共同进程与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相互交织,“半殖民主义”也得以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下被重新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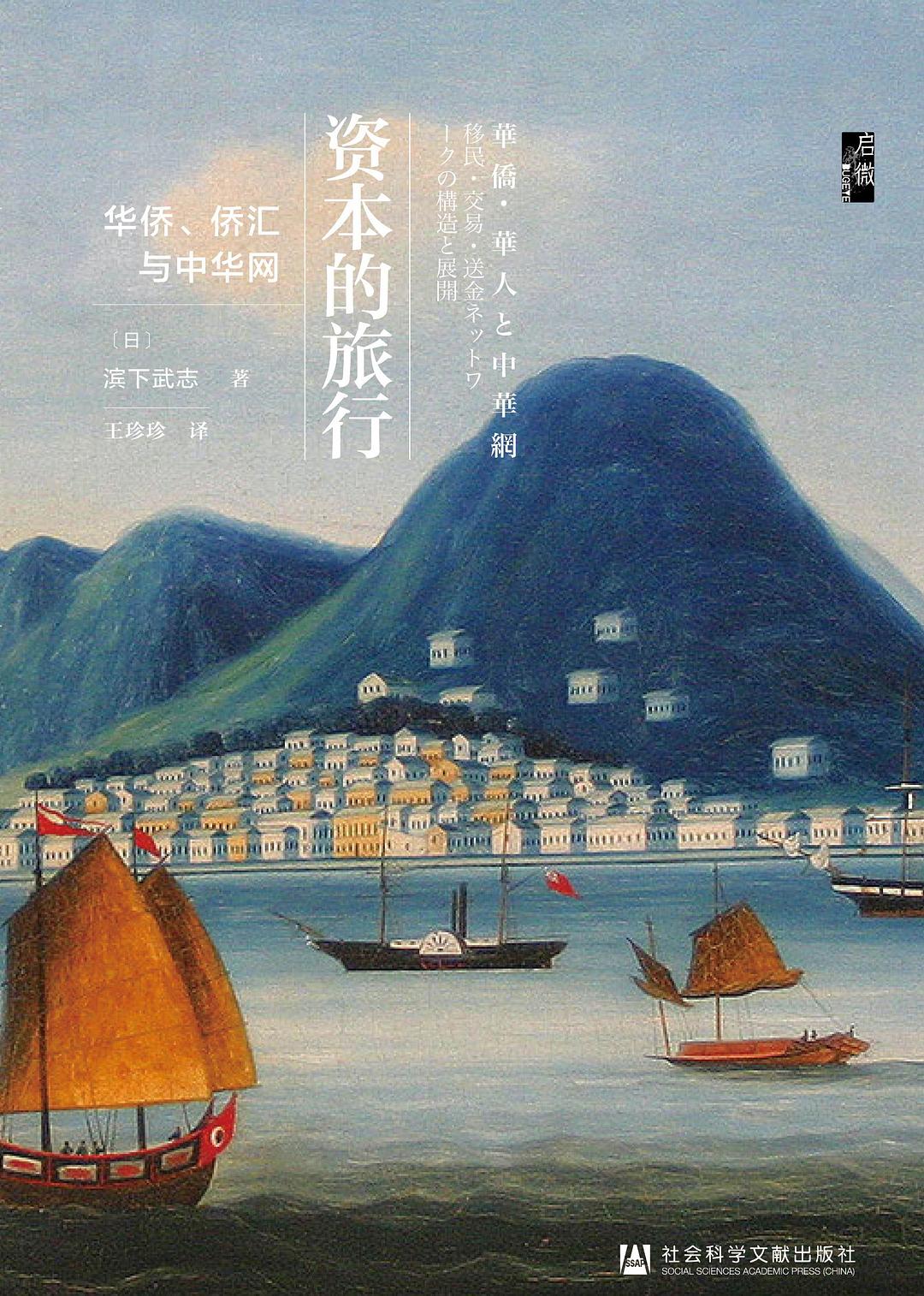
资本的旅行
6.5
滨下武志 / 2021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为另一部全球视角下的跨区域研究,滨下武志教授更侧重于对于中华关系网的构建。但与《大船航向》相似,二者皆展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以往不易察觉的联系。
ps.如果说本书有什么让人感到不满足的地方,当属对国民党政权航运政策的论述仅始于1927年其建立名义上的全国性统治之后,从而略过了其作为地方政权的广州政府时期——这使我们无法判断其1930年代收回航运权、航运公司国有化等政策是基于其作为全国性政府的考量,还是兼有既往执政理念的延续性。而这种政策变化是否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主权、政权与航运权三者联系的发展变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其缺失(或忽略)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