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与其说是一部汉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史学理论。
——施爱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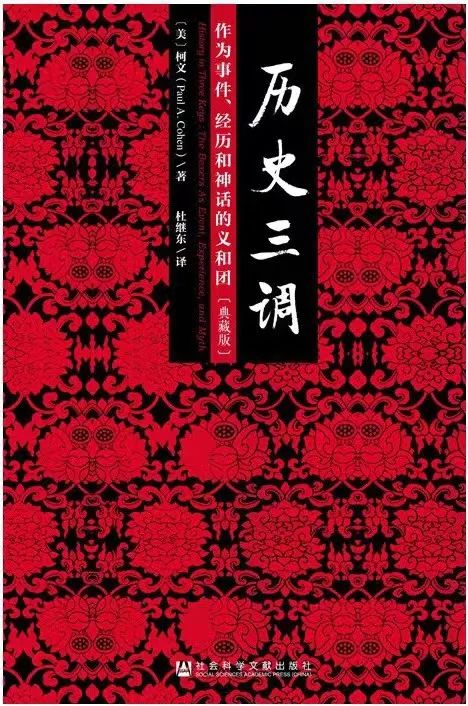
《历史三调》这本书,虽然主题是义和团运动,副标题就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但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就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柯文在书中所提到的作为事件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学家研究所得到的历史;作为经历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历史;作为神话的历史指的就是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为现实服务的历史。
历史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对它独特的定义,每个人都会赋予历史不同的意义,在这些不同的历史认知中,我们也许会考虑过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每个人在刚接触这个概念时都会疑惑的一个点:什么是历史?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用义和团作为一个事件来讲述了一种历史认知的方式,他在书中指出:“‘我’并不是对历史任何方面都感兴趣,而只对直接影响了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观念感兴趣。”这就从一种层面上解释了这本书,其重点关注的并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不同认知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不同思考方式。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例,从三种维度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这是与以往相比较更为新颖的探寻历史的方法,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在这本书中的绪论中,作者从具体的考证工作入手,向我们阐明了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对历史叙事化处理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将人们经历的历史和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割裂开来。这本专著不同于大部分的历史专著,作者在向我们揭开义和团面纱之前煞费苦心地撰写了一些文字,其中辩证地向读者说明了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有着比表面上更复杂、更细腻的关系。比义和团运动革命期间发生了什么更引人深思的是,作者在探究这些历史过程中的历史观。这让我对以往所所积累的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标志性意义有了全新的认知角度。我们不仅要了解历史,还要了解历史是如何有条不紊地来到我们面前的。
在裴磊的《历史多重人格现象思考——《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后感》中说:“我们看到的历史知识它的面具,但面具背后的真相才是真正的历史,但我们却无法得知。当我们确切地认为我们已掌握了足够的理性知识的时候,知识足够支撑起解释整个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面具表面而已,而对面具背后的历史本身还相差甚远。”似乎是作为对这句话的解读一般,在读者们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考虑到类似的问题,恰如所谓“神话的历史”,也就是革命家和政治家所塑造的历史,出于现实目的,人们往往抽取事件中的某些片面,通过夸张和描绘变形,给这些事件打上一个特定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便是用于拱卫自身的工具;或是“经历的历史”,也就是当事人的记录或回忆,但因为每个人都是事件中的一份子,所以每个人都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中进行这一场碰撞,或者说是一场博弈,在同一个事件中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却正巧凑成了作者笔下的“事件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在各种已知条件下将数不清的历史进行凑整,拼写为一副图画,用语言文字,用其内心中对于他所看到的历史画面进行描摹,构成了这一片面的布局。但是历史学家们在重新塑造历史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因果逻辑让这一切都看上去有条不紊,可是谁又考虑到了事件中的随机性呢?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有逻辑的东西,比如今天老师问我什么时候交作业,我说我明天交,但是在今天我写完自己这份作业以后,心中便颇为激动,我迫不及待向老师发送我写的东西,展示自己的成果,这也是一份随机性,这也证明了,历史的逻辑性是在人的行为的随机性下进行跳跃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既定发生的,而是充满了偶然与随机性,否则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枯燥的‘程序’。”
因此,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终究是有局限的,他们对过去的重塑并不是真正的过去,这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叙事化处理的问题,而是在于历史著作对于历史事件的高度总结简化和浓缩,在“神话创造者”们的笔下,他们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按照清晰化的条例和明确的故事发展时间线,堂而皇之的、清楚完整地描述了过去,但是真正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处理好的就是经历和历史之间的悬殊差别,并对这些差别做出反应,将其中反映出的东西做出系统完整性的解读。在历史学家的角度里,找到繁琐复杂的故事线中的那根脉络,清晰明确地找出其中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经历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所有事件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都显得那么合乎其身。从一方面讲,个人经历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风浪,个人在这整个历史事件中本身就是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的,其中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明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对于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到来都是无能为力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改变不了事情在他身上的发生,他改变不了时间线的推移,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可能努力地,尽可能去改变自己能够碰到的未来,撬动一点点那些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能是被动的。但他也是主动的,在这一层面上,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历史,个人在发生自己的叙事能力,人们把自己的经历变成故事,变成历史,并赋予其原本并不存在的意义,因人而异的同一事件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同的,都具有其不同的意义,只不过是相对于历史学家们的叙事,个人叙事的能力功能显得更加朴素苍白而已,对于其余人来说只能称之为故事,但对于时间长河,对于那个人本身来说,这却是他的历史。历史学家同个人不同的最终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根据知识层面而非感觉层面来勾画历史。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或者说一定会下意识地去遵从当时社会公认的关于真实性的强制标准,准确来说就是他们一定会按照当时社会主流或是末流的社会观念来参考历史标准、制订历史标准。在这一层面上来看,这件事情似乎也符合了章学诚所指出的“史德”观念,即著书者的心术,这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职业标准要求,也是历史学家们的职业标志。于是柯文在此提示历史学家们“必须十分小心”。
历史学家们无法真正还原真实历史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也是他们没有做到真正“小心”所引发的。历史学家们在已经了解了历史结果的角度去还原历史,他们总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上帝视角”存在的。他们重新塑造历史的方法以历史结果作为出发点,来一步一步描绘出之前的历史,同时要使所还原的历史在逻辑上十分合理,但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合理”使得其历史在逻辑满足的条件下,导致了还原出来的历史同亲身经历者所体会的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发生。就像数学方法中的“反证法”。在知道结果的条件下一步步去推理方程式的步骤,去还原方程式中原有的逻辑顺序和推理条理。但是数学是具有严密逻辑条理性的一门学科,这同处处充满偶然性的历史是不同的,就像亲历者一定无法得知他所做的某件事的结果,他们也不知道事情发生的进程,更不会知道自己目前所在的阶段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会知道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对于整个事件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会对事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根据事件的结果赋予不同事件不同的历史意义。当然,对于整个事态的全方面了解这一方面,柯文强调历史学家对事件证据的掌握必须有数量又有质量,而且历史学家在利用这些证据重塑历史时要努力在现实于过去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不为人们所知了,因而对于历史研究中史料即证据的运用和掌握也是历史学家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但是总归于此,那就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因人而异,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历史观念,对于历史不同的见解促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世界历史观。
在客观上的解释是:“历史”一词,起源于希腊语historia,意为“研究知识和通过研究获得的知识”。历史作为研究 对象,被大致“切割”成两种形状,一是作为主流的“断代”划分,即将历史分隔成“线状”的古代、中 古、近代、现代;二是非主流的“片状”划分,如将世界各区域划分为“文化”或“文明”进行考察的“文化(文明)形态史”。历史简称“史”,是指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活动行为的系统性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通过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其中包含有三种含义,即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沿革、来历;过去的事实。《汉典》中对于历史问题的解释是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实现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甲骨文中“史”字同“事”字是相似的,指的是事件。“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那么被史官所记录的事情,也就是说,被所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史”。
历史的英文词History源于古希腊语ἱστορία(史记),意为“询问”,“从询价知识”或“法官”。在这些种种渠道上的演进最后幻化为今天的“历史”一词,即“History”。
在中国,毋庸置疑的,历史是作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在古人的努力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同中国那般拥有如此浩瀚磅礴的历史记载,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史书群体,从官修的“二十四史”,再到民间的那些杂史野史,在这些数不尽的经历研究当中,人们对历史研究这一事件提了三个要素,即史实、史料、史家。
再回到柯文先生的《历史三调》,不论是事件、经历,还是神话上的历史,这不都是对于历史的一方面解读吗?三个层面的认知主体各有其特点。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都知道事件的结果,因为他们都具有事件经历者所不具备的广阔视野,但是他们在发掘所谓的“历史真实”的时候,其着重下笔的方面就成了他们所偏好的差别体。历史学家们着重研究历史的复杂性,可在复杂问题被他们梳理简明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对历史的着眼显出片面化了。而神话制造者则是为了寻找思想资源,常常会片面来看待历史事件,但他们的片面看法是从主观上出发的,而历史学家们的片面则更多的是在于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理解力度问题。因此,这两者在处理史料的时候,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们更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但在这二者的方向出发,他们对待历史的片面性,又与历史参与者的片面性有所不同了,参与者无法超越时空的局限,但他却拥有其他两者所都不具备的优势和体验,他们可以自己“创造”历史,这个创造出的历史,指的是后世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在这一方面来说,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其实也是历史参与者,不过他们参与创造的历史,则是自己时空的历史了。
人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会不自觉把自己放在历史发生时候的时空之中,这似乎是《与历史对话》一书中所体现的矛盾相同一般。该书探讨局外人几乎不知道但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色彩,这本书中表露出浓浓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这是中国中心观对于外文的报复。这正如巴拉克·奥巴马有意识地把自己摆放进以《圣经》内容构建的美国民权运动史中一般;如马丁·路德·金的不断演讲;如中国人将越王勾践的故事不断翻出放在自己人心中,使中国人对此熟知其细但外国却从未有耳闻;如文艺复兴中,人们借助古典复兴的名义来传播新的思想,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古代故事与当下历史之间的互动在当下层出不穷,人们似乎都渴望借此来展示此前人们同自身思想的共同之处,他们片面地看待历史,在历史学家们描绘出的“完整”的历史事件中,又借以片面的看法,使自己成为“神话制造者”。对于不同历史面向的深刻反思,无疑是有助于我们考究不同历史概念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的,神话中的“神性”是由不同时代和处境中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和理性光辉的照耀之下,义和团被神化为迷信、落后、愚昧的象征;在一战以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狂热时期,义和团运动又被神化为爱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在建国之后,文化大革命之时,则又成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榜样。面对不同的神话版本,我们其实并不会唾弃和厌恶,那些神话中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风向标。有时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价值。在对待不同历史的同时,我们所能做的,并不是想方设法揭下来那段历史的“面具”,而是要在不断求真求实的基础上,运用理性尽可能地借助这个面具的表面来探查其背后所表达出来的真相。
傅斯年曾指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一,在《历史三调》中的史料运用则是异常突出的能力。柯文先生在记叙义和团运动作为“经历”的层面时,较多地运用了类推的形式来解读人物的心理活动。这其实也包含了非常浓重的臆测成分。在《历史三调》中,柯文在以历史学基本方法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加深入地诠释了所要表述的内容,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到特定的历史现象与事实。
在此,借助唐艳香女士的一段话进行总结:
总之,《历史三调》柯文所要书写的并不只是义和团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他只是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探寻历史真相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神话,“想发现一种历史学家们跨越他们历史论题界限的方式”。对他而言,义和团运动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个放大了的个案,可以作为他解说自己关于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实现“从一粒沙中看世界”。
我们应对历史抱着敏感的直觉,时刻注意,在坚定自身历史观的同时,做到柯文先生所期望的“必须十分小心”。我们时刻保持敏锐求真的精神,保存自身的“史才四长”。
柯文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未必正确,但是无论如何,《历史三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式,值得历史工作者认真思考。

作者简介
康晨阳,就读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湘潭大学历史学会第24届团支书,湘潭大学风华文学社第30届副社长,主编期刊《夏鼎》第一辑,参与编辑《风华》等学生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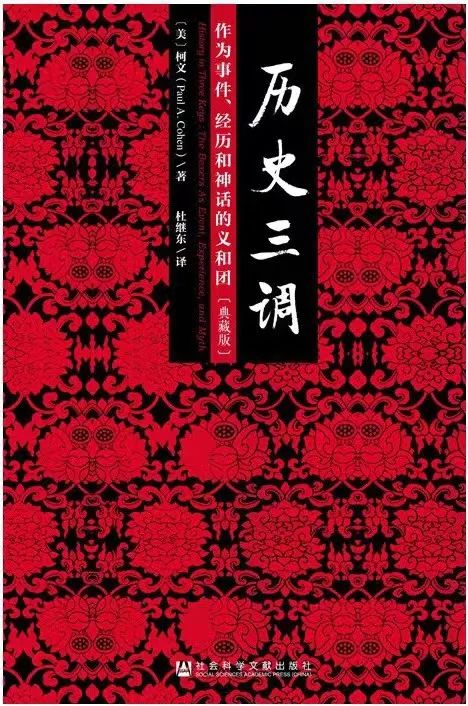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