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洋铭

卡伦·拉德纳(章静绘)
卡伦·拉德纳(Karen Radner)是慕尼黑大学近东暨中东古代史洪堡讲席教授,长期致力于古代两河流域文献、历史和考古学研究,尤其关注亚述帝国时期。去年,她的《古代亚述简史》中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她的《巴比伦简史》中译本也将于近期面世。这两本书的译者、鲁汶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常洋铭应《上海书评》之邀采访了拉德纳教授,请她谈谈自己学习和从事亚述学与近东考古研究的经历和心得,以及她如何思考亚述学及古代近东研究在当代的学科定位和社会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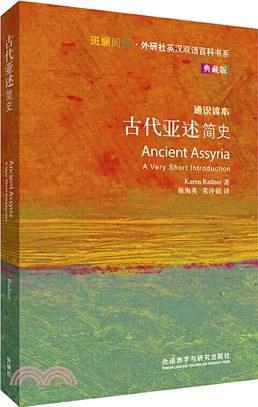
【奥地利】卡伦·拉德纳, 颜海英、常洋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280页,42.00元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古代近东文明的?
卡伦·拉德纳:我在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座小城长大,那里有一处非常重要的铁器时代遗址,即迪伦堡(Dürrnberg)的盐矿开采基地遗址,所以我自幼就对整个古代世界充满兴趣。之所以专门研究古代近东文明,是因为在我十六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叙利亚旅行,我对那次旅程非常着迷。那里曾经有过那么伟大而繁荣的文明,在地表上却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文献和遗迹去了解他们。
您在学习亚述学和近东考古学的过程中,接受到的是什么样的训练?哪些学者对您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卡伦·拉德纳:我在维也纳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是一个四年制的学习项目。我的专业被称为“古代闪米特语言和近东考古学”(Altsemitische Sprachen und Orientalische Archäologie)。我选修了所有楔形文字语言的课程(其中许多不属于闪米特语族),以及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等。我的老师是赫尔曼·珲格(Hermann Hunger),他是全世界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天文文献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另外,我的老师还有专门研究阿卡德语语法的汉斯·赫希(Hans Hirsch)。除了学习古代语言,我还修读了以中东和地中海东部为重点的考古学课程。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下,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了第四年的学习。在柏林期间,我的学习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方面,主要跟随曾经发掘过乌鲁克遗址(Uruk)的汉斯-约格·尼森(Hans-Jörg Nissen)和曾经发掘过谢赫-哈马德丘遗址(Tell Sheikh Hamad)的哈特穆特·库内(Hartmut Kühne)学习,并且和罗伯特·恩格伦德(Robert Englund)学习苏美尔语。与此同时,我还在约阿希姆·马尔赞(Joachim Marzahn)的指导下,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柏林近东博物馆(Vorderasiatisches Museum)的楔形文字泥板部门工作。我认为马尔赞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因为他教会了我如何绘制楔形文字泥板的摹写图。我的博士论文是由赫尔曼·珲格和海德堡大学新亚述时期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卡尔海因茨·戴勒(Karlheinz Deller)共同指导的。在我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每年夏天都会参加田野发掘,主要是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直到现在,我还花很多时间在田野工作上,目前还在主持着位于伊拉克北部的一个考古项目。

拉德纳教授(中间)与研究团队成员在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遗址

拉德纳教授在伊拉克北部的派什达尔平原考古项目点
包括亚述在内的古代两河流域(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三千纪开始,延续了三千余年。而您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聚焦于公元前九至前七世纪的新亚述时期(也称“亚述帝国”)。为什么这个时期对您来说如此重要?或者说,为什么包括亚述学家和普通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关心这个时期?
卡伦·拉德纳:在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军队的攻击之下,亚述帝国核心地域的城市被一一攻陷,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很突然地就崩溃了。因此,我们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研究——在建筑物起火时,楔形文字泥板并不会被毁坏,反而会被更好地保存下来。也是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崩溃,使得新亚述时期成为古代两河流域文字记录最充分的时期之一。我认为这一时期非常引人入胜。因为在当时,亚述帝国的影响力覆盖了从地中海到非洲东北部(现苏丹境内)、再到波斯湾和高加索山的广大疆域。这使这些地方的人、资源和思想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交流。比如说,鸡就是在此期间被引入西方的。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您撰写和编辑了许多部关于新亚述时期出土文献、历史、地理和考古学的专著,可否请您向读者们简要介绍一下新亚述帝国最重要的遗产?
卡伦·拉德纳:作为一个国家,亚述帝国比以前的任何国家都更大、更成功,它为此后的阿黑美尼德波斯帝国做了铺垫。亚述帝国最具影响力的创造和遗产之一就是它的长途驿传系统,即一封信由一系列信使而非一人走完全程来运送。这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它必须依靠于一个广泛、深入且可信的行政控制与管理体系。如今有许多学者认为那个时期末期出现的一神教中的神的概念便是以亚述国王为蓝本的——亚述国王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统治者,他用条约将他的臣民约束在他身边,规范他们的行为。由此可见,亚述帝国对政治和宗教概念的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它!
2005年,您离开欧洲大陆前往伦敦大学学院任教,与许多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如艾美莉·库尔特(Amelié Kuhrt)、西蒙·霍恩布鲁尔(Simon Hornblower)等共事。如果将您此前的工作与后来的著述相比,可以发现您关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变得更加多元,是否可以认为您尝试在亚述学领域探索其他的研究路径?
卡伦·拉德纳:在此期间,我的研究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因为我在伦敦大学的教学也涉及古代埃及。因此,我对连接或区分古代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有了更多的认识。另一方面,与历史学家一起工作肯定影响并促进了我自己的研究,我开始更多地思考古代国家的组织,尤其是他们之间不同的凝聚策略。从2008到2012年,我主持了一个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AHRC)资助的研究项目,主要研究亚述帝国的信息渠道,特别是长途通信的作用。这项研究重点关注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在当时,由亚述国王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扩大了两倍。亚述国王留下了大量的铭文,从他们的角度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统治,并将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自己。这些资料尽管非常重要,但却将国王以外的对帝国的扩张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人撇在一边。我喜欢称他们为“亚述帝国的建设者”,并且倾向于强调这些人在亚述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与中国历史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在亚述帝国,未来的国家官员也是在王宫中进行集中训练的,而且这些见习官员中有许多人在少年“进宫”之时就被阉割了。现在,我们能够读到一些国王与他们的臣属之间的书信往来。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会对他们的国王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显然是因为擅长他们所做的事情而被委任的,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2015年,您回到了德国,在慕尼黑大学担任近东暨中东古代史亚历山大·冯·洪堡讲席教授,但却是在历史系,而不是在慕尼黑大学历史悠久的亚述学与赫梯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syriologie und Hethitologie)。在德国,一位从事古代文明领域研究的学者成为历史系的教员或被称为历史学家,在当时(可能现在仍然是)是一件新鲜事。您是如何在慕尼黑大学定位近东暨中东古代史的?慕尼黑大学的近东暨中东古代史教学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卡伦·拉德纳:2015年,当近东暨中东古代史洪堡讲席刚设立的时候,它是德国大学中第一个此类教授席位。在慕尼黑大学设立这样一个教席的想法是由我的同事马丁·齐默尔曼(Martin Zimmermann)教授倡议的,他是一位研究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公元前四世纪末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区的本土文化传统。在慕尼黑大学,我首先将近东古代史定位在历史学科内。当然,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需要借鉴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研究手段及成果,但我们的研究问题和教学倾向于集中在“大局”上,比如说:是什么将社会联系在一起,是什么塑造了社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人,而不是他们的文献和文物,这可能是我们在研究和教学上与亚述学、赫梯学、近东考古学专业的最大区别。我试图鼓励那些对古代近东文明感兴趣的历史系学生尽快开始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等课程,因为这在进行原创性研究时非常重要,这些课程是由我在亚述学和赫梯学研究所的同事讲授的。
除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所提供的高级课程以外,我们还定期为初学者提供一系列的研讨会。系列研讨会中第一门的关注点便是新亚述帝国,去思考这个国家在公元前九至前七世纪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学生而言,看到亚述人如何处理每个现代国家也必须面对的挑战,着实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个人的贡献和参与、权力的下放或者信任和控制之间的平衡。系列研讨的第二门则专门讨论对许多人来说是古代近东的代名词的城市——巴比伦,时间范围是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到公元后一千纪中期。在此期间,马尔杜克的雄伟神庙逐渐淡出大众视野,一神教取代多神教成为主流。这门研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们在漫长的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跨度中,观察这座城市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发展历程。对于学生而言,这个一度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一片废墟,这让人颇感唏嘘。系列研讨的第三门则关注公元前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涵盖了新巴比伦帝国(即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时期)、赛特王朝时期的埃及(当时海军对这个国家变得极其重要)、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王国(世界上第一枚硬币就是在那里发明的)、雅典及其激进的政治进程(包括民主在内)以及波斯帝国的诞生。这门课程的重点是向学生介绍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内极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景观,以及我们想要了解这一时期需要依靠的形式非常不同的原始资料。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旨在了解过去。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任何地区和时期。然而在欧洲和北美,亚述学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古代近东研究(包括赫梯学等)一直受语文学传统和二战后区域研究兴起的影响。在欧洲,亚述学通常是独立的,或者与埃及学和近东考古学相互依存。而在美国,亚述学通常是近东或中东研究系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亚述学、埃及学乃至古典学的教学方式也与五十年前基本相同,对于现状的任何挑战都会引起争议。作为亚历山大·冯·洪堡讲席教授,您的任务被描述为“将古典和古代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普遍的古代史”。您将如何定义亚述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您认为这种转变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或超越这些问题?
卡伦·拉德纳: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亚历山大·冯·洪堡教授讲席的主要结果是,我和我的团队成员为历史系学生授课,学生中也包括未来的教师。当然,学习历史的学生要比更为专精的考古学或语文学学科要多得多,因此我们接触到的人也多得多,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埃及和古代近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是“死”的——相对于古典文明,因为主流的历史叙事为它构建了一个不曾间断、直至今日的连续性。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一些最伟大的文明结束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它们不得不一步步地被重新发现——自十九世纪以来,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
在你的问题中,你正确地强调了许多古代近东研究项目的语文学特点,这是因为古代近东的人们所使用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字母文字非常不同。楔形文字对任何接触过汉字的人来说可能都很容易理解,但在西方世界,这被视为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大学里的大部分培训都是为了学习如何阅读这些文字,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也是去理解它们的内容,并且经常需要从许多分开的零散的抄本中重建整个作品,且这些抄本都不完整。因此,进一步的解读或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往往不被视为优先事项。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是不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亚述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之下,许多可靠的文本版本及译本已经问世,因此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努力使这些文本在网上变得更加易于搜索,而原始资料的更大可及性也使得将古代近东纳入历史课程变得更加容易。在慕尼黑大学,我和我的团队正在建设“慕尼黑楔形文字文献开放数据库”(Munich Open-access Cuneiform Corpus Initiative),这一计划主要致力于新亚述和新巴比伦时期出土文献的数字化。

慕尼黑楔形文字文献开放数据库项目团队,右一为拉德纳教授
众所周知,两河流域所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地区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处于战争、冲突和恐怖袭击不断的动荡之中。许多考古遗址、考古工地和博物馆被破坏;无数的文物,如楔形文字泥板和雕塑等,被掠夺并偷运到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在您为大众读者所写的《古代亚述简史》和《巴比伦简史》等书中,您经常提醒您的读者们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及其人民与当代中东以及他们自己联系起来,您也乐于分享您对伊拉克、叙利亚的现状及其文化遗产的看法。当下,您在中东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您又如何看待自己身为古代近东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卡伦·拉德纳:我经常待在中东,因为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我通常参与涉及亚述帝国的项目,由于亚述帝国的领土非常大,所以尽管有些地区一直为战争所困,但我还是能够持续地开展工作。我以前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工作过,但从2010年以来,我主要在伊拉克工作。2015年至今,我在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主持了一个发掘项目,该项目位于今天被称为派什达尔平原(Peshdar)的地方,那里在古代是亚述帝国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发掘一处在亚述占领之前和占领期间一直存在的定居点。事实证明,这项工作非常有趣。因为对于当地的一般人来说,亚述帝国的到来似乎没有造成什么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但是,定居点的精英们则非常喜欢亚述的物质文化和装饰,乐于接受各种时尚,这些时尚同时也流行于亚述帝国的核心地域。在派什达尔平原,我们与当地的文物部门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一半的研究人员都来自库尔德地区,而外国研究者则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各个国家。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一起,我认为这对于团队所有成员而言都是一种多元的体验。我们还确保以英文和开源的形式发表我们的成果,以便在派什达尔平原的每个人以及对它感兴趣的人都能读到这项研究的内容——人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派什达尔平原考古项目2021年度工作团队合影
派什达尔平原的发掘工作位于远离冲突地点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与这里的冲突和暴力绝缘。最近,我在摩苏尔待了一个星期,和海德堡大学的同行一起,参与对ISIS破坏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echerib)宫殿遗址的现状的评估。在ISIS占领期间,摩苏尔的居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许多建筑被摧毁,很多房屋至今还留着战斗的痕迹。ISIS也将摩苏尔及其附近的文化遗产作为打击目标,因为摩苏尔城就位于亚述帝国最后的首都尼尼微古城(Nineveh)的遗址之上。他们这样做有两种目的:第一,他们想要摧毁塑造摩苏尔居民身份的最突出的纪念物,其中包括清真寺、内比尤努斯遗址的约拿墓以及摩苏尔考古博物馆。后者展示着该地区一些最重要的遗址如卡尔胡(Kalhu)和哈特拉(Hatra)等地出土的文物。ISIS制作并大肆传播针对文物的破坏行为的视频,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清除城市中的非伊斯兰教因素。第二,他们还以非常系统的方式掠夺考古遗址,搜罗珍宝,甚至亵渎内比尤努斯的墓地遗址。他们掠夺的文物将会在国际文物市场上被非法出售——这些文物可能在几十年后才会出现,伴随着一个捏造的出处。ISIS在摩苏尔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所作所为,凸显了许多人对过去的双重态度:一是连续性,即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极为重要的对当地历史的认同和归属感;二是疏离感,认为过去与今天并不相关,过去充其量是一种可以用于谋求经济利益的资源。在我看来,古代近东研究者有责任确保前一种连续性和归属感超越单纯的地方性。就两河流域而言,即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地区,我们必须强调它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人们聚集在一起,建立了第一批村庄,以及后来的最早的城市。它是数学和天文学的诞生地。当像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这样的地方被掠夺时,失去了一段历史的并不只是伊拉克人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2021年9月,拉德纳教授考察被ISIS破坏的辛那赫里布王宫遗址,照片摄于王宫朝堂(throne room)所在地。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