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县城往北两公里左右的碗窑村里,最近入驻了几支来自全国各单位的考古队。7月下旬,王筱昕跟着考古队来到碗窑村,作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元明陶瓷考古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她將在这里进行发掘和整理,同时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准备材料。
都说隔行如隔山,外行人看来,考古学要么是墓室里的探宝小分队,要么是拍卖行里火眼金睛辨真伪的鉴宝大师,但考古学究竟学什么做什么?知之者甚少。
对于记者各种小白式疑问,在考古现场忙活了月余的王筱昕的解答,一言以蔽之,颇有些哲学思辨:考古学解决的,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考古学探源
“从学术角度来说,考古学的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复旦大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系的潘碧华副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考古学并非一个纯文科的学科,“跟历史学主要研究文献不一样,考古学需要从人类社会的物质遗存来做研究,所以为了获取这些遗存,田野调查和发掘在考古工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中国人对于考古一道并不算太过陌生,我国古代有一门学问是金石学,何为金石学?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对我国古代碑碣刻石的收集、著录与研究,称作金石学。追溯起源时,不少人将金石学看作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潘碧华细致地补充了这一说法:“金石学的确和考古有些关系,不过它主要研究传世文物,特别是这些文物上的铭刻文字,重于考据,所以跟文献史学关系更大一些。考古则不然,考古研究的是地里挖出来的文物,所以二者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金石学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的源头。”
中国考古学最初其实跟一名西方的地质学家有关。“北洋政府时期试图发展工业,需要专家勘探各种矿石储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因此受邀参与勘探工作。由于当时军阀内战,他的找矿工作并不顺利,但发现了不少古人类遗留下的石器和陶片等,其中最为国人熟知的就是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仰韶文化就是以此命名。”
1921年,安特生把当时西方的田野考古技术引入中国,先后发掘了辽宁葫芦岛的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前者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第一挖”,而后者不论从考古发现的丰富程度还是后来的影响力来看都要远高于前者,因为仰韶的发掘首次证实了中国存在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真正搞考古的人并不多。上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哈佛求学归来,作为体质人类学的博士,被国内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凭借在美国掌握的田野考古研究方法(在美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他从新郑李家楼大墓到西阴村发掘,后来又参与主导了殷墟的发掘,逐渐成为国内考古学的执牛耳者。除此之外,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考古学课程,从西方引进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各地生产建设中,也涉及了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学专业建设因此走上正轨,其中又以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科建设较为完备。考古学引入初期即为印证历史,因此大部分考古学都归属在历史学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逐渐增多,考古学探索古代文明的能力不断增强,学科视野不断扩大,理论方法不断完善,考古学已成为教育部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不再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不少学校的考古学专业也从历史系中逐渐独立出来。”当我学考古时,我究竟在做什么?
许多人说考古学是一门需要坐冷板凳的学科,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很多学者终其一生,或许都不会有什么大众意义上的重大考古发现成果,从这一点来看,考古诚然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学科。不过,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考古界的主流,不是“坐在板凳上”,考古和田野是分不开的。
考古系的学生们大多听过这样一句话,“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考古,下一趟‘工地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了,田野考古是你们的一个‘分水岭”。“工地”,是考古学师生们对于考古田野的昵称。
一般来说,考古系的学生在大三时会经历第一次田野考古,他们也将第一次上手各种考古工具,比如手铲。一把趁手的手铲,能够帮助考古学家更快更好地发现各种考古迹象,普罗大众对于探铲的热情可能更高,这一工具据说来源于盗墓贼常用的洛阳铲,经过改造后成为了考古学家调查勘探时的好帮手。
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靴、遮阳帽等则是考古队员标配的行头,在野外时,他们一般还腰挎“破铜烂铁”,手拎“大包小包”,一个个灰头土脸,对于工作时的仪容仪表,考古界的朋友们总是自嘲:“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才知道是考古队的”。
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的一大功臣傅斯年,曾将考古工作戏称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形象地概括了考古田野工作的内容。事实上,野外的考古工地还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遇到盗贼或者野兽,堪称考古惊魂现场。“有一次发掘工作结束后,留下了部分队员看守场地,结果入夜后队员们遇到了一匹狼,嗷呜嗷呜地渐渐靠近帐篷,幸好当时同学及时打电话呼救,一群人赶到后赶跑了这位不速之客。”一名考古工作者笑着给记者举例子。
为了解决某些学术目的,考古队主动向文物局申请发掘项目,进行遗址探寻的行为被称为主动性发掘,主动性发掘并非考古界的主流,大部分考古活动都是由于基建工程的原因,不得不对遗址进行清理,即被动发掘,也称抢救性发掘。比如三峡工程的修建,将淹没海拔175米以下的广大地区,而这些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文物资源,为此,从上世纪末起,全国各地考古和古建筑专家奔赴三峡,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保护工作。“从历史遗迹发掘中还原真正的历史并且加以印证,这就是考古的工作。但在技术还不够先进的情况下,对文物最好的保护还是将其深埋地下,比如世界瞩目的秦始皇陵。”
经过两个月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王筱昕和考古队员们在云南建水窑取得了一些成果。从建水土陶厂厂区向北延续500余米的各个山岗处,依次分布着20多处古代瓷窑,考古队发现了两座龙窑窑炉,出土物极为丰富。
每天早晨8点半,王筱昕准时到达考古工地,扎在自己的探方里,判断各种地层单位的相互关系,和工人配合逐层向下清理,对每天出土的文物進行分类和筛选,直到晚上5点半收工。目前,考古队发掘到的层位是由古代窑业废弃物形成的渣堆,厚度超过1米,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窑具等遗物。
事实上,“搞收藏的不懂考古,懂考古的不搞收藏”是约定俗成的行规。
“现在每天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给文物做记录并做好标签。如果是保存情况比较差的文物,无法对其器型做复原的,我们会全部采集,然后按数量装袋,比如500片装一袋,如果是能做复原的,我们称之为可复原器,它们比普通残片保存的信息更多,为了避免它进一步破碎,需要登记件数后用泡沫纸间隔保护单独装箱。如果这些可复原器里面,有纹饰或者工艺非常特殊的,就要把它单独拎出来做个小件并且附上标签,写明它的各项数据和归属单位甚至出土坐标等,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现场的登记工作是为了之后的室内整理阶段能够更为有序。”考古工地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宾馆,稍事休息,王筱昕还要对每天的考古发现做一个总结。据了解,考古现场的工作结束后,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费时数年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是规模非常大的考古活动,历时5年10年也是可能的。
重视田野并不意味着书斋工作不重要,毕竟中国人一向追求“知行合一”,没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又如何在考古现场中辨别真正的宝藏呢?说到这里,王筱昕澄清了下,考古还有一个大众误区,认为考古学者对于文物鉴赏和收藏总有心得,事实上,“搞收藏的不懂考古,懂考古的不搞收藏”是约定俗成的行规。“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者研究的都是真品,对于辨别真伪其实并不精通;另一方面,作为文物的第一经手人,瓜田李下,避嫌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峡库区“白帝城遗址”考古证实自南宋就筑城把守。
中国考古也要国际化?
考古没有门槛,但如果色弱色盲,可能就无缘这个工作了。原因无他,想象一下在一堆黄土里找到普通土与文物土的区别,没有点火眼金睛的辨别能力,怎么揽这个瓷器活儿?要知道,古代人类活动都依托于地面,不同性质的活动会导致地面被不同程度地使用,最终反映到土地上就是土质、土色的细微差别。对土质、土色的细微判断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通过刮面来判断遗迹现象是考古学家一生都不断修习的课程。
这种对于田野技术的重视,是中国考古从业者在世界考古学界的一大优势和特色。潘碧华向《新民周刊》介绍,中国的田野技术比西方强得多,跟中国的遗址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欧洲的遗址一般都是石头建筑,但中国是以土遗址为主。相当于就是从土里找土,比如我们发掘车马坑遗址,木质马车埋藏地下都化成灰了,你要从土里把灰剔出来,再在灰的基础上还原当时的造型。一开始老外都不相信,觉得是我们造假,直到他们来中国,我们手把手做给他们看。”
当然,国外的科技考古对国内的考古研究影响也很大,“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在科技考古上与国外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鸿沟正在慢慢追平,但潘碧华直言,国内考古界的视野还是不够广阔。“如果了解一下欧美院校的考古学课程表,你会发现他们的考古是全球视野,比如地中海考古、南美考古、东南亚考古等。中国考古界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的材料、中国的历史。诚然,中国的考古资料已经足够多,我们研究不过来了,但本身这方面的研究人才缺乏,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学生出国留学,虽然学习了国外的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但研究对象依然是中国的。”不过,这样的现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人心有所改变,围绕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跨国考古活动,给了中国考古学界一个扩大视野的契机。
“人类对于自己的过去总是充满好奇的,过去的我们成就了现在的我们,还会影响将来的我们。随着考古活动的进行,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文化遗产,文物的出土加深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程度,而许多文化遗产被发掘后建成了遗址公园,又为老百姓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地。”在潘碧华看来,考古学不仅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学科,也是一门仰望星空、探索未来的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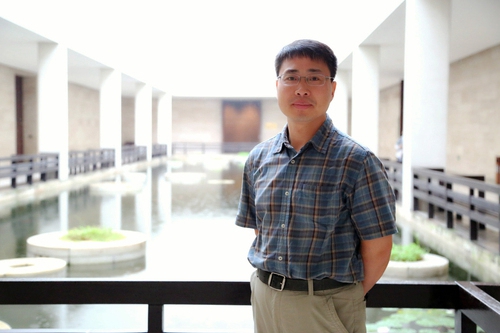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