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终岁末时,沈珉老师寄来书稿《中国近代书刊形态变迁研究》,嘱我写序。慨然允诺之后,我才发现力所不逮。虽说她的研究也可算在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范围内,但立足于符号学对现代书刊形态的审视,我虽很有兴趣,却十分陌生。拖延许久,也只能说点隔靴搔痒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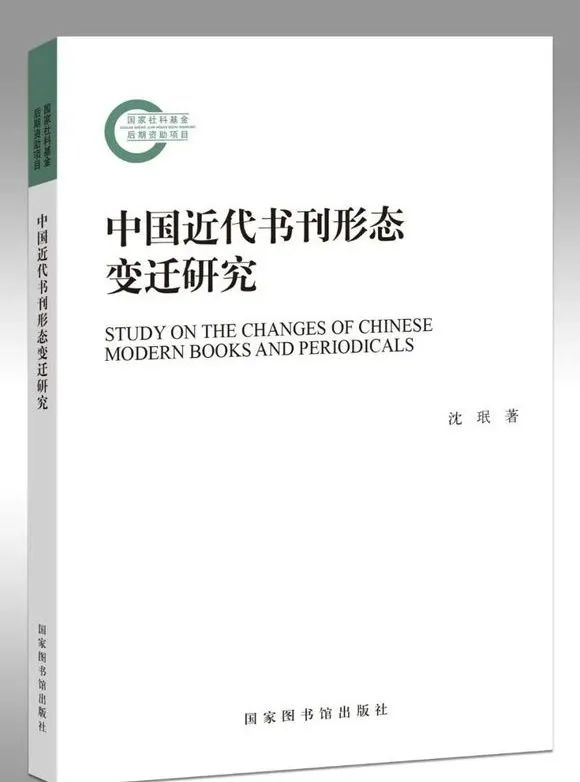
作者在本书中,是将书刊形态作为视觉符号来对待。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符号是产生意义的形式。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书籍形态是传达自己独特意义的,而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近代以降中国书刊形态的赓续与变迁、特殊和多元,更是呈现出新的历史轨辙和时代面貌。作者将书刊形态视为“文化观念的有策划性的表达”,并试图在符号学框架中找到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紧紧围绕“变迁”(涉及“视觉”“设计风格”“类征方式与表征”“设计理念”和“设计民族性的探索与认识”)做文章,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书刊史的研究,这种尝试我认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获得了成功。
在我看来,沈珉老师的探索其实也是对当下出版学研究方法论讨论的一个呼应,是对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史、编辑出版史学术范式转换的一个具体实践。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逐渐成熟,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在出版史研究与新出版史学的相关层面,深入探讨出版史研究在研究视角、理论思维、范式突破等方面对新出版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其重点则是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本人并没有给“范式”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依据他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的阐释,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某一学科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务的看法以及共同的世界观。具体到出版史研究,我们理解为这种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行相关研究时所共同遵循的模式与框架。它是由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构成,它体现了研究者看待和阐释研究对象的基本方式。

按照库恩的观点,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这一新范式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此时科学革命就发生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专家、新闻史学界的朋友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及其团队的新报刊(媒介)史研究。
和新闻史一样,过去的出版史研究主要是革命史的范式,还有现代化范式。近些年这一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展了大胆而有效的探索。何朝晖的《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一文,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历程,分析和评估了已有的各种研究范式,进而重点探讨了社会文化史语境下中国古代出版史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新突破,指出出版文化史的书写将成为未来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重点所在。此外,杨军、王鹏飞等人也在出版文化、编辑学等领域下探究过研究范式转换问题。我和诸位同人一起开展的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史、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专题的探究,都有试验的意义,也得到了张人凤、洪九来等同道的积极呼应。出版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视野的开阔、领域的拓展、思维的创新。显而易见,沈珉老师的中国近代书刊形态研究无疑是属于出版史研究新方法的尝试、新范式的探索。因为有了符号学的框架,作者便能将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书刊形态方面繁乱、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概括出规律,给人启发,十分难能可贵。
多年来,沈珉老师从事中国传统图像与出版图像研究,数年前就出版有专著《现代性的另一幅面孔——晚清至民国的书刊形态研究),发表了许多篇相关论文,一方面努力运用新方法,尝试新范式,探索新问题;另一方面又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建立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作者正值“人间四月天”,生机勃发,充满学术激情,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在坚守中突破,在创新中拓展,在“出版图像”这个值得深耕的领域继续开掘。
说 明
此文是为沈珉教授所著《中国近代书刊形态变迁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1月版)撰写的序言。该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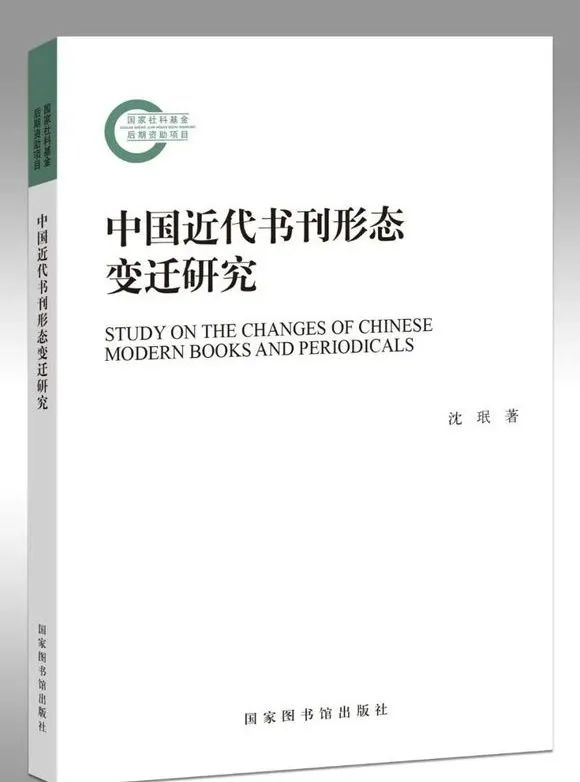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