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华
(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浙江平湖314200)
内容摘要:本文借鉴美国学者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关于历史撰述的方法论启示,主张历史教学要重视史实真相的重塑过程和相关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渗透,提高历史教学的实证性。
关键词:历史真相 认识途径

以史导论的前提是了解历史真相。正确的历史结论必须建立在全面把握史实的基础上。因此,历史教师首先要搞清“教什么”的问题。否则即使运用先进的教学方式也是在误人子弟。但是要弄清历史真相是何等困难。严格地说,历史并无所谓“本来的面貌”,而只有人们所理解的面貌。因为历史事实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着所谓史实的人,即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并不等于史实本身,而只是所谓的史实的阐述者。我们对历史的知识和认识是通过史家的炮制,再又通过我们自己思想的折射而形成的。因此,历史认识的过程充满了主观色彩和断章取义。如何让历史教学更具有实证精神?近读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深受启发,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它们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调子”。如果我们对塑造历史的各种途径之特点有所了解,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关注历史知识形成的途径,博采各种历史认识途径之长,去伪存真,那么我们的教学无疑更能彰显历史思维的过程性,促进学生对历史方法论的元认知,减少历史教学过程中常见的偏执、僵化和盲信等错误倾向,从而营造出体悟、探究和批判的历史课堂氛围。
一.如何看待历史学家的认识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作为后来人,历史学家知道事情的结果,对整个事件有全方位的了解。与历史事件的原始参与者不同,历史学家具有宽阔的视野,即辨别历史上不同的个人的经历之间有无联系和把空间和时间跨度很大的大量零散史料组合起来写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能力。因此,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历史事件本身,而且是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例如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影响,人民版必修一这样表述:“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人民挺身而出,掀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义和团战士不畏强暴,英勇斗争,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实现。”这段话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宏观视野和立场,它启示我们要把历史事件放到历史横向和纵向的时空坐标中去观测,才能看出成因与意义,才能使历史学习变得有条理、有规律,有深广度。但是历史教科书真的把一切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吗?事实上,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人,人在参与历史运动中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学家分析问题有时也难免想当然,把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给想简单了。比如,义和团的动机:是反对帝国主义、排外还是对旱灾的担忧?答案真是唯一的吗?如果我们给学生提供更多不同渠道的史料,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可能更丰富。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历史学家使用的史料。美国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就认为,幸存是不确定的、带有偶然性的、不可预知的。某些类型的证据比另外一些证据更有可能保存下来。除记录在耐久的材料上的证据以外,“容易留存下来的”证据包括当时的人“收集和保存”的资料(如官方档案)。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在其著作中过多地使用容易留存下来的那类证据。就义和团而言,除义和团首领和支持义和团的人写的数百件揭贴及义和团起义结束半个世纪以后收集的口述史资料以外,留存下来的其他所有资料——中国的官方档案文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写的除外),中国文人的纪事、信函、日记及当时的洋人所记的材料——都是从反义和团的角度写成的。大部分拳民是文盲,是按照口耳相传的传统习俗生活的,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没有留下显示这些作用的任何文字材料。因而,在梳理拳民自己的观念时,历史学家不得不主要依靠间接分析法,在讽刺挖苦义和团的材料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帮助学生了解历史学家重构历史的这些特点,学生就不容易盲从教材权威,停止思考,就会有意识多读些其他的史著以重新审视教材观点或者建立自己的观点。若能养成这样的习惯,不仅历史教学死记硬背的面貌可以改观,而且能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培养现代公民的功能。
二.如何看待历史亲历者的认识
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因为历史学家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则不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的意义。所以,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他们不知道局势会如何演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模糊性对他们的意识有非常大的影响,致使他们以根本不同于历史学家事后回顾和叙述历史的方式来理解和认知他们自身的经历。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面临着文化、社会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局限性,导致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所以,亲历者的记述至多是对历史的生动而有趣的描绘,虽能提供很多历史细节和感性认识,但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本身。我们需要对亲历者们各种相互矛盾的记述进行梳理、归类、比较、甄别等研究工作,才能复原出一幅大致接近真相的历史画卷。但是历史课给了学生这样的机会吗?我们的历史教材太追求知识容量了。为此只能把许多历史事件简单化处理。以人民版为例,“义和团”这块内容的课文标题旗帜鲜明地定性为反帝运动(似乎怕学生读了课文后还看不出这一点)。对于历史亲历者的看法,教材只提供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写给德皇的报告:“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其他历史亲历者都“失声”了。根据如此片面的史料推导出来的历史结论真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那么,在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的行动描写多于言语实录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教学呢?除了史料补充呈现外,我们还可以设问:那些人当时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是怎么想的?同为人类,我要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会怎么做?这些提问能促使学生以历史亲历者的角度看待历史,发挥历史想象能力,重返历史现场。那样形成的历史知识可能更有价值。可以说,历史既没有历史学家安排地那么井井有条,也没有历史亲历者叙述地那么混乱和浅显,我们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剥离包裹历史真相的层层“伪装”。
三.如何看待历史神话制造者的认识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一直没有停息。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历史神话制造者的目的不在于加深历史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根据现实的需要,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越容易被“神圣化”或“妖魔化”。大众记忆——人们普遍相信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往往与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究各类史料证据后确定的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是大相径庭的。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历史学家非常重要,但在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更有可能被契合其先入之见的历史——他们感到适意和他们所认同的历史——所吸引,而对更客观的“真实”历史不感兴趣。我们的学生就是普通人,他们容易被历史现象迷惑。涉及历史题材的诗歌、戏剧、小说、艺术和电影对历史的神话化,这种形式比历史著作更容易使历史形象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教师需要运用严谨的史学方法帮助学生从“穿越剧”那样的“伪历史”中走出来,建立起真正的历史对话。这可是历史教师的看家本领。如果只能照本宣科,那么历史教师的位置可以被任何人取代。
以义和团运动为例,评价其历史地位是个极有挑战的难题。因为只要中国人对西方或他们自己的历史抱有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义和团就会继续扮演特殊角色,充当制造神话的材料。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代表帝国主义,又代表现代化,前者是坏的,后者是好的。两者都是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攻击目标。因此,历史上的义和团具有一种内在的潜力,可供后来的中国人充分挖掘和利用。
值得指出的是,一流的神话制造者绝不会完全无视历史事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义和团的神话化达到新高潮的情况下,媒体向中国公众展示的义和团形象也不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67年春红卫兵活动高潮时期为攻击刘少奇而写的介绍红灯照的文章,广泛引用了亲历者的记载、口号、歌曲以及其他资料。《光明日报》甚至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录自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并注明了出处。神话制造者往往在引用资料时断章取义,以支持自己的论点。《光明日报》史料专版上,有一条用于说明义和团是英勇无比的战士的史料:“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于法,无不视死如归。”原著中紧随其后的一段话未予摘录,内容是说,义和团不怕死的原因之一是,当神一附体,他们进而会进入神志恍惚的状态。如果神附体是他们具有勇敢精神的原因之一,会使他们的爱国英雄形象大打折扣。
历史教师有时候也会成为历史神话制造者。他们在历史课堂上犯的也是一流的神话制造者的错误:阉割或者粉饰历史。某教师在讲历史人物史时喜欢引入历史人物青少年时代的小故事。他认为这既增加了趣味性,又进行了道德教育。殊不知很多小故事都是后来人为了神化伟人杜撰的。牺牲了真实的历史课还剩下什么?历史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应该对历史多一份敬畏!
四.结束语
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注:但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也制造神话,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也完全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写入历史)。但三种“认知”历史的路径其实对历史教学都有启发。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学会倾听各类历史亲历者的声音,具备历史神话制造者不断开展时代与历史对话的意识。这些难道不是学生应该学习的?建立对历史知识考证的意识,我们才能从庞杂的史料与偏见的迷雾中走出来,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虽然,我们不可能全面恢复义和团运动的原貌,但综合运用多种认识历史的途径,我们的确能够恢复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能以大体上接近事实的语言讲清楚历史真相与神话化的历史和故事化的历史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不是全部历史的亲历者,却是自身历史的亲历者。这种个人的主观经验是我们评说和省察与众不同的历史经历的基础。我们不仅知道运河,而且了解挖运河的人们遭受的痛苦,如果我们自己经历过类似的痛苦,将使我们更容易了解别人的痛苦。总之,历史教学要重视史实真相的探索过程,重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渗透,落实历史教学的实证目标。
优秀历史公众号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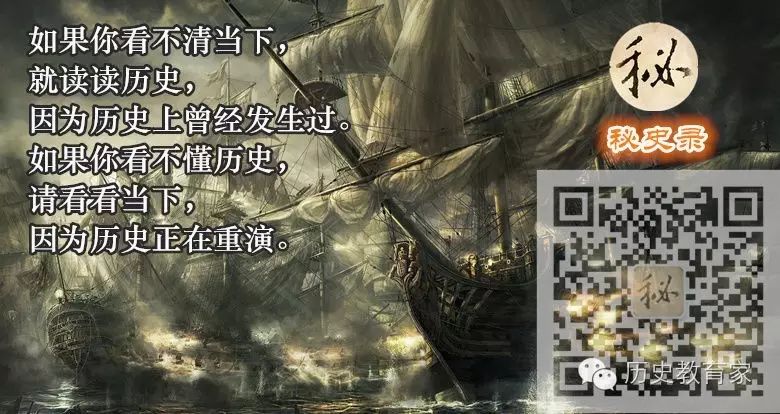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