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68.00元
先从书名翻译中的“主义”与“问题”谈起吧。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史家的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的原书名是“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中译名把“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都置换掉了,这无疑是很成问题的,无论是“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还是“兴起”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这里的不可置换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相信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不是译者的问题,那么就姑且看作为当代词语研究和翻译研究贡献一个有点小意思的例子吧。
接下来,也顺带再谈两个也纯粹是词语学的“主义”例子。
一是“New Liberalism”,这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在这里被译为“新型自由主义”,显然是为了与“Neo-Liberalism”被译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译法区别开来。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不仅在时间上相差大半个世纪,在思想诉求上也完全不同,都译为“新自由主义”显然会造成思想概念的混淆;而且在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思想舆论场中,不管批判还是赞成,后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备受瞩目,而先在的New Liberalism反被遮蔽与遗忘。但是对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后者所具有思想与观念意义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本书译者把New Liberalism译为“新型自由主义”,站在New Liber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也有人把Neo-Liberalism 译为“‘新’自由主义”,以示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区别,从严格的词义内涵上说应该是更为准确的,但是流行的译法已经难以被改变过来了。
二是“社会主义”,也就是“Socialism”与“socialism”的区别,作者在“缩写表”中说,前者“涉及该词的教条的、正统的以及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后者指的是该词的一般意义,即本书第二章“自由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意义;译者在本页“译注”中说把前者“译为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完全正确,也非常符合我们所熟悉的语境。
再回到现在书名中的“进步主义”这个概念。我想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几位同人办的报纸)发表的《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就是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当时我特别关注的是,“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对穷人的苦难麻木不仁,这是美国社会能最终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几年前,政治学者钱永祥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借鉴美国进步主义的经验教训诠释八十年代改革运动的价值观,不仅在历史上可信,并且有助于今天中国的社会逐渐找到一种“平民的理想主义”来恢复道德生机。在以“进步主义”置换“New Liberalism”的语境中,这也是颇有启发性的。弗里登在该书“中文版前言”的开头就讲到,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十九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后来在第一章也继续谈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改革问题的关注,是进步主义思想总体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还只是一股潜流,之后逐渐壮大,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导因素”(34 页)。这些涉及“进步主义”的论述,或许也可以作为对“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这个书名的一丝安慰吧。
迈克尔·弗里登的这部著作以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出现与发展为论述核心,打破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纯理论路径的桎梏,从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渗透、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复杂语境、社会历史背景中出现的改革议题与社会舆论中的激烈论争等各种维度的相互碰撞中,重新诠释新型自由主义的思想轨迹与核心价值,是一部关于英国新型自由主义发展的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在我看来,该书最具思考魅力的是,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作者深刻地论述了存在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与社会改革议题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影响和意义,使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重新被置于它们所赖以发生和成长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这是一种充满经验实证方式和历史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也成为对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社会改革与进步运动作思想分析的重要思想史资源。《英国历史评论》的推荐语说该书“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我相信对正在思考改革开放四十年议题的读者来说,这种思想、现实、学术三者交叉结合的思考路径本身就很值得借鉴。
弗里登在书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它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它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该规划为未来,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可能是20世纪英国在国内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20页)。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认为,“简言之,福利国家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1914年之前进入公共生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对于它们来说,使民政秩序获得稳定的前提,即普遍的医疗服务,老年退休金,失业与疾病保险,免费教育,公共交通运输补贴等等条款,不是代表20世纪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19世纪晚期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成结果”(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10页,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5月)弗里登念兹在兹的新型自由主义对英国社会进步的影响问题,这段论述可以看作历史学家的简洁回应。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13 年5月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发展现象?弗里登告诫我们,要把注意力从传统的政治思想人物、那些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上移开,转而关注发生在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各种讨论,应该阅读的是书籍、报纸、期刊、议会辩论等各种资料。像L.T.霍布豪斯和J.A.霍布森这样杰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是置身于更大的群体并且受那些群体影响,因此更要关注积极活动在各种松散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直面工业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代价,并且专注于减轻其弊病的方法,贫困、失业、住房、卫生、疾病、教育等社会问题都在他们的不同视角中得到表达。他最后强调霍布豪斯和霍布森都不是抽象的理论家,而是一直致力于解决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21页)。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思想舆论场,在学院体制中自命为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者的学者们或许也应有所思焉。
在上述的社会与舆论氛围中,新型自由主义发展出四个核心观念,并以相互关联的方式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这四个核心观念是:一、必须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抑制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和提供机会;二、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产生一种基于相互援助的共同体精神;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有赖于一种广义的福祉观念才能实现,这种福祉观念把个人的发展和完善置于核心位置;四、国家是实现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不再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他强调新型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和当年那样具有新意,表明恰当的共同行动并不必然会缩减个人自由,反而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同上)。

迈克尔·弗里登
讲到这里,弗里登很自然地把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s)拎了出来,认为它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变得枯竭;它以一种挑衅的、夸张的、过度竞争的方式挑选出自由概念,牺牲了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还用狭隘术语来阐释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而没有把宽容、反思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包括在内。但是他同时也指出新型自由主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对国家的力量和意图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对专家的信任产生一种旨在引导全体人民走向可欲目的的温和家长制;它的和谐概念过分一元化,低估了任何社会的内在多元性。更重要的是他准确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无力感:“在越来越被标语和粗俗修辞所主导的政治世界中,它无法特别有效地向更多民众传播其观念。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不愿在牺牲理性的情况下依赖于情绪化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缺乏激情。……但他们绝不使用某些在政治世界中常见的方法,即煽动和激起会造成不稳定的情感,如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语言。”(23-24页)在自身的弱点与难以消除的无力感之间,新型自由主义的真实状况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在日后的传播、发展的命运中必然备受曲折与磨难。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初叶的思想发展与社会改革实践可以证明,“新型自由主义是一个明显具有融贯性和针对性的观念维系。它专注于具体的社会弊病而又没有陷入乌托邦主义,但它的社会观点和计划是积极而有力的”。在今天,弗里登承认自由主义家族可以存在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每一种自由主义都必须论证自身的正义性;他更为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静止的学说,也不是一套普适的信念,必须坚持发展、变化、竞争和自我批判的精神(25页)。
接下来作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回顾新型自由主义对当时推动社会改革、形塑福利国家的影响时,一方面,由于新型自由主义的观念和纲领早已融入广泛的政治话语和政治议程之中,因而难以发现它的直接影响力的依据;另一方面,学术界没有多少致力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曾经产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新型自由主义,竟然通常被政治思想研究者所遗忘。另外,新型自由主义自身是如何蜕变、发展的?有一个学术争论的焦点是,有观点认为这要归功于在工党那里达到顶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政治竞争迫使自由主义向左转,为自由主义的先进派别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
对此,弗里登则指出,“本研究的主旨是表明:从智识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完全是自由主义自身促成了其政治信条的转型,而且它也有能力这样做(尽管人们自然无法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开放社会中观念之间总是存在交流和互换)。如果所追问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究竟保有连续性抑或发生了断裂,那么,答必定是前者”(53-54页)。为了证明这个主旨,作者展开了有关英国社会政治与政策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这是占据全书最大篇幅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部从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切入的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社会改革史。
对今天更加关心社会改革与进步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思考和理解新型自由主义与英国式的社会改革的内在联系:“新型自由主义者所创建的思想体系,显然是针对那个年代的直接社会问题。这种思想体系持续表达了他们对具体事务的兴趣,以及促进当前社会有所改进的必要性。他们一直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提议,承认任何改革都必须在压力和局限之下进行,以及改革必须满足的条件,并相应地指出了行动的方法”;“即使实际的立法并没有体现他们最先进的观念,但在现代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与政治行动中的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的重建过程中,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此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总体探讨已经完成了”(340页)。
弗里登在全书的“后记”中引述了霍布豪斯的一段很长的话,其中有几点意思比较重要:当政治斗争只是围绕着私利的漩涡,原则当然是不重要的;拥有并知道如何运用原则的人,是消除社会偏见和政治阻碍并为改革铺平道路的精神领袖;未来的进步希望有赖于那些与国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思想者,他们会以现代环境要求的方式重新表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弗里登赞同,并已从多种角度论述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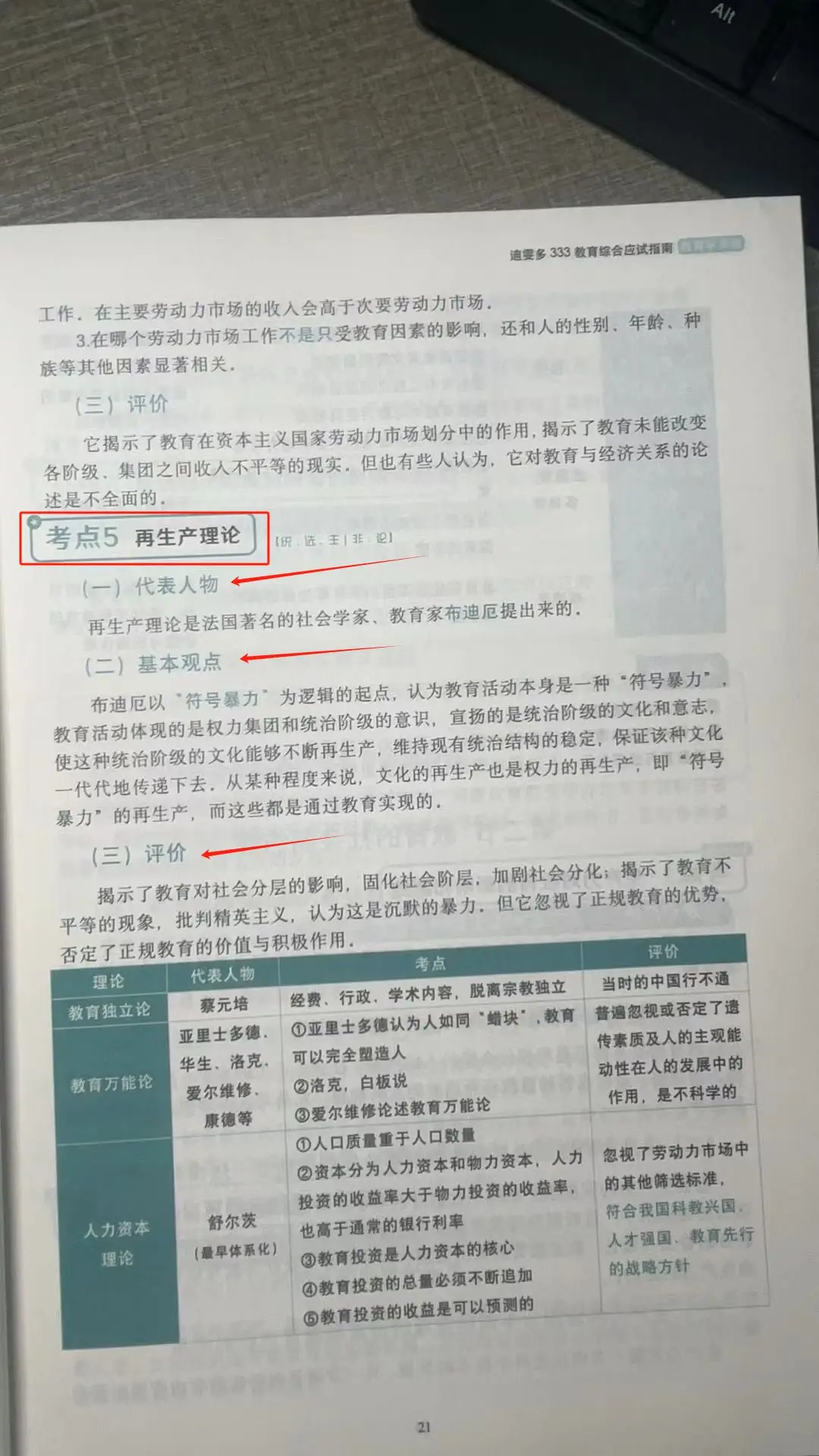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