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2015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的文章,认为通过六普资料与五普资料的比较,相对于2000年中国社会结构,2010年中国社会结构中“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李强认为,倒丁字型结构及其必然导致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如果想从结构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扩大中间阶层数量,改变倒丁字型结构,办法就是改革户籍制度与增加城市容纳力。对于这一判断与分析,我有不同看法。
中国社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例外
李强其实也很清楚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下面一横与上面一竖不在一个结构里,他说:“实际上,中国是有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而不是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 。实际上,李强提出倒丁字型结构的2005年时,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有了极大调整,决定农民工能否进城的主要障碍早已不是户籍而是收入了,或者说是市场因素了。只要农民有了足够收入,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城市买房生活。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不过,现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中,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大都已清除或正在清除,而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制度仍然大多保留,比如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之所以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是因为土地包括宅基地是农民的最后退路与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应该允许进行交易的。基本保障的交易对城市人来讲,也许只是多了一个节假日到农村看星星的休闲去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却可能在进城失败后无路可走。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保护农民的体制。
正是农民有农村这样一个退路,当农民家庭认为进城有更多机会时,他们选择进城获取收入,而当他们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就退回农村。农民有农村这个退路,就使得独立运行的农村社会结构避免了与城市社会结构在同一个结构中的“结构紧张”关系。正是有农村退路,进城农民就可以在城市一搏,同时,正是有农村退路,进城农民就不会失望而要努力打拼,他们在城市获得的收入也许过不好体面的城市生活,却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的生活。
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规模巨大的贫民窟人口,若对这些国家的城市家庭进行收入统计,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例外都有一个底层的长长的一横,而其上面也一定会有一个高高的一竖,这样的倒丁字型收入与社会结构不是罕见的,而是普遍的、一般的,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结构。
相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例外。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结构中因为存在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这个农民阶层处于社会收入与声望的底层,似乎农民阶层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底层的长长一横,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实际上,因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保护,而使城市与农村成为两个相当不同的社会体系,也正是因此,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有效地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及由此造成的倒丁字型收入与社会结构,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城市普遍存在的结构紧张,以及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紧张所放大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从而使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世所罕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保障农民返回农村的权利,是中国得以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诸种问题的成功经验
显然,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也就不存在所谓倒丁字型结构比金字塔型结构更坏的问题。反过来,当前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一方面农民自主进城,城市对农民开放,一方面规制资本下乡,农村对城市资本有限开放。这样一种体制之所以可以成功,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印度城市正规就业机会只有大约10%,并非是印度对劳工就业的保护不力,而是由印度所处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无一不是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中国的优势在于,通过保护进城农民在农村的退路而缓解了城市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压力。如果一方面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一方面又让进城失败的农民不再可以返回农村,就必然出现城市倒丁字型结构,就必然导致结构紧张,这样一种结构就必然会放大各种危机以致危机不可收拾。
将作为农民最后退路和保障的返回农村的权利制度性留给农民,不向城市开放,不向市场开放,不允许农民失去返乡权,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得以成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诸种问题的重大经验之一。基本保障不允许交易,要靠国家力量来保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却常成为易被忽视的常识。
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向纺锤型结构转变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对农民返乡权的保障,甚至通过国家对农村的大规模财政投入来解决农民在农村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了农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生活的一定品质。农村生活本身并非倒丁字型结构底下的一横,相反,农村生活品质虽然低于城市体面安居的生活品质,却要远远高于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品质。
从进城农民的角度来看,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进城农民无非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另一个结果是进城失败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会有相当部分农民进城失败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进城农民,他们面临的是继续留城还是返乡的选择。这样一来,在农民体面进城和农民进城失败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可选项,即农民体面乡村生活的选项。农村生活并非最坏的,农村收入比较低,消费也比较少。因为进城失败农民可以选择返乡,中国在城市混吃等死没有希望难以体面生活的城市底层阶层就必定是一个很小的规模,而城市体面生活的群体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而不断扩大。这个城市体面生活的群体也可以分为一个相对较小的高收入层和一个相对较大的中下收入层。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就因为底层比较小,以城市中下收入阶层与农村中间层为主的中间阶层相对庞大,而城市上层也注定比较小,而形成一种纺锤型结构。
这样一来,整个中国社会就可以分成为可以相互交流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均衡的四大阶层,即城市高收入的上层,城市中下收入的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以及城市低收入的底层。正是通过农民进城和返乡的调节,而使四大阶层尤其是后面三个阶层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
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越来越多农村中间阶层向城市中下收入群体的转变,从而将当前分化在两个不同结构中的中间收入群体通过结构性转移而最终聚合到一个结构里面来了。只有当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以后,农村中间阶层才可能完成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转换,中国社会结构才可以统合到一个结构里面,从而形成当前一般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而因为大量农村人口已经转移进城,国家财政也有能力对城市少数下层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就使得之前用于保护庞大农民群体的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城乡二元体制变得不重要起来,中国城乡也就有了一体化的条件。
也许,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具有同样的故事:制度、市场等等,中国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在讲城市发展的市场故事的同时,又讲好了农村保障这样一个非市场的故事。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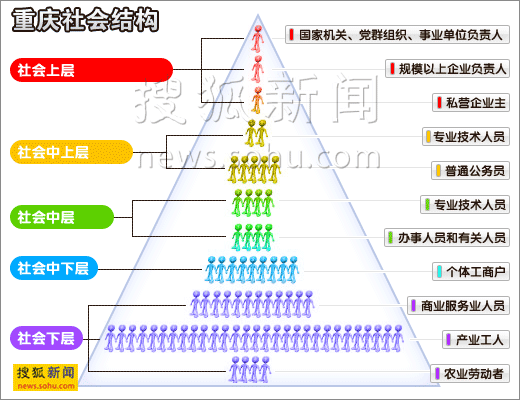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