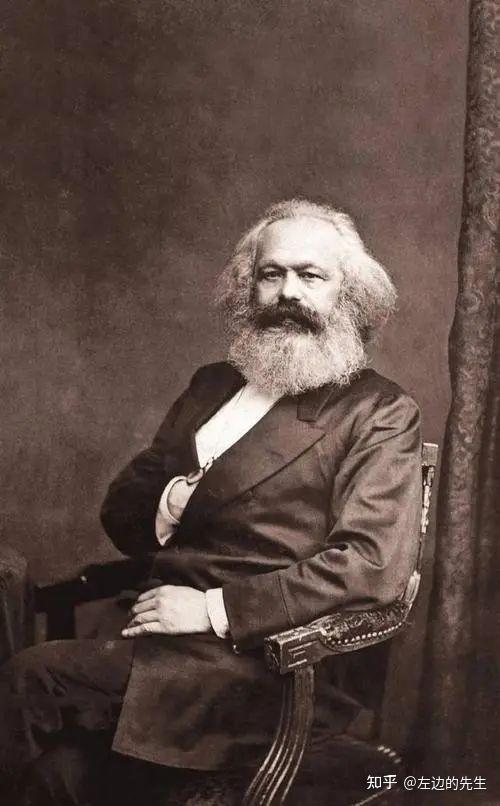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便会关心你”,相信许多人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在CN,不论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口头教育还是教科书的书面教育,我们都能看到其在宣传上着重强调要“关心政治”,如此深入、全面的宣传,为何我们周围依旧有许多奉行政治冷感主义的人呢?我这里主要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出发进行探讨,不过多讨论具体层面的施用。
一般来说,在现代,奉行政治冷感主义的人有两种,一是处于意识形态阶段政治冷感的人,表现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知道要这样做,另一种是现代犬儒主义阶段(即日子人)是——他们明知如此,但他们照旧为之。
意识形态阶段政治冷感的人,虽然受到表面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强烈熏陶,表现出“知”的全面认同,但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实际的撕裂让他们又归于了政治冷淡当中;而现代犬儒主义阶段的人,则附加了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但他们又并不会展现出古希腊犬儒主义的特征——不打算追随任何人,意识形态的残余依旧在指挥着他们,他们在“知”的怀疑中无条件追随,又在“行”的付诸上完全断裂,沦为一种好似启蒙了的虚假意识。二者虽然在认识层面不尽相同,但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却是一致的。
上述二者的第一种政治冷感的情况是非厌恶状态的政治冷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揭示了一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现代的抽象二元论,在这种二元论当中““政治国家”就表现为“物质国家”的形式,发展成为“同现实的人民生活并行不悖的特殊现实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形式上的分离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分离,带来的结果就是个体的二重化,即个体同时作为国家的成员(公民)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市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得不将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彼此分离的导致政治国家的公民角色也是同作为市民社会的市民角色彼此分离的。二者在一种集体幻觉中似乎存在着同一,存在着同一个主体,但这种主体具有本质上不同的规定,因此实际上这里是双重的主体。也就是说,个体实际上处于一个双重组织中。正是这样的一种双重分裂,使得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的个体,他需要承认普遍利益和公共道德以及法及政治实体的权力;而作为私有制下的私利的个体,他则受到利己主义原则和物质利益的支配。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是二重分离,为什么不是既关心政治国家也关心市民社会的情况成为普遍状况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市民社会视作国家形式的物质基础,而国家是市民社会二重化的结果,它只是市民社会保障特殊利益所必然需要的普遍利益的外壳。因此,国家并不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的可能,而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在这种分离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对于个体来说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市民社会中的人才体现为现实的人,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都是市民社会利己主义原则的衍生,在这种衡量当中,个体自然首先选择了市民社会的角色,冷漠了政治,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非厌恶状态的,由“现代”国家属性所自然产生的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是厌恶状态的政治冷感,是在基于前者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的前提下,多数是认知到虚假的政治化的影响,即政治生活的实践同它的理论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政治理论,在现实实践中发生了矛盾的情况下产生了厌恶状态的政治冷感,现代犬儒主义者(日子人)一般表现为如此。政治解放的不彻底,表现为体现着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范畴也依然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些范畴事实上只是特殊利益的反映,而并未真正代表普遍利益,这使得宣传的高度政治化和公民角色的无力的强烈对比,使得当中的大多数人在理性不在场的思辨当中产生了对政治的全盘厌恶。鉴于特殊原因,我不会在这里对这种的产生进行过多讨论,诸君可以沿着我说的线索自行进行观察、思索。
所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使得个体被撕裂为了市民与公民,过着双重的生活。他的类生活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之中,在此他只能作为抽象的主权中的“平等”的一员实现他的被“宣告”的所谓的“普遍性”,但是在现实的市民生活之中,他又要作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过着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对立的生活,与他人处于持续的对立和冲突之中。
那么,这里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处于未分离状态,人们就会关心政治了吗?就不会政治冷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说是不完全否定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指出:“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人都是政治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中世纪是现实的二元论。” 在前现代的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中,国家和政治制度与人民的生活直接同一,市民社会就是“国家的市民社会”,其本身就具有政治的属性。但是在中世纪,普通的农民、纺织匠、铁匠这些人难道很关心政治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同一,是政治等级与社会等级的同一,是政治制度与人民生活的直接同一,这种未分离的状态其实是“不自由的民主制”,在这里,人虽然构成了政治国家的现实原则,但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他们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现代国家所已经达到的政治解放的高度。这种同一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侵凌,他们依旧不是行使着政治权力的主体,而是被政治权力介入的主体,这种同一不在于行使,而在于介入。
简单了解后,我们可以认识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同一是一种前提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完全的充要条件。那么,究竟既然单一的同一还不够,那么还需要怎么样的一些条件呢?是福利国家?是议会选举?都不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恰恰是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对立,是逻辑上的A与非A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可能通过任何逻辑中项来中介,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的彻底解决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以使得对立的双方获得真正的统一,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为此所提供的答案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质料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
真正的民主制必须是一种自由的民主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民主原则的主张:“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 只有作为人民的自我规定的真正的民主制才是以人自身作为出发点的,并因此才构成真正的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所主张的又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民主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所设计的代议制民主还是古典国家主义者所设想的直接民主制,在实际上都已经预设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在这一点上,共和制和君主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争论实质上是抽象的国家范围内的争论,现代国家的政治解放也不过是一种半自由的、局限在抽象的政治国家范围之内的“解放”。
故而,分离问题的解决因此并不是简单地归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未分离的状态,真正的民主制不仅要在自身之中保存现代国家所已经实现的政治解放,还必须进一步建立在对作为整体的人的自由的确认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同一的升华只有在‘人’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时才可能,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真正的民主制”中包含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同一不仅要求政治国家的解体,也要求市民社会的解体,即政治国家的去政治性的和市民社会的去私人性,正如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灭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消灭国家,国家将失去它的政治性质,成为真正的国家,政治不再构成国家自身,而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的一个环节。(注意,去政治的不是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不能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的旧唯物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待,这是一种片面的幻想。)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也将会消除它的市民的即私人的性质,成为真正的社会,各个特殊领域的私人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
在这里,真正的国家就是社会,正如真正的社会就是国家一样,国家与社会在此合二为一,在这里,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在这里,完整的人才得以在他的全部生活中自由地发展自己全部的本质能力;在这里,自由人的联合成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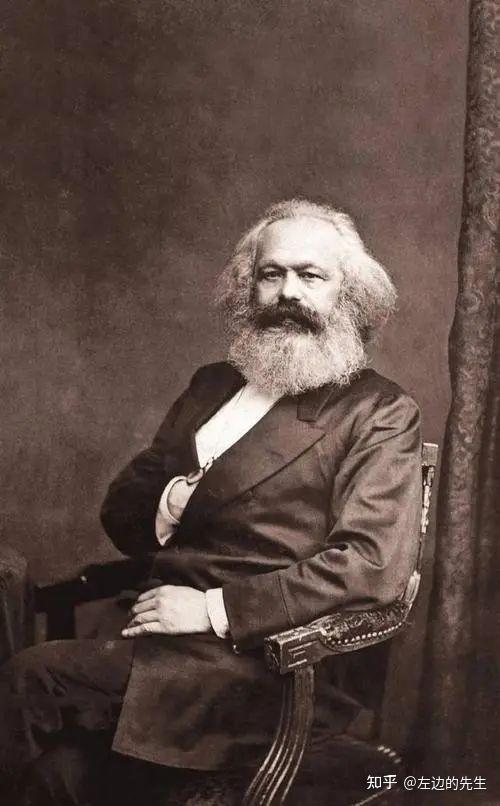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