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道德时代,那个自觉的、高尚的、自我感动的时代正在加速离我们远去。另一个更真实、更势力、更尖锐的时代正朝我们走来。
相比于道德的消失,我们更应该对它的产生感到震惊——人类是一个多么自私与贪婪的物种呵!但他们竟然可以因为一套松懈的、笼统的陈词滥调而收敛自己的吃相,这个力量到底来自何处?!
其一,作为自我超越的道德感。
道德感的本质是一种意志自觉。
人类所有有意义行为的动力因有两种——欲望和理性。奇怪的是,这二者驱动下的行为所触发的快乐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欲望驱动下的行为,其带来的快乐是即时的、稍纵即逝的,甚至会给人带来后怕、迷茫甚至虚无和不安。欲望来自身体内部,是我们的一部分,人类不得不接受它的安排和奴役。但是它本身也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具有天然的自我反噬倾向,这是隐藏在我们身体内部的自杀性力量。先民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可以抑制这头危险野兽的力量——理性,它比欲望看得远、想得多,它能意识到纵欲的危险。理性驱使下的行为所带来的快乐更持久、更真实、更有安全感。
从起源来看,道德感是人对自我的否定和压抑,人确实是自私和贪婪的,但它同时是一种生命,既如此,安全、长久地生存和繁衍必须优先于纵欲,这才是人性中更根本的要求。
由对欲望的恐惧(这种恐惧久远到疑似天生)发展而来的对自我的警惕和不信任——这就是道德感的来源。用理性的势能束缚欲望,以一部分快乐为代价换来必要的安全感,这是道德的基本特征。
道德感是人类特殊的自我保护和发展机制——它要面对的威胁来自自己,它要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认可,通过自我破坏来实现自我保护,乃至自我超越、自我改造。人类或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物种:通过自我否定获得成就感,对人类来讲,敢于与自己为敌,否定自我的人才是人中之杰,因为他实现了自我扬弃。
其二,作为自我类比的道德感。
《孟子》中记录了一件事:齐宣王曾经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准备杀掉,他心生同情,但又不愿意耽误祭祀,于是命令把牛换成羊。这件事被传为笑柄:把牛换成羊,只不过换了另一头无辜的生命去枉死而已。
但孟子却从中看到了道德感的另一起源——“不忍人之心”,即我们所说的同情心。孟子还发现,触发同情心的关键在于“在场”:齐宣王之所以想要救这头牛,只是因为他看见了;他之所以忍心用羊来换,是因为那头羊在当时为止只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抽象概念。孟子由此得出了一个乐观的结论,就连政治家都能保有这样的“仁之端”,那岂不是所有人都有成为道德家的潜质?
所有的生命都有保存自己的欲望,求生欲使得我们和其他生命体具备了共情的可能性。
当我们直接目击其他生命陷入危险或痛苦时,那种身临其境的震撼使我们发动回忆,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到对方的处境,由此生发出助人的意识。孟子还举例说,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颤颤巍巍地走到井口,这一情景任谁看见都会下意识地伸出手护住孩子。这类举动几乎是本能反应,在行动前那一刹那根本来不及权衡利害。那么这个本能反应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只好猜测,当自己毫不犹豫地伸手帮助他人时,其实内心里完成了一次自我救助,那个救助对象实际上是你自己投射在那个处境里的影像。
除了上述这种无意识的助人心理,还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我类比。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康德所说的“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就属于这一类。
不得不承认,康德的说法似乎更冠冕堂皇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拿自己的欲望(好恶)去做类比;而康德希望我们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公共尺度,用来不偏不倚地自我衡量、自我要求。但无论是以自己的欲望揣度人心,还是以自己的理性做人世间的大法官,无非都是自我类比思维的产物。
道德家们似乎不约而同的发现,美德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去功利性,即无私性,而或许感同身受(无论是下意识的感性代入,还是深思熟虑的理性推演)才是最大限度的无私(虽然这其中仍然带有必不可少的自私成分)。

其三,作为社会准入机制的道德感。
道德或许是维持秩序成本最低的社会机制了。
法律也起到相同的作用,但是法律有两个缺陷:首先其社会运营成本较大,无论是监督、举报、裁决、处罚,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成本。当没有涉及到较大的利益纠纷和意气之争时,一般人不会触发法律机制。法律因其流程繁琐、机制臃肿,在诸多生活细节中留下了秩序空白。其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恐吓装置,它通过剥夺和惩罚来威胁人们。虽然,它也可以成为我们保护自己的工具,虽然它的底线非常低,我们一般不会触犯到。但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竟然悬在一个恐吓之网上面,怎么说也有点不太舒服。
道德正好弥补了法律的缺陷,它扩大了社会权力的管辖范围和渗透深度,使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有规矩可循。而且它不是用惩罚来威胁我们、逼我们就范,而是用所谓的“高尚的境界”来引诱我们、鼓舞我们、提携我们。其运营成本极低,且更能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舒适感。
道德所谓的“高尚境界”,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感动、自我认可——成功地压抑了自我的人成为了新人,在这个境界里,他超越了旧的自我,获得了理性的重新认可。以前他是欲望的奴仆,现在他皈依了理性,后者才能给他归属感和安全感。我们把这个叫做“内心的宁静”。
这是道德给我们的许诺和奖励,而法律给不了这些(法律只能提供在外的、事实上的安全,而不能像道德一样,由于对它的遵守而引发内心的宁静与喜悦)。
当然,除了许诺和奖励,道德也保留较温和的惩戒权,这就是“放逐”。道德是一种全社会默认的、自发遵守的规矩。你不遵守它,意味着你拒绝融入社会,其他成员逐渐会将你当做异类排除出各种社交圈子。当你发现自己被孤立、被排挤,你知道到的正在放逐你,但是只要你愿意体会其中的准则并愿意效仿,放逐令又会逐渐放松,最终消失。作为一种社会准入机制,这种惩罚相比于法律来讲,已经相当温和了。

道德是这样一个悠久的、高明的、如沐春风的东西,它让我们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可现在它正在无可挽回地式微,变成“迂腐”、“不识时务”的代名词。因为人类行为在一个新的领域找到了另一套价值逻辑。
现在,塑造人类行为的装置只剩下律令(法律、政令)和市场规律。只要不违反这两种装置,社会就会为一个人提供正反馈,它们正在塑造一种全新的人。
律令在每个文明时代都存在,只不过由于通讯和管理技术的提升,现代政府把它变得更加绵密了而已。第二种力量即市场经济的导向和要求才是削弱甚至替代道德的新力量,说白了,这种新力量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道德最大的区别是前者鼓励欲望,而后者压抑欲望。
如上所述,对欲望的警惕一直是道德的重要起源,道德也因此是以“罪感”为背景色的。在罪感的羞辱下,人心中的任何欲念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任何一个鼓励欲望的行业都会受到鄙视,商人在很多早期文明中都要遭受白眼,因为他们怂恿人们去破费和享受;那些以便捷和轻松为目的发明则被斥为“奇技淫巧”;就连一些追求自身权益的行为也会偶尔被指责为“斤斤计较”。节制、清贫、忍让、苦修,这才是道德社会中标准的“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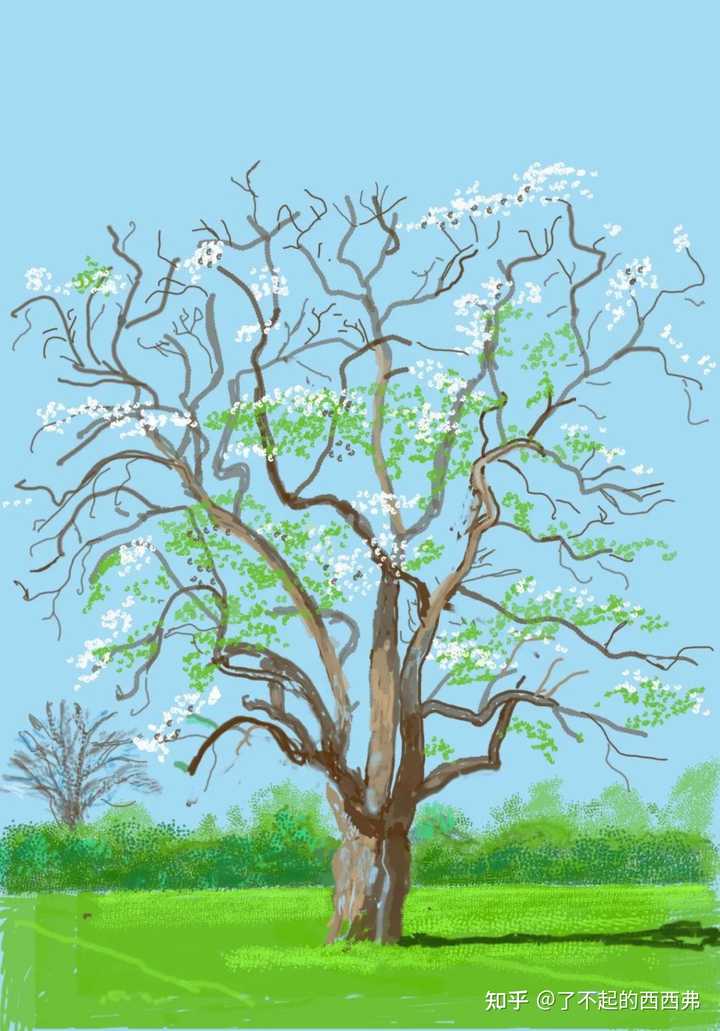
然而,资本主义市场不欢迎这种人,他们没有斗志,没有出息。市场自有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它以人类欲望做燃料,驱动社会的运转,神奇的是,这么多危险的欲望在其中聚合冲撞,创造出来的竟然不是邪恶和危险,而是真金白银的财富!
欲望从罪恶的深渊变成了转化财富的矿产,作为自我超越的道德失去了它的敌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传统道德侧重保护弱者,解救他人。资本主义精神鼓励竞争,而竞争的本质就是削弱他人、壮大自我——助人成为了妇人之仁。
助人从一个高尚的本能反应,变成了违反市场行情的行为,作为自我类比的道德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
有人会说,新环境会催生出新道德,来配合市场的需求,比如诚信、平等、公正等等。但这已经不是原生道德,而是次生道德,一种类似于社会契约的东西,它并不根植于人性中的原始情结,而只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策略,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所谓的“大格局”,其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换来“大利益”而已。

在抛弃了道德的后道德时代,我们堕落了吗?
“堕落”这个词带有很明显的道德色彩,我们站在道德时代的立场去评价一个无道德的时代,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堕落,这么形容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却胜之不武。站在一种道德体系中指责另一种道德体系是不合法的,站在道德时代去批评另一个没有道德的时代没有道德,这顶多算是全真但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
那么,我们该如何站在道德之外衡量这个时代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