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历史著作,在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中享有盛誉,即使在作者逝世近30年的今天依旧热销不已(当当五星好书,页面累计评论6760),这部被称为“力透近代社会风云的精湛之作”的作品,就是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先生晚年精心编撰的一部哲理性历史著作,全书共20章30余万字,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和全新的史学视角,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方面面展示了近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
今天,小编邀请你一起,读一读这本好书的精彩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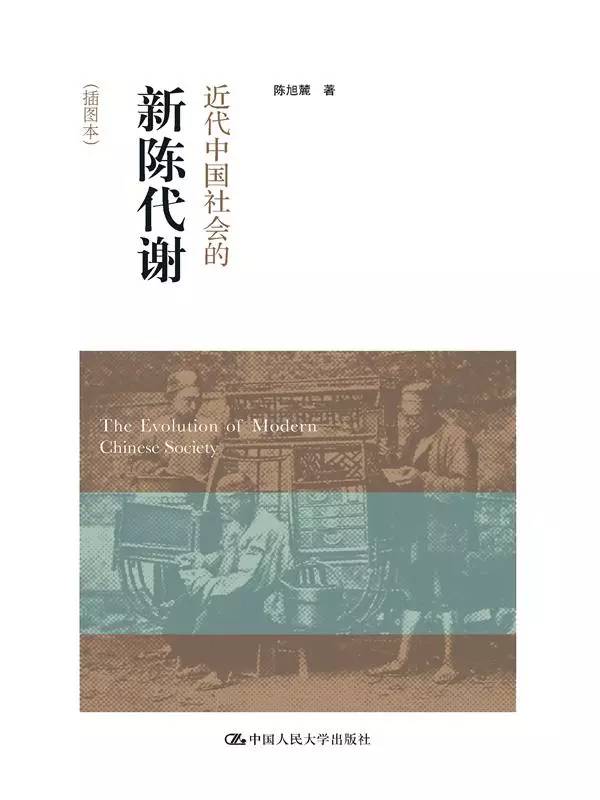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
该书修订版精装本即将于9月上市
“中等社会”一词,于古无征。它是中西社会冲撞、交错与融合的产物, 是20世纪初年的革命党人所着力论说的一个概念。在这一概念背后,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和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它崛起于庚子之变后,不仅反映了那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裂变与改组,而且反映了在欧风美雨浸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 革命党人出自“中等社会”,又代表了“中等社会”。当他们用这个概念把自己同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同时体现了“中等社会”自觉意识的开始。 它的出现本身体现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实力的消长,并很快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
在19世纪,曾有过以上等、中等、下等名人名事的说法。如太平天国时期,绿林人物张嘉祥就说过:“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安枕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广西天地会民谣,流传颇广。张嘉祥后来投顺了朝廷,并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敌手之一。有人因此而不愿意承认这种饱含反抗精神的话出诸他口,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这里所区分的上等、中等、下等主要是以贫富贵贱为天然尺度,着眼于社会个体,因而它仅仅是直观的结果。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中等社会”则不仅仅是直观的结果,而且是理性抽象的结果。义至而后名立, “中等社会”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概括了操各种不同职业而居于相同社会层次的人所构成的复合体,它着眼的是社会构造,因而它具有比前者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内涵。就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而言,“中等社会”相当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属于“中等社会”。但出现于20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又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当时人说:
“
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鸠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
这段话虽只以湖南一省的情形为言,但它对“中等社会”所做的界说是具有典型性的,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中等社会”的状貌。它用“豪农”、“巨商”、“大工业”(这里所谓“大工业”究系何人,待考。若按常理推断,当指居于上等社会或与上等社会有密切联系的张之洞、盛宣怀辈。)作对比,反衬出 “中等社会”在经济上类乎尚有剩钱余米之属的中产地位。但更能说明“中等社会”特点的,则是它所例举的诸种社会构造成分。
(一)“自居于士类者”。
在传统小农社会中,民概分为四: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为四民之首。学而优则仕,修身诚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恪守的政治信念,所谓“士而仕,犹农之耕也”。 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这一特殊身份。但由士而进于政治行政系统的并不在多数,因为取得“功名”本身并不意味着得到官职。在中世纪的中国,“功名”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它不仅把有功名者同平民社会区别开来,而且赋予他们以各种权利。即便未能跻身于官僚之列,也能凭借它左右乡村社会的众多事务,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般说来, 这批人在职的时候,是官;不在职的时候,则是绅。然而士与士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并不都是一样的。 其中之低级者,如众多的生员,只是小绅士,实际上已经介乎绅与民之间,他们没有上流绅士那么多财富和权力,又比一般的“耕氓市井”之类多了一点儿功名。 于是这些人天然构成了乡村社会里的中等阶层。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阶层,有人估计,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一部分士类大约有9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二十四。这个数目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当然也不能直接用来说明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情况,但它提供了一个可资推算的依据。所谓“自居于士类者”,这是一部分。他们不属于中产阶级,也不具有多少新质,但他们又被归于“中等社会”,这种事实说明了“中等社会”依然带有旧时代的深刻烙印。
“自居于士类者”的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19世纪末开始的各种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包括为数不少的留学生,以及从传统经生、儒士脱颖而来的知识分子。同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八股士类相比,这类人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那种“舍帖括八股书画之外更无其他学问”的“阘茸污贱骄蹇无耻之士”,对传统经籍版本的热衷与执著逐步让位于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他们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在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下,他们开始了新的追求。在传统经籍之外寻求有益于社会进化的新知,寻求强国之道。所以 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经出现,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目,甚至被尊为“制造新中国之良工”。20世纪初年颇具声势的“学界风潮”之后,“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寄以殷切的期望。有人曾说,中国社会“殆已有多数之绝望,乃于各种绝望之中而单有一种焉,浮影于热心家之脑中,而产生出一线之希冀者,此何物也?吾必曰:学生社会!学生社会!”“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把学生视作变外来为内在的触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反映了随时代变迁而来的社会观念的变化,突出了学生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与八股士类不同,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拼搏于科场,不再执著于功名,但在久已习惯用士农工商划分各色人等的社会里,他们仍然“自居于士类”。据统计,1902年共有近代学堂35787所,1912年增至82272所;学生则从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比较起来,这批人在数量上更多于八股士类。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于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在这个时候,新的社会需要使旧的知识无用武之地,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因此, “中等社会”里的旧式士类在斯文扫地之后另谋出路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投笔从戎即是一条重要的出路。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陈孝芬是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曾被山东学政赏识过的秀才吴佩孚,最后“弃却儒冠,另就事业”,投身到武备学堂去了。读一读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人物记载,类似吴佩孚者大有人在。除此而外,还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于是而有“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之类称呼。旧式士类的这种变迁,不仅是职业的变化,而且是利益和感情的变化。 在同一过程里,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 随着他们的产生,同时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职业,如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西医)、近代学堂的教师以及职业革命家,等等。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并因此而成为“中等社会”的中坚。
(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
在传统的中国,士以求义为志,商以求利为本。士与商不仅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后者为前者所不齿。在 以农为本、商为末的社会里,轻商、卑商、贱商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商是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的。 但从19世纪中叶起,这种人为的界线开始模糊了。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促使中国感受和认识了商品与资本的力量,于是而有 洋务运动中出现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倾力呼吁“商战”,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商战”不仅包括商业,而且包括工业,它既重视商品的消费流通过程,也重视商品的生产过程,所谓“商战”需以工业、农业为本。作为民族压迫下所产生的反应, “商战”非常自然地把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同民族自强联系起来。于是,为士类鄙夷的商人之业开始得到了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承认。创设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在其初始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印刷各种商业、商界的文件和账簿等,所以称“商务”,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即透露出这种历史信息。与这种观念变化同时发生的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外力侵蚀下的逐步改组,它比观念更有力地改变着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三种新的情况:
其一,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外国商品的输入改变了旧式商业的经营内容,随着经营内容的改变经营方式亦随之改变。上海“京广杂货铺”之易名为“洋货号”、“洋货铺”,当然不只是名称的更易,更重要的是它所经营的商品内容的变化。当商业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的时候,商业的主要联系对象是农村,但当商业以经营洋货为主的时候,其商业网络会撒得更广,其联系对象也会广泛得多。《上海县志》记载了同光时期一个叫朱佩珍的人由“习贾”而独资经营五铺。“起家徒手,无所资藉,徒以重然诺,审取与,为士大夫所爱重。东西各国人士来此经商或旅游者,闻其名,争结纳焉。”这段话生动地说明, 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的结果改变了商人本身。为士大夫所爱重,与东西各国人士相往来的形象是旧式商人所不曾有的。与其说这是“重然诺,审取与”所取的,还不如说这是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的变化所造成的。 在他们和士人之间,传统的界线已趋淡化。
其二,旧式士类渗入了工商业。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种新风气。它既是传统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也是经济与社会变动压力逼拶而成的结果。这两种结果里,又往往交织着爱国主义的情愫。张謇在中法战争后即认为“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甲午战争后,他目睹国事日非,毅然辞官,以状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业,“士生今日,固宜如此”,即体现了这样一种情怀。在这个时期,仅川沙一县就出现过好几个操工商之业的“诸生”。例如:“黄彬,字紫文,高行镇人,国学生,干练有才。光绪初年,邑人朱其昂创办上海招商局,章程皆其手订”;“朱纯祖,字丽生,市区人,监生。……年甫十龄,孤苦零丁,学习米业,中年创设朱丽记花米行,历二十余载”;“姚光第,号述庭,市区东门外人,南邑诸生。……光第感于清季地方贫瘠日甚,就其家设机器轧棉厂,实为川沙机器轧棉之始”。 “诸生”弃文经商,不再局促于科举——仕途之一路,固然是在“耻于言商,耻于言利”社会风气转变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但 这种事实又有力地冲击了旧时代的义利观念,表现出旧式士类的价值指向逐渐由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这批人由士类而来,因此他们并不是旧式商人。他们所操之业多为近代化的制造与贸易。因此也不是旧式商业。
其三,新式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商业。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各省开始兴办农、工、商、矿之类的专科学堂。这种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加上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是一批数目可观的专业人才。他们中的多数人沿着工商业径直走向工商界。这部分人是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工商业者。
上述三类人物都是以工商为业的,但又不同程度地出入于“商与士之间”。他们的利益同新的经济方式连在一起,并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逐步向近代人转变。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保留着传统的痕迹。1904年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纷纷设立商会。到1911年,除川、粤、桂、滇、黔、湘等省没有统计数字外,各省市共设总商会34个,商会616个。(据《各省商会详表》统计,见《中国年鉴(第一回)》,1544~157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以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的商会之设,是20世纪初年出现的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尽管它仍带有某些中世纪行帮的印记,有的甚至还受到行帮的制约,但商会取代行帮却是一种历史趋势。它的大量出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工商业资本家群体意识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工商业资本家在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立宪运动等众多社会事务中日益显示出其自身的实力和存在价值。是他们,奠定了民主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
“方术”一词,始见于《庄子•天下》,原指学术和治术。汉代以降,方术乃泛指一切神术,包括阴阳推步之学、数往知来之术、相术、医术、神仙术、厌胜、符咒、祈禳、扶乩,等等。在中世纪的中国,它们大多出自传统信仰或古代巫术,带有很强的迷信神秘色彩。这里所谓“方术技击”者,泛指用一技之长以取得较为富裕生活的人们,例如名优、书画家、以岐黄之术鸣者,以及其他种种自由职业者。
对“中等社会”内部构造的分析说明,“中等社会”是一个反映特定历史内容的复杂的社会实体。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形象已经可以辨识,但资产阶级的阵营是不明晰的。不明晰是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一种特点,它们同其他社会成分的交叠和粘连还没有完全消除。然而, “中等社会”的复杂性,并不仅仅表现在社会构造上的新旧交叠与粘连。单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就可分为革命与改良两大派别,而在革命与改良两大阵营内又存在着许多宗旨各异的小派别。作为“中等社会”的代表,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这个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它们显然不是铁板一块,毫无分歧的。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固然表现出革命党人很强的近代政党观念,但同时也存在着传统的畛域观念和宗派主义思想,而且后者往往模糊和掩盖了前者。革命党内的许多争议的背后几乎都有这种旧的意识在作祟。1908年《江汉日报》连载的《革命党史》一文就曾对革命党内部各派的政治主张做过介绍:一、以黄兴、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派”,它“承继中国数千年来所谓‘内诸夏外夷狄’之学说,恢复国权,发扬国粹者固有之民族主义也”。中国内地学界多属此派;二、以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为代表的“民族民权主义之急进派”,它“法欧美之学说,倒现在之政府,建社会民主政体……且直以武力而期成功”。革命党人多属此派;三、以陈天华(陈死后由宋教仁“执其牛耳”)为首领的“民族民权主义之渐进派”,它“同第二派之主义,有其实行而大异其趣,不徒用武力,俟党势十分扩张,国民程度稍为发达,而后徐图成功”。此派“党员甚少、势力微弱”;四、以张继为领袖的“无政府主义派”,它主张“倒现在之政府,不建再后之政府”。在这四派之外,还有以“女子复仇”为宗旨的“尊女主义派”,由刘光汉指导;有主张“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派”,以“蜀魂”为领袖。这种说法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革命党内部的政治分野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人都有建立民主政体的自觉意识。孙中山曾说:
“
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
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复杂性。 作为一个整体,革命党人都有反对腐败王朝的要求,是清王朝的叛逆。但“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和“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首先不是把清朝当作一个君主专制政体来反对。翻开那时的报刊,扑眼而来的,不是反贪官污吏,就是仇满情绪(当然也有借这种情绪来宣传民主革命真义的)。这种事实不仅牵制或遮掩了那些“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的民主追求,而且说明了 他们不是或不全是传统社会的叛逆。
“中等社会”的复杂性并不是个别人为的产物,归根结底,它导源于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的反映。 “中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是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互相交织纠缠而又矛盾冲突的产物。中国近代社会是“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的社会。微弱的若干工商业都市与普遍停滞着的农村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与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也都是摩肩挨背地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物质形态上社会发展序列的重叠交错,决定了“中等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观念意识的多重性。 “中等社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但它的复杂性又说明它的不纯粹性。不纯粹性是正常的,天底下没有绝对纯粹的东西。但“中等社会”的 这种复杂性和不纯粹性,毫无疑问又给后来的历史布下了浓重的阴影。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