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看到某些语言学家献给现代语言学的赞美辞,知底者多慨叹之。试想,中国语言学家没有自己的语言观,借用外来的语言符号系统论看语言,而且趋从于语言符号系统论关照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却不知道语言符号系统论只是未经实证的假设。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早就指出它的理论基石“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之说不成立。笔者认为,它的三大理论支柱语言层级装置论、语言基础关系论、语言子系统论均属臆想,这说明现代语言学家是在不知道语言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研究语言的,也就注定不会取得“辉煌成就”。尤其不清楚所谓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其实并没有普遍意义,却奉为圭臬,趋从之以研究汉语,就更要出乱子了。至于出了哪些乱子,潘文国先生《危机下的中文》《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等书及其相关文章中论之颇多,反思派中其他学者著作中也多有论析,兹不赘言。

可是,这么说问题就来了:否定了语言符号系统论,在语言研究中怎样处理语言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怎样看待纯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发展趋势?这的确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纯语言研究为何形成趋势
其实,所谓纯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发展势趋,不只是因为语言学就是语言学,也不只是因为受了语言本体论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者在语言研究中尽可能避开政治问题。这样做,站在语言本体论立场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就要弄清楚语言究竟是什么,有个确能揭示语言本质的语言观,先让语言本体论靠得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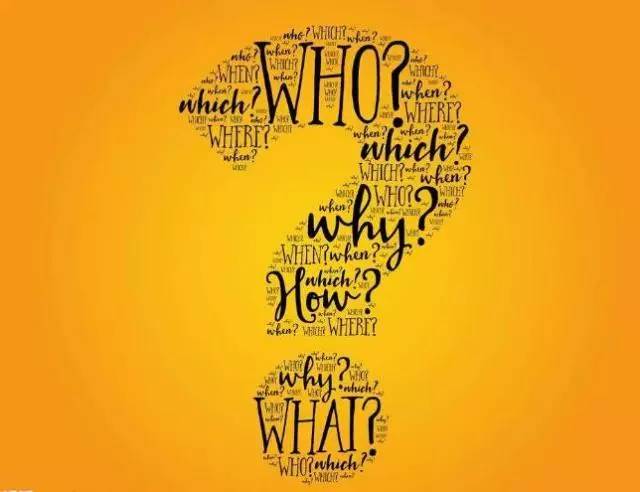
然而,现行语言观——语言符号系统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那么,基于语言符号系统论提出的语言本体论也不成立。换句话说,在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何为语言本体还不清楚,所以现在说的“语言本体论”还只是无本之木。既然如此,坚持基于语言符号系统论提出的语言本体论做研究就不是语言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不可能有语言学的未来。换言之,就目前情况看,纯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发展趋势说到底是一个误区,甚至是一种悲哀,并不值得称许。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语言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纯语言学的研究,学者研究语言多下意识地远离社会政治。这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眼下的原因。例如19世纪,西方学者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语言阶梯论。他们认为,不仅人类语言有等级差别,而且连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也有优劣之分。认为屈折语是高级语言,使用屈折语的民族是文明民族;孤立语是低级语言,使用孤立语的民族是野蛮民族;黏着语及其使用者介于前二者之间。语言阶梯论流行了七八十年,但始终没有人给出有力的证据,却曾被列强用作侵略使用孤立语国家的借口。所以,语言阶梯论看似是纯语言学研究的结果,但实际上带着严重的种族偏见,因而不能说没有政治问题。仅就这一事实来看,后人强调语言研究要远离政治也是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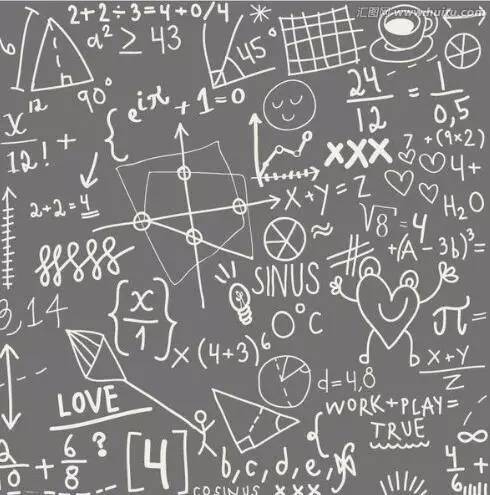
还有,近百年来世界上两大阵营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各阵营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从未停止过,所以,语言研究要确保应有的客观性,要提高其学术价值,语言学要健康发展,就不能沦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这也会让一般的语言研究者远离政治。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现代汉语研究领域里借用“政治正确”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例子很不少。这也会让部分语言研究者自觉远离政治。
语言研究无法远离社会政治
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语言不是在真空中演变的,语言研究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且语言研究要求真致用,就离不开对语言主体之语用行为的考察,离不开对语言演变原因的探讨,这便可能要涉及社会政治因素。

“语言不是在真空中演变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语言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政治变化是引起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故略而不论。
“语言研究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语言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政治。这在国内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且不说“在中国的各个学术领域恐怕还没有一个像语言文字那样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官方痕迹”这条“内线”(详见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序言》),只看“外线”,我们的现代语言学本是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而产生的,也是在趋从于国外语言学思想理论研究汉语的过程中畸形发展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二十年和20世纪五十年代两个历史时期最明显。但是说到底,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历史决定的。借用周景耀的话说,“重外遗内、趋附西方话语的研究理路”,走不出“‘反向格义’的殖民牢笼”,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本质特点。历史学家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这话未免有点绝对,但是可以说历史往往与过去的政治密不可分。如晚清以后,由于国势衰落而被打开了大门,以至于国人产生了自卑心理及崇洋心理,这无疑是语言符号系统论关照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入主汉语研究的主要原因。后来其他语言学理论被引进并且分别受到一些人追捧,也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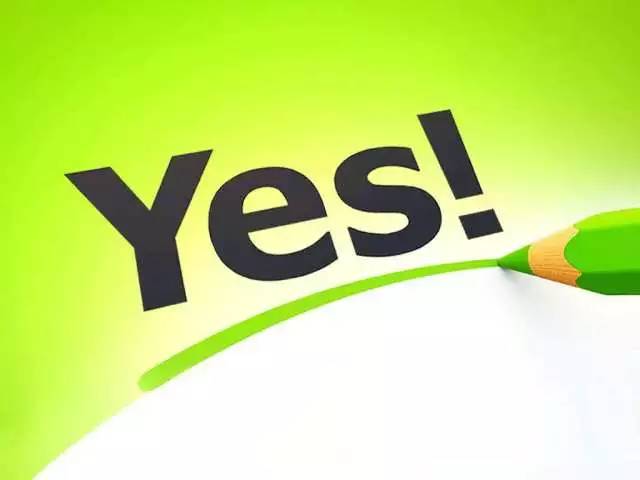
所以,某些现象,孤立地看是纯学术问题,但深层次里却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是一些现代语言学家不这么说,而且饰之以“与国际语言学接轨”而已。但是,当某些事实必须澄清的时候,则免不了要探讨社会政治因素。例如,潘文国先生在《危机下的中文》中初步介绍了国内趋从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所造成的诸多危害,如果一点社会政治背景也不交代,恐怕无法写成该书,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交代社会政治背景,才能让人明白其所以然。
再从一些相关的情况看,一方面,如果当初未受机械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就不会产生。这说明,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并不是纯语言研究的结果。就我们自己的情况看,如果没有近代中国的国势不张,没有列强坚船利炮来侵,没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强势来袭,国人民族自卑心理和崇洋心理就不会产生而且日渐严重,学者也就不会求变心切,而趋从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也就不会形成,以至于发生文化断层,连一些名家的文章中也不乏错引古书的现象。中国现代语言学“重外遗内”传统形成的上述原因或直接体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间接与政治有关。如果离开社会政治背景的考察,有些现象就根本说不清。

另一方面,我们要改变汉语学研究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现状,就必须注意总结趋从于西方语言学思想理论来研究现代汉语的经验教训,有时也要提及包括社会政治因素在内的非语言因素,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因素。否则,只能继续“重外遗内”,继续邯郸学步,而无法“走出‘反向格义’的殖民牢笼”。
还有,站在笔者所提出的新语言观“语言是人与生活世界互动作用中产生的表情达意的音义符号”的立场上讲,从事语言研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经常考察一些人文因素,有时不可避免地探讨相关的社会政治。否则只能继续借口语言本体研究,继续画地为牢,因循守旧,致使语言研究继续滞后于社会发展。

至于不说自己趋从于西方语言学理论做研究,而附和人家谓之“语言学原理”,特别有些学者喜欢附和人家说“语言学无国界”,实则因偏见使然,而且其间也隐含着一种政治主张,因为此前世界上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至于当初索绪尔名其书曰“普通语言学教程”,则是由于受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主导;我们趋从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失败,也可证明所谓“普通语言学理论”不是纯语言学的思想理论。至于“语言学无国界”之说,说到底不过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余音,就更不能说与政治无关了。
综上所述,提倡纯语言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现行语言观——语言符号系统论不支持这样做,所以需要弄清楚语言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谨防两个偏向。一是防止将基于语言符号系统论提出的语言本体论绝对化,因为语言符号系统论并未揭示语言的本质;二是防止为政治服务而使语言研究庸俗化,特别要防止用“政治正确”压人而使语言研究发生质变。总之,当前从事语言研究,既不能机械地回避政治,也不能旁骛政治,只能探讨语言的变化是否起因于社会政治因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语言观更新的汉语复音词疑难问题研究”(15AYY011)的成果]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