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融不进,老家回不去。”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缔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强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个体化并不全然以“我为我而活”的形式呈现,当更多的责任与风险纷至沓来,回归家庭成了一种新趋势。

阎云翔(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纪8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导师凯博文(Arthur Kleiman)曾对他开玩笑说:“云翔,请你不要再写下岬村了,但是你要不断地回去。”
1971年,17岁的阎云翔拿着2角钱的站台票,从老家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偷偷登上北上的列车。
几番辗转躲藏之后,他被位于黑龙江省会哈尔滨以南50公里处的下岬村接纳。
在此后的8年中,他务农,考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而不得,并因为没钱为村中的婚丧嫁娶活动随礼而羞愧。
正如黄村之于林耀华、凤凰村之于葛学溥,在下岬村的特殊经历,成为阎云翔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线索,他的代表作《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所涉及的一些核心命题,也来源于此。

黑龙江一村民居 / 图虫创意
从1989年起,不断重返下岬村成为贯穿其学术生涯的行动。
从阎云翔论文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009)出版至今,中国农村被经济腾飞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裹挟,持续经历巨变。
从“城市融不进,老家回不去”的农民工到以土味、雷人视频强势占领短视频平台的“农村网红”;从时常见诸社会新闻报道的“天价彩礼”“光棍村”到许多返乡笔记结尾处的“农村凋敝”感叹,传媒中可见的农村图景日益复杂。
显然,农村已不再是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般的所在。
阎云翔依然保持隔年访问一次下岬村的习惯,但他渐渐将观察国人生活方式的视角由农村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他发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缔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强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个体化并不全然以“我为我而活”的形式呈现,当更多的责任与风险纷至沓来,回归家庭成了一种新趋势。

《小欢喜》剧照
以下为阎云翔的口述。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叫做《小欢喜》的电视剧。
它是围绕三个家庭展开的,其中有个角色是北京某区副区长季胜利,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他选择回归家庭,强烈要求退居二线工作。
最后,妻子的病好了,他还得到了升迁。越过如此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家庭为重成为国家层面肯定的价值观。
剧中,季胜利的儿子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在当下许多年轻人看来,无论面对什么挑战、付出什么代价,“不分开”都是不可妥协的底线。

个体与家庭:从“反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传统大家庭”属于重点改造对象。
与此同时,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遇到事业和家庭的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放弃家庭,舍小家保大家。
于是,我们会发现那时以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体制精英夫妻分居率特别高。对于他们而言,长期身处异地或者不和自己的子女待在一起,并不是个问题。
过去10到15年中,我对自己提出的一些结论作出重要修正,便与这个有趣的现象有所关联。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我提到了个体的崛起,包括个体主观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欲望的合法化、自我发展在人生中被赋予越来越高的比重,以及年轻一代有越来越强的表达个性和愿望的冲动,等等。
但事实上, “我为我而活”“我即我存在的目的”“我必须以自己选择的道路生活”式个体主义同中国的文化土壤及现实存在冲突。
具体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将更多责任放在了个体身上。
当人民公社与单位体制瓦解,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种种福利和保障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逐渐消失,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与不可预测的风险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甚至在独自应对挑战、承担责任方面,还带有一些不可选择的、强制性的“一刀切”意味。

电视剧《风再起时》就聚焦了八十年代几个家庭的故事。
这也涉及我作出的另一个修正。以前谈论中国家庭生活的变化的时候,我提到了父权被削弱,大家族开始让位于小家庭,夫妻的自主性、独立性日益凸显,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表现得非常充分。
然而,当个体必须以一己之力探索由陌生人组成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社会时,家庭反而成为最可靠的资源、最值得信任的保险机制,重要性急剧攀升。
无论是城市青年动用父母资源或财产找工作、买房,还是通过考学、读书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为了赡养家人,不得不选择稳定性高而非有助于自我实现的工作,我们多少都能看见代际依附的紧密化。
但这种从“反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的转变,其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特点。在强调思想独立、选择自由的同时,越发精细的劳动分工、越发纵深的发展恰恰决定了个体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独立,因为其衣食住行的任何细节都由别人提供,正如扫除实现理想的障碍需要多方面的帮助。
于是,独立和自由的背后,其实纠缠着相当复杂的支持网络:
来自农村的父母倾其所有供子女读书,是为了让他们改善人生境遇,找到好工作;
兼具理想与能力的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发现,要想在城市拥有一份不错的事业,他们拥有的资源远远不够,只能求助父母,通过两代人的共同努力维持基本指标。
从情感意义而言,父母对子女的依赖也在增强,这就是为什么“空巢”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当所有人都想实现自己定义的理想生活状态,就会愈加清晰地感受到手头资源的缺乏,不断争取资源并求助的过程中,就愈加不能独立,如此循环往复。

老人为回家探亲的孩子准备了满满一竹篮的“山珍”。/ 图虫创意

现在要判断一个人发展得成不成功
你可以看看他办事、摆酒的时候
请了多少没有亲属关系的客人
只有弄清以上的基本问题,我们才能将目光转向农村,因为农村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这种宏观变化是无法割裂的。
公众倾向于认为这70年来中国私人生活的起点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而我则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指出,个体化是个连续性的过程。
换言之,个体化事实上发轫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集体化时期,后者的重点在于将个体从传统的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这个“破”的过程是在文化和政策层面上全面展开的。
在这之后,女性与青年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这些都可以看作推进个体化的有利因素。
说到底,国家推进社会改造的目的,就是把个体先变成各种集体的成员,即把他们从千千万万个亲缘组织、家庭组织中拿出来,重新嵌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框架。
当这一步完成之后,国家又通过经济改革从个体生活中逐渐撤离,降低了集体对个体的那种既是束缚又是保障的影响,个体就获得了更多人生选择方面的自由空间。
从这个意义讲,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后40年对于促进个体化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
不过在后40年当中,我们还发现与这一进程相关的新型人际关系现象。以农村为例,可能有“天价彩礼”,或者拥有一定权势的人通过婚丧嫁娶甚至摆“无事酒”敛财。这分别是家庭内部和公共生活中的典型例子。

婚礼是村里一等一的大事。/ 图虫创意
彩礼的高涨我以前解释过,实际上是代际之间财产转移的一种形式,即年轻一代通过结婚提前支取他们认为应该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家产。
但到了现在,这种提前支取愈演愈烈,变成一种代际剥削,年轻一代尽可能掏空父母的钱包。父母为筹备年轻一代的婚礼,甚至可能欠下债务。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从集体中独立出来的年轻人越发熟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争取自身发展的各种有益条件(但他们往往忘记尊重他人与自身对等的权利,也忘记承担相应的义务)。
除非是在特别穷苦的情况下必须留一笔钱为家里的男孩娶媳妇,新娘的父母很少截留彩礼,那么彩礼事实上就成了新娘的私房钱,或者说小两口的安家费,这使得新娘在要彩礼时特别有动力。
另一方面,彩礼还具备父母情感投资的色彩,等于说那种无条件的孝顺文化崩塌以后,代际之间能不能保持良好的人情关系成为父母能否获得养老保障的条件之一,子女也会因此而自我说服:
“反正你们将来也得靠我们养,现在多要点儿是应该的。”

广东某地婚礼现场,光酒席就备了3天的量。/ 图虫创意
而摆酒的实质,则是“过去送出的礼物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收回”,譬如你可以通过给父母祝寿,把之前参加别人婚礼的份子钱要回来。
在一个流动性比较低的村子,大家在随礼方面心中都有一杆秤,因而可以维持相对的平衡,唯一吃亏的可能只是那些没有小孩或人口比较少的家庭。
但当这种共同体因为城乡流动的增加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当许多人搬走并不再回来,办事、摆酒、收礼就成了越来越工具化的理性行为。
而在权势加持的情况下,积极随礼会被认为办事聪明,不随礼则意味着将来会遭到报复或被边缘化(至少很多老百姓认为有这种可能性),这就使得酒席成为权力拥有者敛财的手段。
在传统文化中,每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基本上是稳定的,就是以家庭和亲属关系为基础,不会增长多少。
但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络的扩张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因为这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增加,可供“薅羊毛”的对象选择越来越广泛。
所以现在要判断一个人发展得成不成功,你可以看看他办事、摆酒的时候请了多少没有亲属关系的客人。
总而言之,“天价彩礼”“摆酒敛财”虽属于毫不相关的范畴,但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即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情文化、人际关系网络仍然非常重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学者曾经假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个体进入流动状态,有机会和更多陌生人接触,人情文化、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会降低。现在证明这个预测是错的,所以很有意思。

央视节目《陇东婚事》描绘了一个甘肃小县城的婚恋产业链。

“农村凋敝”有煽情色彩,
而“融不进,回不去”
对于所有移民而言都是一致的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正在通过短视频网站成为“网红”。这一通过自媒体毫无门槛地表达自我的颠覆性变化,是这三五年值得关注的现象。
它究竟会对农村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目前没资格评论,因为我不确定在没有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人愿意以出位的方式表达自我;
而那些土味、雷人的表达,究竟有多大部分是内心的真实写照,而非出于吸引眼球、获取流量的动机?
不过“农村网红”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点——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每个人自我表达的愿望都会得到实现。
因为技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也将曾经不知道彼此存在但处于相同生活状态、拥有相同想法和审美的人联系在一起。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你大可嘲笑农村“网红”拙劣、低级、不择手段,但你无法否认自己和他们拥有如出一辙的表达欲。

网络上爆红的竹鼠兄弟
与此同时,“农村网红”所带来的“城乡结合部审美”也引发了广泛的议论。有人觉得这意味着带有主体意识的亚文化的崛起,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对城市文化的不成功模仿。
我将它看作城乡差别,或者说所谓“城乡高下心态”的一个体现。这背后自然有户籍制度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进程确实是以城市化的形式表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多少都被追赶心态笼罩,并在各个层级上体现出来。
我们能看到的是农村青年模仿城市青年、小城市向往大城市,那么大城市向往什么?
还记得90年代的时候动不动就说看我们这儿建了多少高楼,越来越像香港了,其实香港也不过是“水泥森林”吧,但“国际化大都市”所具有的范本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然而追赶也好,竞争也罢,你会发现实现发展的渠道越来越雷同,有关美好生活的想象越来越扁平,变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有一条路可走。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是单向度的,社会资源和劳动力越发向城市集中。于是我们不时听到“农村空心化加剧”“城市会在未来彻底吸纳农村”的声音,前些年接受采访时,也有记者提到,很多非虚构作品也好,返乡笔记也好,都在惋惜“农村凋敝”。

农村真的空心了吗?/ 图虫创意
我的判断是,先看看这些文字出自谁之手,答案是城市人,或者一些出身农村但后来受过良好教育、不再生活在农村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是站在农村外面为所谓“凋敝”唏嘘。他们觉得,如果没有那么多人“逃离”,留下来的不只是老人,就能实现繁荣,同时竭力维持着世外桃源的想象,好让他们在城市的嘈杂之外保留一个精神寄托。
这其实是带有煽情、夸大色彩的,同时也不大公平。
事实上,年轻一代如果发现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是可能去任何地方的,包括返乡,正如一些老人会进城去和子女同住,给他们带孩子,我觉得不应该下过于绝对的结论。
对于农民工群体“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的尴尬境地,我也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如果户籍制度有所改革,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就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落脚城市”,农民工也就是正常的移民群体。
而他们心理、文化层面上的挑战,对于所有的移民而言都是一致的。

“移民群体”应有一个被接纳的机会。/ unsplash
以我自己为例。我1986年到美国,现在待了33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融入这个国家,同时我也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回到”中国。这和“城市融不进,乡村回不去”的农民工有多大区别呢?
有时候我觉得愿意移民的人本身是要具备一定心理素质的。我具备比较强大的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精神,所以反而不那么需要认同,不那么在乎融入,而是彻底地享受多元文化所提供的丰富资源和自由选择的生活状态。
或者说,我觉得处于一种中美文化中间地带也是全球化时代独特的认同。假设没有户籍制度的束缚,新移民“回不去,融不进”的心理状态到底有多么“尴尬”便值得讨论。我认为这是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多少都要面对的新常态。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8期
✎作者 | 卢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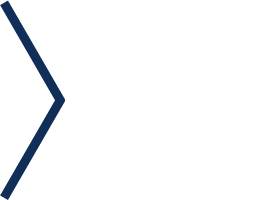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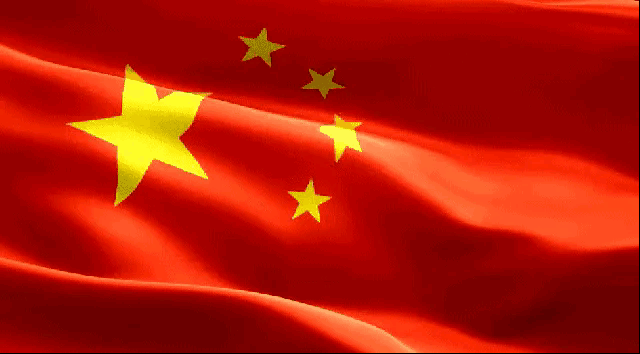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